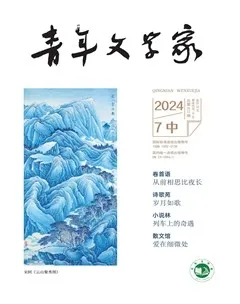論王粲《七哀詩三首》及其北人情懷
提及建安時期的詩人,除開“三曹”之外,首推的必然是王粲。王粲作為“建安七子”之一,被劉勰稱為“七子之冠冕”,歷來受到人們的推崇,是研究建安時期詩人群體中繞不開的存在。《七哀詩三首》作為王粲早期詩歌代表作,展現了王粲在詩歌上的藝術手法與成就,詩中承載的思想情感,是王粲荊州避亂時期內心北人情懷的集中體現。
“國家不幸詩家幸”(趙翼《題元遺山集》),漢末動亂,政治腐敗,諸侯混戰,百姓流離失所,士人顛沛流離。“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劉勰《文心雕龍》)的社會現實,使得士人開始正視自己內心的情感,作文誦詩,將自己的情感世界展現在世人面前。“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劉勰《文心雕龍》),漢末動亂,轉變了文人抒情的方式,促進了五言詩的發展。傳統文化在建安時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裂變,呈現出多種文化競相爭奇斗艷,并行不悖的狀態。這一時期詩學觀念的轉變,更多地體現在由“言志”向“緣情”的轉變,《尚書·舜典》云:“詩言志,歌詠言。”《毛詩序》言:“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漢末建安時期,詩風的轉變正是突破了自古以來的藩籬,將詩歌的抒情功能不斷放大,讓詩歌擺脫了長期以來為政治教化服務的功能,而單純強調詩歌的審美特征,為后來的詩歌發展開闊了道路。
王粲與他的《七哀詩三首》歷來為人所重視,并不斷被研究。劉勰《文心雕龍·明詩》提到,“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又說其詩“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龍·才略》中更是盛贊:“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鐘嶸《詩品》將其詩列為上品,稱其《七哀詩三首》為“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劉熙載《藝概·詩概》則云:“仲宣情勝,皆有陳思之一體。”方東樹《昭昧詹言》稱王粲:“蒼涼悲慨,才力豪健,陳思而下,一人而已。”今人研究王粲不勝枚舉,綜合來看,王粲是以“慷慨”為時代底色,當然這與他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可分割,其個人表現為才情橫溢、辭藻華美的藝術風格。在五言詩方面,王粲典正穩健、體弱情柔、文辭俊逸的詩風,為人所稱道。
一、王粲的北人意識探因
大多數研究王粲的學者都將其詩歌創作以建安十三年(208)為界,分為兩個階段。詩人的創作風格與其所處的環境、所遭受的境遇息息相關,如杜甫的詩風在安史之亂前后便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風格,王粲詩歌創作風格也因不同的身份地位,發生著轉變。另外,兒時的出身環境,在一個人成長過程中有著深藏的精神烙印,影響著一位詩人的創作,成為他詩歌中潛藏的精神和情感體現。
南北之分,一直是中國歷史上難以回避的問題。先秦時期,北方一直是王朝的統治中心,更是“中國”的代名詞,南方由于地理環境等原因,遠離政治中心,始終被視為蠻夷不化之地,被排除在“中國”之外,西周乃至春秋戰國時期,作為諸侯國的楚國占據南方大半疆域,實力強大,但依舊被稱為“楚蠻”或者“荊蠻”。到漢代,哪怕開國皇帝出身舊楚之地,由于政治中心始終在北方一帶,南北之分依舊埋藏于世家大族的觀念之中。出身北地的世家大族始終對南方心存歧視,這種強烈的南北對立意識,在許多文學作品中都有體現,而作為北方世家大族出身的王粲,身上同樣有著濃厚的北人意識。
自西周宗法分封以后,宗族觀念便深深扎根于中國大地。漢魏時期,宗族觀念尤為盛行,世人皆以豪族為榮,以寒門為恥。而士族子弟,也多以先祖為榜樣,希冀在功名事業上能夠繼承先祖輝煌,光耀門楣。《三國志·王粲傳》載:“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王粲出身豪門,祖上位列三公,可謂顯貴,而當時的大將軍何進,帝后之兄,原是販肉屠夫,因后戚列于高位,想與世代清貴的王氏結親,竟都被拒絕,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門第觀念。而王粲出身名門,又滿懷抱負理想,家族烙印深深打入他的靈魂,怎能容忍自己碌碌無為,將一身才華盡付東流而無半分漣漪。
漢末動亂,群雄割據。王粲作為一介文人,沒有陷陣殺敵的武藝,也沒有縱橫捭闔的辯言,更沒有平定天下的謀略,失去了安定生活環境的他,面對這樣的亂世,難免心生慷慨悲涼之感。這也恰恰是亂世文人的共同特點,成就了這一時期“建安風骨”的時代特征。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寫道:“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徐公持也在《魏晉文學史》中說:“尚氣、慷慨、悲情是建安文學情感取向方面的特征,它與文學內容的真、高、剛、直特征,構成了建安風骨的重要兩翼。”“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漢末亂世,自然是亂世文學,充斥著悲情的基調。少年成名的王粲,面對亂世,注定是要經歷悲劇性的遭遇,從蔡邕“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三國志》)的聲名鵲起,到避難荊州時劉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三國志》)的冷落,使得他內心深藏的北人意識迸發,無論是《七哀詩三首》還是《登樓賦》,都表現出濃厚的北人意識和“思歸”情結。也正是這大起大落的遭遇,讓王粲在創作上實現了由四言詩到五言詩的蛻變,將詩歌的抒情功能大大增強,其情感抒發在個體化與社會化之間追尋到了契合點。
二、《七哀詩三首》的北人情懷抒寫
《七哀詩三首》是王粲早期五言詩的代表作。“七哀”,《文選》六臣注呂向注:“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余冠英在《三曹詩選》中稱其為一種樂府歌辭。雖然現存三首詩作的寫作時間分建安前后,但都具有典型的建安詩歌的風格特征,蒼涼悲慨,志深筆長。而《七哀詩三首》其一與《七哀詩三首》其二中表現出的深沉的北人情懷和“思歸”心態,是王粲北人意識的抒發與時代背景的融合,是由早期五言詩重在社會化敘事向重在抒情化敘事的轉變,是由言志的、議論的、散文化的寫作方式,向緣情的、寫景的、詩意化的寫作方式的飛躍。同時,表現在王粲詩歌中的這一種變化也是建安時期詩人群體的一個縮影。
王粲的北人情懷抒發,離不開時代背景的影響,同時也是個人自我遭遇的寫照。王粲為名門望族之后,祖上位列三公,年少成名,本以為可以大展才華,卻因戰亂,背井離鄉,來到了地處南方的荊州;又本以為可以依靠祖輩蔭庇,有一個安身之處得以施展才華,卻因“體弱通侻”而備受冷落。這種心理落差,積郁于心,使他很難對荊州產生心理認同,加之出身自北方士族的優越感,更加劇了這種身份上的疏離感,表現在詩歌上,便有了《七哀詩三首》其一和其二中那股濃濃的北人情結,久久不能釋懷。在劉表死后,曹操兵發荊州,王粲極力勸服劉琮投降曹操,而不是依附孫權或者劉備,未免不是受他內心北人意識的影響,畢竟曹操當時統一北方,歸附曹操便可以回到他朝思暮想的家鄉,這種“思歸”的心態,可以說貫穿了他荊州時期的文學創作。當然,王粲這種北人情懷并不是一開始就表現得非常濃烈,而是隨著時間不斷強化。我們從《七哀詩三首》其一進行分析: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這首詩被認為是王粲赴荊州時所作,創作時間諸家各有爭議,爭議之處主要在于王粲赴荊州的時間。而無論主何時之說,都不能忽視王粲在詩中描寫的場景與所表達的思想情感。這首詩主要描寫了詩人因戰亂從長安避難去往荊州時所見所感,全詩“事—景—情”三者結合,形成完整的結構,同時采用雙線結構,第一線索:開篇寫明當時的社會背景,李傕、郭汜等禍亂京師;之后交代抒情主人公在戰亂中不得不背井離鄉,避亂保命;然后寫離開時送行的悲傷場景,感受到個人命運無法把握的無奈。第二線索:寫路途所見,通過饑婦棄子表現普通百姓的沉痛與苦難,“蓋人當亂離之際,一切皆輕,最難割舍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寫其重者,他可知矣”(吳淇《六朝選詩定論》),令人肝腸寸斷;最后抒發自己的感懷。兩條線索交叉,“離京”與“望京”“治世”的對比,將個人命運的無常與世人共同的悲苦相融合,成就了這一首時代的悲鳴。張玉榖在《古詩賞析》中評價:“末日,南登回首,兜應首段;傷心下泉,繳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動。”方東樹在《昭昧詹言》中評價:“其莽蒼同武帝而精融過之。其才氣噴薄,似猶勝子建。”而王粲這一時期的北人意識并不是太強烈,更多的是對自身深處亂世的憤懣與迷茫。但詩中“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與“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四句,依舊表現出王粲內心身為北人的優越之感,還未能在荊州立足,內心便已經對荊州輕視,身份的疏離與內心的不認同,似乎注定了王粲在荊州郁郁不得志。
北人情懷最濃烈的,當數第二首。
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
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
山岡有余映,巖阿增重陰。
狐貍馳赴穴,飛鳥翔故林。
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
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襟。
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
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
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詩人開篇設問便帶有濃厚的北人情懷,“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這蠻夷之地本就不是我的故鄉,我為什么要在此滯留?此時王粲已經三十歲左右,在荊州度過了十三年的時間,一身才華無處施展,同時又備受冷落。內心復雜的情感,似乎是難以深藏,在同時期所作的《登樓賦》中也明顯表達出來,“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無不是對荊州生活的失落與惆悵,以及對北方故鄉的“思歸”之情。第四句的“愁”字,更是成為點明全詩的主旨,一個“愁”字貫穿全篇,成為全詩之眼。而就整首詩來看,詩人抒情寫景,已不同于東漢五言詩重敘事的風格,其寓情于景和借景抒情的手法,更是成為后世抒情寫景的范式。詩中“方舟”以下八句,通過景物描寫形象生動地表現了詩人內心深處的思鄉之情,“狐貍馳赴穴,飛鳥翔故林”兩句更是借用屈原《九章·哀郢》中的“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通過用典的形式寫景以寓情。“日暮”“重陰”“清響”“猿吟”等景物與詩人情感發生共鳴,引出了詩人心中無限的惆悵與哀傷,將江上泛舟看到的景物渲染得更加凄涼,進一步突出了詩人滯留荊州不能返鄉的孤獨與寂寞。詩歌通過賦予景物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將情與景交融,并注入詩人的自我意識,這不得不說是建安時期詩風觀念的一大轉變與成就。同時,詩中“愁”“悲”“憂”等強烈的感情色彩,也將王粲內心濃厚的北人情懷顯露無遺。而詩末“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表現的思鄉難歸、壯志難酬之情,也仿佛為之后歸附曹操埋下了伏筆。
漢末建安時期,動亂的社會現狀加速了文學的覺醒。每一位被卷入時代洪流的文人都身不由己,但文學的覺醒帶來的情感抒發,可以給他們在心靈的天地尋找一分安定與解脫。王粲生于世家,這是他的幸運;遭逢亂世,也是他的不幸。才華難以施展,避難荊州,備受冷落,使得他內心深藏的北人情懷迸發,從而通過詩賦等形式將潛藏的情結落于筆端,留下了千古名篇,這是他獨有的氣質。正如沈約在《宋書》中所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并標能擅美,獨映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