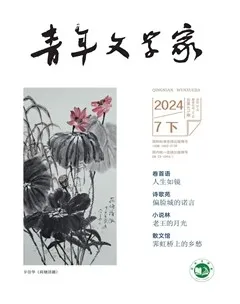意境在接受思想上對意象的超越


意境是一個活躍在中國古代文論中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國美學的核心范疇。盡管它由來已久,但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至今學界對于意境的范疇仍存在著種種不同觀點。這說明了意境概念的重要性與話語的蘊藉性,同時這些不同的觀點也將意境變成一個具有豐富闡釋空間的美學范疇。探究意境范疇中的接受思想,就要重新追溯意境的生成歷程,而從歷時層面來講,意象和意境關聯密切,相互作用,意境在意象的基礎上出現。德國美學家姚斯認為歷史的接受者經歷了一個保持固有經驗,完成接受,改變舊經驗,從而建立新的經驗結構的過程,這是一個發展的過程。意境比之意象具有超越性,具有新的意義內涵和審美經驗,更能體現“天人合一”“生命超越”的傳統文化和哲學底色。這種超越性體現在接受思想方面最為明晰,接受理論將提供新的研究視角,為意境在中國文論的當代建構中獲得新的闡釋提供理論依據,也為中國乃至世界的接受理論研究開拓新的視野。
一、意象范疇的接受思想分析
先秦是中國文化的奠基時期,意象與意境的概念在先秦時期開始萌芽,以道家和儒家的思想精華為主。之后,在漢魏六朝時期正式誕生了意象的概念,這與魏晉時期“人的自覺”與“文的自覺”有著密切關系。在這個階段,出現了宗炳“澄懷味象”說、劉勰“窺意象而運斤”的神思論等獨立的文論思想,“象”從哲學的抽象概念中抽身而出,向審美功能進行轉變。
(一)讀者之意
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其文論中的接受思想是“以意逆志”說,在《孟子·萬章上》有言:“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講解了最早的解讀詩歌的方法,那就是用讀者自己之“意”去追尋“詩”之“志”,也是詩人盡力在詩歌中表達出的意思。周克平認為“在言意關系上,儒家主張‘言意一致’”(《中國古代文論讀者意識與特征》),正如孔子的“文質彬彬”說、“辭達而已”說要求作者與文本所呈之“意”相符,所以孟子所言之“意”屬于文本或者作者,而非讀者。但不可否認的是,孟子的“以意逆志”說對孔儒文論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證明了早在先秦時期的文論思想就已經意識到接受客體或者說讀者的存在,只不過尚未能發現其自身的主動性和接受過程中的再創造活動而已,而后者將會在接下來中國文論有關意象和意境的思考中得到更進一步的闡釋。無獨有偶,關于言意關系,道家代表人物莊子在《天道》和《秋水》兩篇中提出了具體的“言不盡意”說,又在《外物》中認為“得意忘言”,這不僅強調作者在創作時會意成言的困難,其實也證明了他的讀者意識,因為如果沒有接受的環節或者讀者只能接受作者之“意”、文本之“意”,他又怎會知道“言不盡意”的事實,或者能夠為了“得意”可以“忘言”,舍棄文本之媒介。漢代許慎在《說文解字·心部》中也對“意”的解釋有類似的讀者意識,他寫到“意,志也。從心察言而知意也”,所謂“從心”而出以察言,歸根到底是讀者之“心”察他人之“言”。
(二)象在言意
在中國古代文論的言意關系中發現讀者意識之后,對于意象范疇來講,“象”的生成極為重要。早在《周易·系辭傳上》中就提到了“象”的由來:“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象”作為解決“言不盡意”的問題而出現,換言之,是為了“盡意”而存在,其中暗含的邏輯是“象”能比“言”更好地“盡意”。這又有兩層意思:第一,“象”能更好地表達作者之“意”;第二,“象”能更好地令讀者明白其中之“意”。值得注意的是,“象”作為言意關系當中的媒介意義也已經凸顯了。之后,魏晉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以老莊解易的方式也明確了“象”的媒介功能。他說:“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建立了一個“意—象—言”的結構,而“象”在言意關系中是至關重要的樞紐,因為“意”通過“象”來顯現,“象”借助“言”而形成。但因為“得象忘言”“得意忘象”,所以“象”超越了“言”,“意”又超越了“象”。這也是對老莊“言不盡意”“得意忘言”思想的延續,而到王弼這里,“象”作為媒介也無法再能“盡意”。因此,誠如朱良志所講,在“象”的概念演變史中“已經確立了象在展現無限世界意義方面的特殊功能”(《中國美學十五講》)。意象中“象”的這個重要功能,這為后來“象外之象”“境生象外”等學說乃至意境范疇的生成打下重要基礎。
二、意境范疇的接受思想分析
魏晉時期,意象正式進入中國古典美學領域,到了唐代,又融入了佛家宗教思想的“境”的概念被創造性地引入到文藝領域,由此開創了一個新的審美范疇—“意境”。唐代以后意境理論逐漸豐富和成熟,在繼承意象范疇的基礎上,發現了“象外”的特殊審美空間,并更加著重于“意”與“境”的進一步融合,直至將意境上升為一個具有中國審美特色的美學范疇。
(一)境生象外
《說文·田部》中對“界”的釋義為:“界,境也。”可以說,“境”和“界”的含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境界是一個有局限意義的、現實直觀的時空概念。但是佛學傳入中國后,佛經的翻譯常借用“境界”一詞,將它從原來實指疆土界限的含義提升到精神的層面,表示一種外在現象內化于心的形態或者高度。之后,“境”的概念進入文論思想。唐代僧人皎然便從禪學的角度講“詩情緣境發”(《秋日遙和盧使君游何山寺宿敡上人房論涅槃經》),“取境”自“采奇于象外”(《詩式》)。所以,當意境在意象生成之后的誕生,于意象范疇中的先秦儒道思想基礎上又加入了釋家的理念,如此產生了新的內涵,也就是繼道家發現“言外之意”的“道意”之后,禪學對于“空”之“真意”的領悟,加深了原本就已在意象中出現的虛實結合的審美取向。這意味著意境繼承了“得意忘象”的審美理想,不再滿足于“言盡意”“象盡意”這樣的言意關系的解讀,復歸心與物之間的根本聯系,而又在超越象的媒介功能之上生發了“境”的概念。之后,劉禹錫的“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記》),司空圖的“味外之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與極浦書》)的提出都將意境的審美追求延伸到更遠的理念世界,于有限中見無限,于短暫間求永恒,重新打開了具體成型的意象中“言余不盡,余味無窮”的審美空間。由此可見,意境范疇是儒道釋三家思想融合的產物,體現了意境在意蘊淵源和審美追求上對意象的超越。
(二)意與境渾
“境”在詩學領域的最初運用始于王昌齡的《詩格》,詩人在書中用“亦張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則得其真矣”,強調了讀者在接受過程中主體想象思維的再創造能力。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中描繪了二十四種不同的詩歌意境,其創造的關鍵在于發揮“超以象外”的“虛”的作用。意境要善于以實出虛,也是暗指接受主體應該發現作者和文本之外的讀者之“意”。此外,司空圖認為意境所能達到的藝術高度在于“思與境偕”,主張在意境的審美空間里主體與客體、理性與感性、思想與形象達成天衣無縫的融合。清代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緒論內編》中點明了意境中除“虛實結合”之外的另一重要概念—“情景交融”。關于“情”與“景”在意境中的交融,清代王國維用“無我之境”與“有我之境”的概念將情景關系聯系到了心物、主客的關系。之后,王國維進一步在《人間詞乙稿·序》中對意境范疇進行總結:“文學之事,其內足以攄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與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境勝,或以意勝。”意境就在于“意”與“境”的融合為一,不再局限于孤立的“象”,而在于虛實、主客、情景的渾然一體的審美空間。“意境兩忘,物我一體”是中國最高的藝術境界,所以意境的本體是“意與境渾”,而以“境生象外”的表象顯現出來。
三、意境對于意象的超越
放眼接受美學視野,通過德國學者伽達默爾、姚斯和伊瑟爾的接受理論,我們能借助西方概括性、系統化的理論成果對意境于意象在接受思想上的超越進行更為具體的探討,以期獲得新的解釋。
(一)得意忘象
意象范疇發展演變至唐初時,殷璠在《河岳英靈集》中提出“興象”說。殷璠在用“興象”評論盛唐詩歌時,強調詩歌應具有言外之意的詩境,給讀者帶來一種耐人尋味、含蓄不盡的審美體驗。“興象”說的出現可以說是意象范疇向意境范疇演變的關鍵節點。在那之后,關于意境“境生象外”的觀點才逐漸完善。意境范疇對于“韻味無窮”的審美追求,也是王弼“得意忘象”的根源之果,最早來自老莊道家“大象無形”和“唯道集虛”的傳統哲學思想,也就是“言不盡意”說的延續。這些思想的根基都是姚斯所謂讀者的“期待視野”的形成。意境從意象中生發,讀者在“期待視野”中繼承著前人的審美經驗,又不斷擴大著“期待視野”。不同的是,意境本身的創構就蘊含“期待視野”自我擴展的審美追求,意境因此在歷代的讀者面前擁有永恒的魅力。
早在先秦時期,古人就已在孟子的“以意逆志”說中隱約察覺到文學作品的接受過程是伽達默爾所謂讀者與文本間的視域融合,同時也受到“言不盡意”說的啟發,在意象、意境的范疇中加入讀者再創造的意識,側面證明了作品文本中擁有讀者想象力發揮的空間。“虛實結合”“韻味無窮”的意境中那些含義不明的“虛空”,正是現象學美學家英伽登認為文本中存在的“不定點”,也是伊瑟爾進一步提出的“空白”,等待讀者用自己的理解對文本的這些“虛空”進行填充。伽達默爾早已提出,藝術存在于讀者與文本的“對話”之間。在意象中,這種“對話”總是被具體的物象所禁錮,但是意境本就將“對話”的全部內容包含在“境”的審美空間里,所以意境對于意象的超越在于“境生象外”,得意忘象而生境。
(二)境與世界
意境對于意象的超越,從殷璠的“興象”說開始。“興”來自《詩經》中出現的最早的詩學概念—“賦、比、興”,體現古人對于心物關系的最早了解,指內在之心受到外在之物的觸發而進行感興。“心如何感受物”的問題體現在文學上就是“言何以表達意”的問題。起初,“象”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選擇,是心物、言意之間最好的媒介,但后來“立象”也不再能“盡意”了,“意”超越了“象”所能表達的范圍,于是“境生象外”,“境”成為“象”之上更好的媒介。
然而,朱良志卻說“境可以說并非僅僅是媒介,它就是世界本身”(《中國美學十五講》),他解釋說:“象”重外在表征,而“境”重心物關系;“象”是經驗中的象征、喻體,而“境”是體驗中的世界的呈現。“境”不僅是連接心物、言意的媒介,也是“世界本身”。“境”中有“象”,以“象”出“境”,意象是意境的基礎,但真正使意境之為境的是意境超越意象的部分—超乎主客、物我渾融的審美世界。意境的審美追求意圖進行作者、作品與讀者三者的消融,“確立了以生命本身來呈現生命的原則”(《中國美學十五講》)。
中國的意境范疇與“反語言、反知識”的中國哲學相關,其追求就是超越具體的言象世界。意境范疇中對于“意”之含蓄、“境”之空白的審美追求,使得其本身自成一個不斷生發、指向無盡的審美空間,是一個具有生命力的、同時也超越了有限生命的審美空間。它蘊藏著超越現世人生以及具體個人的有限,向著代表無限的“天道”進取,直至達成“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追求。這是中國古典文化與傳統哲學共同的思想根基,代表了中國藝術獨特的生存情感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