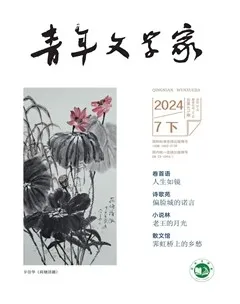迷失于鏡像,建構于虛幻
《高老頭》是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著名小說之一,它展現了一個青年野心家拉斯蒂涅在巴黎逐漸墮落的故事。拉斯蒂涅出身于沒落貴族,只能靠自己努力生活,他渴望通過學習法律改變命運,然而在巴黎社會中,他在金錢、權力和道德的層層考驗和打擊下,逐漸放棄自己的原則和良知,最終陷入墮落。
法國精神分析學家拉康提出的“鏡像理論”是后現代精神分析的重要理論之一。其主要出發點是經由他自己“改造過的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其核心在于“一種無意識的自欺關系”。在個體發展的過程中,會經歷一個自我認知的階段,他們會觀察和模仿他人的行為,并將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和評價內化為自我意識,從而形成自我認知。但是這個“鏡像”并不是真實的自我,而是一個被社會和文化所塑造的虛假的自我,是個體在成長過程中為適應社會而形成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導致個體產生無意識的自欺行為,實質上是他者對自我的異化和奴役。基于此,本文將結合巴爾扎克和拉康的“鏡像理論”,探討拉斯蒂涅在自我建構過程中所遭遇的悲劇性轉變,并進行剖析與反思。
一、前鏡像階段—純真本我
在拉康的“鏡像階段”理論中,前鏡像階段即嬰兒出生后1至6個月時期,在這一時期,嬰兒對外界的感知呈現為被動狀態,他們的肢體亦尚未發展協調,對鏡中的自我形象尚未形成認知,只能靠著視覺圖像、聲音影像等外部力量被動地去接受外部給予他的感受,來完成對最初世界的認知。因此,此階段的嬰兒亟需成人的幫扶,表現出明顯的依賴性,即“動力無助”和“仰倚母懷”。還未前往巴黎的拉斯蒂涅正處在這一階段。
拉斯蒂涅來自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家里人口眾多,為了每年給他匯去一千二百法郎,只得省吃儉用”,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在鄉下度過了相對寧靜的童年。這種缺乏物質豐富和社會誘惑的生活環境,使他的內心世界保持了一種原始的純良和未被世俗沾染的本真。這時的他,對外界的認知完全依賴于他人給予的圖像和聲音,沒有自己的判斷和理解。家庭的溫暖和鼓勵對拉斯蒂涅的成長起到了關鍵作用,這不僅為他學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在其性格形成和理想塑造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拉斯蒂涅的追求不止于個人命運的改變,他渴望成為一位正義的法官,以改變家庭和社會的命運,體現了他對公正社會的深刻追求。在當時,這樣的理想或許被認為是幼稚的,但也正是這一幼稚的想法展現了拉斯蒂涅最初的純真,同時對當時的社會現實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這一時期的經歷為他未來的成長和選擇埋下了伏筆,也塑造了他對社會和自我認知的獨特視角。
二、鏡像階段—自我探尋與掙扎
初至巴黎,拉斯蒂涅居住在骯臟破舊的伏蓋公寓,作為典型的下層社會生活空間,其雜亂無章、魚龍混雜的狀況象征著主人公內心最初的質樸與夢想。而當他踏入鮑賽昂夫人的客廳,他才真正領略到上流社會的奢華。客廳在此刻不僅是一個物理空間,更是上流社會生活方式的象征—豪華馬車、金色扶手以及點綴其間的鮮花,這一系列細節描寫構成的不僅是物質景象,更是拉斯蒂涅內心世界對奢華與地位的渴望。他第一次對自己的理想產生動搖,但是他和所有年輕人一樣有著狂妄的特質,“為了錦繡前程,拉斯蒂涅克決心雙管齊下,既依靠學問,也依靠愛情,既成為一個有學問的博士,也做一個時髦的年輕人”。他渴望把兩條線都握在手中,他想象自己將成為一個完美無瑕的上流社會成員,兼具學識與吸引異性的魅力。這種追求可視為對拉康“人類認識起源于人們對形象的迷戀”理論的生動詮釋,具體來講“從本質上看既是一種審美認識,也是一種虛幻,它表示的是主體趨向于整體性和自主性的努力”(劉文《拉康的鏡像理論與自我的建構》)。借助“鏡子”,也就是巴黎上流社會生活這一媒介,拉斯蒂涅在尚未成熟之時便想象自己是一位學識淵博、風度翩翩的貴族。這一形象補足他尚未成熟的部分,本體的“他”與鏡中的“他”構建起關系,由此進入“想象界”。
(一)虛幻的自我探尋
拉斯蒂涅初次與巴黎上流社會打交道的過程,充分展現出鏡中“他”的虛幻特征。在與雷斯托伯爵夫人見面的路途中,拉斯蒂涅“還是濺了一腳泥漿,他不得不在王家廣場上讓人給他的鞋子上光,刷凈他的褲子”,種種細節描述映射出他在社會階層跨越過程中的小心與無力。即便他盡可能地保持優雅,卻仍舊無法避免在現實面前的跌跌撞撞,如“泥漿”一喻,既指代現實中貧民區到貴族區的泥濘道路,也象征著社會階層之間的難以逾越。此外,拉斯蒂涅以為通過簡單的攀附,就能進入上流社會,但現實卻給了他沉重的打擊,在雷斯托府邸的尷尬處境以及最終被列入黑名單的結局,都說明一個道理:缺乏實力且沒有足夠的社會資本,僅憑一時的機巧,是無法在階層固化的社會中立足的。
雖然鏡像是虛幻的,但是“鏡中影像卻賦予嬰兒一種連貫的、協調一致的身份認同感……于是,嬰兒開始迷戀自己的影像……建立起一種欲望關系”(胡俐萍《拉康經典的鏡像理論對我的啟發》)。在6至18個月期間,鏡像所構建的理想化自我形象為嬰兒提供了一個穩定的身份認同基礎,由此嬰兒對鏡中自我產生迷戀,通過模仿和認同鏡中的自我,試圖在心理上獲得對身體控制感的想象性滿足。對于拉斯蒂涅而言,他的自我最初來源于想象,而想象又源于一切外在反射。他的自我就是在他者的投射中構建出來的,同時這也是他不斷靠近鏡中自我的過程。以下每一種欲望投射都是一種他者的印證,構建起拉斯蒂涅的自我。
首先,是鮑賽昂夫人的愛情欲望投射。她向拉斯蒂涅揭示社交界“真理”—“您只需把男男女女看成驛站的馬,把他們騎得疲憊不堪,每到一站您就可棄置不用”,她堅信金錢威力無比,勸誘拉斯蒂涅尋求與富有的紐沁根太太結婚,作為他攀升的墊腳石。她將拉斯蒂涅領入了一個將愛情視為驛站馬匹的巴黎社會,讓他見識了為金錢和地位可以輕易放棄真情的現實。
其次,是伏脫冷的斗爭欲望投射。他看透了拉斯蒂涅的野心與渴望,抓住拉斯蒂涅對財富與地位的向往來操控拉斯蒂涅。他直指法官之路的虛無,并向拉斯蒂涅灌輸他的人生觀和社會觀,試圖將拉斯蒂涅的道德底線推向極致,“倘若人們想撈些什么,就得玷污雙手,只要知道如何脫身便行了”。而后,針對拉斯蒂涅的貧困現狀,他提出一項具體的撈錢計劃,企圖用金錢的誘惑來徹底扭曲拉斯蒂涅的道德觀念。拉斯蒂涅雖然表面上拒絕了伏脫冷,但他的道德感與對成功的渴望之間展開了拉鋸戰。理智上傾向于堅持道德,然而內心深處的虛榮與對金錢的向往卻不斷糾纏著他。在伏脫冷的熏染下,拉斯蒂涅成了一個以利益為中心,根據形勢變化靈活調整目標的利己主義者。
(二)自我矛盾與掙扎
至此,拉斯蒂涅面臨著兩難選擇,一邊是沉溺于上流社會的繁華,另一邊是排斥虛偽與金錢的世界。這兩種選擇,折射出拉斯蒂涅內心的自我矛盾與掙扎,他的內心深處住著一個向往真實情感與理想的純真本我,然而社會的誘惑、他人的期望與評價,卻如同一股股暗流,不斷左右著他的選擇。
在這一過程中,拉斯蒂涅的自我在內外拉扯中發生著變化,其內心的復雜性也得以顯現。在故事的兩處關鍵流淚場景中,拉斯蒂涅對親情與真誠的渴望得以顯露。拉斯蒂涅在鮑賽昂夫人口中得知高老頭被女婿趕走的悲慘經歷,他的反應是“眼睛里滾動著幾顆眼淚”,對于親情之純粹向往與對于高老頭同情與震撼雜糅。這種情感的雙重性在他的內心激起強烈的沖突。拉斯蒂涅在此之前剛剛體驗過親情的美好,因此他無法對高老頭的遭遇無動于衷,這一遭遇也讓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家庭也在像高老頭支持女兒那般無私地支持著他。在這樣的對比之下,拉斯蒂涅的心靈受到極大的沖擊。但他最終難敵誘惑寫信向家人索取金錢,在書信完成后,他第二次落淚,“猶如獻給他的家庭祭臺上的最后幾炷香”,這幾滴眼淚象征著他在道德邊緣的掙扎。愧疚心成為最后一道防線。在各種外在因素的推動下,拉斯蒂涅的內心世界變得愈加矛盾和沖突重重。然而在內心深處,他依舊葆有純真和溫情,這份純真在某些時刻讓他落淚,也成了他自我構建中難以抹去的柔軟部分。
三、后鏡像階段—身份建構的完成
在后鏡像階段,拉斯蒂涅遭遇命運的抉擇,這一關鍵時刻成為其擺脫他人束縛、實現生存的唯一的希望。雖然三位對其欲望投射的人物最終以悲慘的結局收場,但他們已經助力拉斯蒂涅完成“鏡中形象”的構建。鮑賽昂夫人與伏脫冷的教導,他都完成得很好,高老頭的死亡在擊潰他最后一道防線時,又給予他一些額外的啟發—鏡中的“拉斯蒂涅”似乎在學業、愛情、金錢、地位和朋友等方面都取得了豐收,然而鏡中的“拉斯蒂涅”在成功的外表下是一顆冷漠的內心。為實現自己的夢想,他必須放棄許多良知,他的自我瞬間成長。最終,他選擇戴上面具,成為一個復仇的野心家。拉斯蒂涅的自我建構悲劇并非僅僅源自其個人選擇,更多的是由背后那個冷漠、充斥著金錢和欲望的社會所致。
在最后一章中,拉斯蒂涅表現出驚人的溫情,高老頭死前他盡心照顧并憤怒地去請雷斯托夫人,“他聽見歐也納的嗓音里帶著憤怒,不免暗暗吃驚”。他的憤怒滿溢以至于驚到了雷斯托伯爵。而后拉斯蒂涅為可憐的高老頭所做的種種都是極其善良的行為,他了解高老頭對女兒的愛意,發現西勒維想要拿走藏有兩個女兒頭發的鑲金邊的圓章時,再一次憤怒地制止了這一行為,并將其放到高老頭的胸口。這段描寫將年輕人的人性寫得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純真少年的突然回歸,也許是“死亡”前的回光返照,因為不久之后他就要變成一個新的拉斯蒂涅了。
下葬之后,拉斯蒂涅留下最后一滴眼淚,巴爾扎克此處的空間敘事極有意味。高老頭的遺體向下,眼淚向下,完成身份構建的拉斯蒂涅向上,不再屬于人間的純真熱淚也向上。這意味著他從老人的命運中看穿了這個世態炎涼的社會,對人與人之間的所謂正義、親情、友善等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于是他抱定決心,要以一個挑戰者的姿態殺進上流社會的角斗場。這不僅是對社會現狀的反思,更是對個人命運的重新定位。拉斯蒂涅的淚水不再僅僅是悲傷的符號,而是一種對純真的緬懷,一種對人性深淵的洞察。結尾處,拉斯蒂涅以憤怒的報復心態,向社會發出宣言:“現在咱們倆來拼一拼吧。”很多學者偏向將此處解釋為徹底地迷失了“自我”,但是筆者更偏向將此處解釋為一種憤怒的報復。它來自赤手空拳的年輕人,剛剛完成了有關巴黎的啟蒙教育,悲壯又驕傲地試圖報復這套冷血的規則。當社會階梯斷裂、不公現象泛濫,人的本性與社會性難免發生沖突。拉斯蒂涅選擇了社會性,放棄了本性,他不是失去良知,而是穿上了鏡中形象的外衣,其自我建構的悲劇性也正在于此。
基于此,拉斯蒂涅已完成身份的構建,盡管深知鏡中形象的虛假,但他仍不可避免地戴上面具,遵循社會規則,而這些規則讓他難以擺脫他人的期待。他的悲劇在于,盡管意識到這一選擇錯誤卻無法回頭,只能獨自承受著心理壓力和道德困境。在追求成功和社會地位的過程中,拉斯蒂涅不斷掙扎,試圖在滿足社會期望與保持自我之間尋找平衡,但這注定是無望的,因為他已深陷社會規則的羅網。最終,他在《紐沁根銀行》和《不自知的喜劇演員》等作品中,已晉升為貴族院議員、副國務秘書,并被封為伯爵,成為七月王朝的關鍵人物。
根據鏡像理論,拉斯蒂涅的自我構建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在前鏡像階段,拉斯蒂涅在外省鄉下,缺乏物質和誘惑的生活環境,使他的內心世界保持了一種原始的純良;在鏡像階段,他不斷受到他者的影響和投射,鮑賽昂夫人的愛情欲望投射、伏脫冷的斗爭欲望投射都對他產生影響,這些他者的投射為拉斯蒂涅的自我構建提供了基礎,同時也使他逐漸陷入矛盾掙扎之中;在后鏡像階段,拉斯蒂涅經歷自我反思和身份重構,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內心被虛幻的“鏡中形象”所控制。縱觀拉斯蒂涅整個自我建構的過程,無疑是一出悲劇。他以純真之姿來到巴黎,帶著全家的愛與希望攻讀法律,但逐漸在社會的誘惑和規則下失去了純真與愛。他認識到社會的不公平和復雜性,卻無法逃離這些規則。在高老頭死亡后,他選擇戴上面具,遵循生存法則,這種選擇既是對自己本性的背叛,也是對過去信念的摧毀。這一選擇是社會環境的產物,他的故事促使我們思考如何在現實社會中保持自我的人性和良知,尋找既順應社會規則又能維護自我價值的平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