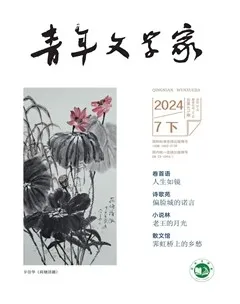走出群體之禮:“客游”的個性化書寫與詩人的集體選擇
自20世紀至今,漢魏時期“客”階層的變化問題一直為學界所關注。歷史學者多將目光對準漢魏時期的“客”階層,以期從中發掘漢魏時期的選官制度、社會流動、土地兼并等變遷。文學研究領域亦有所關注,具體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游士文學的研究與鄉愁文學的研究。在游士文學的研究中,學者往往結合時代背景、政治環境等對與“游士”創作相關的問題加以說明。但在鄉愁文學的研究中,學者對“客”身份的闡述較為籠統,缺少對不同時段下“客”身份特殊性的考量;不僅如此,“客游”中的復雜感情與詩歌的豐富內涵亦有待進一步闡釋,不能僅僅以“鄉愁”釋之。因此,學者需以一貫通視角,從社會歷史下“客”身份和內涵的變動看文學中“客”意象之發展。
本文選擇以漢魏詩歌中的“客”作為研究對象,根據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魏詩卷輯錄出提及“客”的詩篇,進行歸納整理、文本分析。文章將以跨學科視角,對這一時期文本中呈現的“客”意象作一番考究,并力圖探尋群體心理因素對文本生成的影響。
一、尚客之風與五禮體系下“客”的文學書寫
(一)“客”義的轉向與尚客之風
“客”字從“宀”從“各”,本意即為外來之人,《易經·需卦》中的“有不速之客三人來”即本于此也。但在此之后“客”的含義有所引申,在《周禮》系統中,當“客”與“賓”作為一對概念出現時,它們都是天子的客人,但其身份地位有差等。另外,《周禮·秋官》有“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客”在彼時是有著身份地位的專指的,即諸侯之臣。
諸侯之臣,其身份當為卿大夫士之流。然而在戰國時期,由于社會的動蕩與變革,這一階層有人開始為了所依附的統治集團的利益,四處奔走爭鳴,誕生了一批以縱橫家為代表的游說策士,養士納客成為一時風尚。“客”在此時,已漸漸從作為國君設禮的“賓客”,而逐漸成為與主人同謀的“門客”。僅從所指代的身份地位的內容而言,可謂“每況愈下”。
這種尚客之風至漢初仍有保留,譬如吳王劉濞、梁孝王劉武、河間獻王劉德、淮南王劉安等貴族階級周圍都集結了大批門人賓客,但此種風氣在漢武帝時期遭到打擊—“附益之法”限制賓客與諸侯的結合,又察舉制興起,賓客遂漸離私門,轉入國家政治體系中實施人生抱負,此后雖仍有養客之風暫起,然終究不復漢初盛況。
不獨社會上層有養客的俗尚,社會下層亦喜養客,《史記·魏公子列傳》提到:“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車騎過之。’”但侯生不過“大梁夷門監者”,實為微賤之職,卻仍然養客。由此可見,社會下層養客的要求并不高,主人不需要提供錦衣玉食的生活,很多情況是兩人以情義相交,主人以禮相待即可。因此可以說,尚客之風風行于當時社會各階層中。
(二)五禮體系下“客”的臉譜化文學書寫
漢魏時期的“客”是一個龐大的階層,囊括了政治、經濟領域的諸多群體,由于“客”群體指向的模糊性,漢魏詩歌中的“客”身份難以細究,但尚客之風的歷史景觀卻被保存其中。其中不乏體現待客之禮的內容,譬如漢代樂府詩《隴西行》中描寫了婦人見客、迎客、待客、送客之禮的詳細內容,其中的待客儀節是當時社會風情的展現。全詩重在描寫主人待客,因而有關“客”的正面描寫十分有限,只有“客言主人持”一句。結合全詩來看,此處主要是為了體現主客相互讓酒的恭敬守禮,是主人待客禮節的一環,故“客”的形象塑造并不豐滿。
《隴西行》以體現民風民俗為主,雖有待客的內容,卻并不算典型的宴飲詩。而考察宴飲詩中對待“客”的描寫,則可發現“客”的形象依舊單薄。筆者共統計出提及“客”的宴飲詩八首,以《于譙作》為例,“客”是背景板一樣的存在,與絲竹、舞蹈、佳人、珍饈、宮館的表現作用無二,都是為了體現主客宴飲之禮下盛大的場面。另外七首的寫作手法與《于譙作》類似,膳肴美酒、宮館佳人、弦歌雅舞在其中頻繁出現,“客”的形象也依舊單薄。究其原因,這種程式化的寫作與五禮體系下“客”的臉譜化書寫模式息息相關。
“禮”作為群體性的規定有其固定的儀節,而人與物都是執行儀節的一環。在此種程式下,個人的所思所想被模糊湮滅,取而代之的是群體所共同呈現的“禮”。從戰國至漢固然有尚客的風俗,但文學中對尚客的描寫卻以展現宴飲之禮為主。因此,在“禮”之下的“客”形象呈現出臉譜化,并無個人的風采與思想。
二、亂世文學中的漂泊羈旅之“客”
(一)動蕩時局與文學個體意識覺醒
在漢初相對安定的年代里,客的遠行是為了依托主人謀求衣食庇護與更好的政治出路,但當政局動蕩、自然災害頻發時,以百萬計的人民不得不輾轉他鄉以求生路,其間“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資治通鑒》)。在流亡的過程中饑寒交迫、夫妻離散是常有之事,甚至寇虜劫殺、暴死途中也在所難免。據有關學者統計,黃巾大起義到建安年間(184—220),戰亂引起的大規模人口遷移約有六次,單次流亡人數或多達百萬以上,此駭人之景成為漢魏難以磨滅的時代印跡。
對于當時的文人來說,即使未親身加入流亡的途中,也能感受到饑饉、寒冷、死亡的精神威脅。曹操在《蒿里行》中寫道:“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其正是戰亂分裂下對生命的挽歌。離棄故土、漂泊遠行乃至客死他鄉的行為使得時人展開對生命的思考,在詩歌中也大量出現光陰短促、聚短離長、世事無常、人情冷漠的感慨。這種對人生、人事、人情的思考感悟反映了漢人生命意識的覺醒。
(二)羈旅之“客”:個性化生命體驗與多樣化書寫方式
漢魏之際,亂世文學逐漸成為主流,大量羈旅之“客”在詩歌中涌現,其關注的重點在于“客”的個體感受,與五禮體系下的“客”書寫模式有較大區別,如“童童孤生柳”(《李陵錄別詩二十一首》其十七)開篇以比興作起,隨即將身份定位于“游客子”之上,亦由此生發情感。接著述及漂泊時的景象與悲情:夜時的寒風、嚴霜無一不喚起“我”的憂心,而晨間則感傷時光飛逝。一夜一晨,足見時間變化,從一朝一夕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想見在長時段的日夜交替循環中,縈繞排遣不去的是濃重的愁緒。而后俯仰之間,轉瞬則有“盛年行已衰”之慨。詩歌時間結構的變化與情感演變相配合,使得其別有韻味。
漢魏詩常以比興起句,隨后緊跟詩旨,上述“童童孤生柳,寄根河水泥。連翩游客子,于冬服涼衣”則如是。與此相類的還有《古詩十九首》中的“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以及曹植《盤石篇》中的“盤盤山巔石,飄飖澗底蓬。我本太山人,何為客淮東”等。以上“客”“游子”之屬多為詩眼,詩歌即由此展開—摹寫羈旅行役之苦,感慨離家日遠歸期未定,嗟嘆功業未成而時不待人。這樣濃烈的個體情感的表達,與五禮體系下臉譜化的“客”迥然不同。
除了情感表達與“賓主盡歡”之“客”有所不同,“客游”這一主題的書寫方式也呈現出多樣化。例如,孔融《雜詩》以亡子之悲和“客”的悲劇作為主暗線交織配合行文,足見作者的巧思;《李陵錄別詩二十一首》其十七探索了長短不同的時間間隔與情感變化相配合下的詩歌聲情轉換;《古詩十九首·青青陵上柏》以歡娛與凄惻的瞬時轉變,對比突出客子漂泊的陡然心境;樂府詩《陌上桑》移步換景鋪寫行路所見,借此體現軍旅之苦;曹植《門有萬里客行》以地名上的勾連,將“朔方”“吳越”“西秦”等相距萬里的廣闊地域凝練于幾句之內,對比之下可想見“客”生命中的奔波之苦。這些詩歌在結構上的安排都出于表情達意的需要,因此渾然無跡,為后人所推崇。可知“客游”這一主題因詩人個體生命體驗的不同而呈現出多樣化的書寫方式。
在五禮體系下的書寫模式中,“客”與“物”都是儀節呈現的一環。正因如此,文本的書寫呈現程式化的特點。而正是以上這些脫離了五禮體系下“客”形象,將“客”這一群體從原本臉譜化的書寫模式中解放了出來,轉而關注個體。這樣既豐富了“客”的意蘊內涵,展現人內心最真實樸素的情感,也讓文學繼續承載起現實生活。脫離了禮的禁錮,羈旅之“客”的情感、思想方見之于世,亦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其獨特面貌。
三、羈旅之“客”的集體選擇與集體認同
從“客”義本身來看,一直以來都存在兩種不同的指向,一種偏向“客”的本義,僅僅表示外來之人,并不強調身份;另外一種則是周禮之“賓客”、戰國諸侯之“門客”等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卿大夫士、策士群體。長期以來,前者的義項常為后者的光環所掩蓋。但是在大動蕩的東漢末年,代表漂泊羈旅,更近于前者義項的“客”隨著當時“亂世文學”演變為主流,被更廣大的文人所認同、接受。
文人對羈旅之“客”似存在一種獨特的情結。相比于五禮體系下受到尊重優待的“客”,人們在詩中反而更愛描繪羈旅之“客”。這種偏愛在漢魏詩中已肇其端,根據筆者統計,前者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僅收錄八首,后者約收錄有二十八首。雖然漢魏距今千載,文獻多有不傳,但是如此大的數量差距已足以說明問題,且文獻流傳本身也是偏好的體現。從藝術表現力上來看,五禮體系下“客”的書寫模式較為雷同;有關漂泊之“客”的文學書寫則將諸多古今相通的人事感悟與復雜情感融匯其間,聲情多變,其表現力遠非前者可及。
對于漂泊游子的“偏愛”進而形成的身份認同,其成因是多樣化的。
首先,從“客”義本身來說,“客”原義與引申義相比,身份上的限制較少。相應地,繼承其原義發展而來的漂泊之“客”留給文人的闡釋空間也較大—亂世之中的流民,羈旅之臣,游學游宦之人,都可以自稱為漂泊之“客”。對“客”的認定,并沒有身份上的諸多限制,而更多靠心理上的感同身受,因此更易使人形成一種身份認同,引起共鳴。
其次,漢魏時期存在大量的人口遷移現象,偏愛選擇書寫“更痛苦”的“客”,而非“賓主盡歡”的“客”,體現了文學反映現實的需要。而這一社會現象則因為大量的文學書寫凝結成一種文學記憶。更有套語的形成,如“客從遠方來,遺我xxx”“有客從x來”等“典型形式”,會將聽者一次次地代入類似的語境之中。漂泊流亡成為漢魏時期難以磨滅的時代印跡,這種文學記憶長期影響著后世文人的思維與選擇。相比較而言,五禮體系下的“客”作為一種記憶雖多被經史之文所保存,然而禮之下的“客”在詩歌上的文學表現實在有限。可以說,在文學中這兩種記憶之間的齟齬,因其感染力不同而呈現出前者逐漸為人所熟記,后者逐漸被淡忘的狀態。此后在詩歌中雖依舊存在宴飲之禮下的客,然而更多是應時而作,并非出于集體認同形成后表情達意的需要。可見漂泊客游的文學記憶對于后人集體認同之意義。
最后,羈旅之“客”的文學書寫中隱含了文人的某些心理期待。以漢魏詩為例,“客”對于時人而言,是一份痛苦的記憶,對“客”困苦心態書寫的背后,是對更安居樂業的社會的向往。文人在亂世中渴望安定和平的生活,在盛世之中則期待施展抱負,建立功勛。但倘若背井離鄉的選擇并沒有使自己取得世俗上的成就,乃至遭受貶謫,失意文人則將自己滿腹牢騷付諸“客游”的詩歌書寫中。孟子以為:“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文人在表達客游中的牢騷與失意時,也暗含一種否極泰來式的期待。譬如阮瑀《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全篇正是分為兩個部分—漂泊之“客”與宴飲之“客”。此詩雖是阮瑀“述恩榮”之作,卻也直觀地寫出了詩人的心理:在漂泊輾轉中磨礪身心,以期由困苦走向光明之路。
漢魏詩歌中“客”的書寫變化不僅體現了社會歷史的動蕩,更體現了文學創作在這一時期的發展,展露出人文關懷的光輝。不同于前代詩歌中“賓主盡歡”之“客”形象的呈現,漢魏詩中的羈旅之“客”是“客”本身的雙重義項在漢魏之際的一個集體選擇與集體認同的結果。在此之后,“客游”的文化記憶長期影響人們的思維。對漂泊之客的認同與偏愛是詩人復雜心理的體現,詩人傾向于摹寫客游之苦,從某種層面上也折射出其對更和平安定生活的追求,以及否極泰來式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