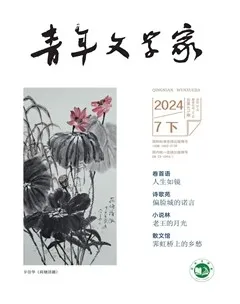先秦“詩”的內涵變遷與以“和”為美的審美心態
“和”在中華文化中是一個極重要的美學范疇,它包括審美主體在審美活動中所體驗的“和”以及客觀對象內涵的“和”。前者與審美主體所獲得的美感相關,后者則與審美對象有關。“詩”作為審美客體,蘊含了能引起美感的構成因子;同時,“詩”在先秦時期的內涵演變,會使審美主體的身份發生變化。本文主要通過對先秦時期“詩”的內涵變遷,進一步探討其背后的以“和”為美的審美心態。
一、先秦“詩”的內涵變遷
“詩”字晚出,在甲骨文、金文中未見記載。在先秦時期,“詩”字最早出現在《尚書》《詩經》中。鄭玄依托《尚書》中“詩言志”的記載,認為“詩”大概起源于虞舜時期。但根據目前學術界的普遍認識,記錄這段“虞廷禮樂”的《尚書》為后人偽作。此外,從邏輯學的角度來看,“詩”作為“詩言志”的理論主體,其出現必然早于“詩言志”這一文學觀念的生成。于是,《詩經》所載的詩成為最可靠、最古老的詩了。而我們所要探討的并非某一既定詩篇,而是先秦時期“詩”這一普遍概念的具體內涵。
“詩”在《詩經》當中也只出現三次:
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小雅·巷伯》)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大雅·卷阿》)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大雅·崧高》)
以上三例中,詩、歌、誦交替出現,如“凡百君子,敬而聽之”“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可見詩是用來聽,用來唱的,從這可以看出早期詩與歌結合的特征。除此之外,從著名的“詩言志”理論,也能看出這一特點。雖然記錄“詩言志”文學觀念的《尚書》被證偽,但依據目前學術界普遍的觀點來看,“詩言志”觀念的產生大致在西周早中期,與《詩經》成書年代大致相同。《尚書·舜典》記載了舜命夔典樂:“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于!予擊石附石,百獸率舞。’”“詩”在此時并不是后來所認為的一種文學體裁,而是詩、樂、舞三者緊密結合的一種藝術形態。同樣,在《詩經》中,詩總是與歌、誦同時出現,說明詩、樂還未分家,詩和樂結合在一起來抒情達意。可見至少在周代的時候,“詩”體現出詩、樂、舞三位一體的特性。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詩與樂逐漸分離。春秋時期的“詩”,多與“賦詩”等活動相關。人們在外交場合中賦詩,常體現出斷章取義、迎合己意的特點。例如,子太叔賦寫男女私情的《野有蔓草》,截取其中符合自己心意的“邂逅相遇,適我愿兮”來表達對趙孟的歡迎。可見在賦詩活動中,賦詩人大多不管詩的原意,而只取詩的字面意義。雖然賦詩活動中也會合樂,但顯然人們更關注的是“詩”中的語辭文字意義,通過字面意義理解,截取符合自己心意的“詩”。這種情境下的“詩”,雖然合樂,但實際上已經與樂、舞相分離。前者作為權威范本用于貴族教育與禮樂學習,而后者則用于交際。
孔子時,《詩經》已經基本定型。《論語》中孔子及其弟子提及“詩”共十四次,其中僅一處不指《詩經》,即“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由此我們可以得出許多重要信息:一是“詩”大致等同于定型的《詩經》;二是詩、樂分家,原本詩所包含的音樂性被剝離開。孔子所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堯曰》),而非“不學詩,無以吟/唱/詠”,以及“《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而未提及與聽覺感官有關的功能。所以,此時“詩”所指涉的是剝離了樂、舞的,已基本定型的《詩經》文字篇籍。
孔子之后,尤其是進入戰國時期之后,“詩”的內涵繼續擴充。除了《詩》與“逸詩”之外,逐漸出現將自己的作品稱為“詩”的現象,如屈原《九歌》中的“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以及《九章》中的“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顯然,屈原這里所指的“詩”與《詩經》無甚關聯。
在對先秦各時期“詩”的內涵進行梳理后,不難發現,“詩”與《詩經》密切相關,但“詩”卻不完全等同于《詩經》,其演變路徑大致可以總結為:從范圍上來說,“詩”的內涵不斷擴大,慢慢跳脫出《詩經》體系,逐漸涵蓋文體意義上的“詩”;從表現形式上來說,由詩、樂、舞結合的藝術綜合體脫離出來,逐漸偏向文字篇章和語辭意義。而“詩”作為審美客體,其具體內涵及表現形式對主體的審美感受與心態有著重要影響。
二、“詩”與“樂”互動中的“和”
人類初期的審美活動與觀能感受密切相關,因此,審美對象的狀態如何,對人的審美感受以及整個審美過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詩”原屬于“樂”的范疇,這是有跡可循的。《呂氏春秋》中有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其中原始先民所歌的“八闋”之歌詞,便有可能是當時之“詩”。這就體現了上古時期詩、樂、舞一體的原始狀態。朱光潛在論述人類詩歌的起源時,從人類學與社會學的角度切入,也得出“詩歌與音樂、舞蹈是同源的”這一結論。從《尚書》中所記載的“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詩論》)來看,在“詩言志”觀念產生的時代,這種詩、樂、舞三位一體的形態依舊保持著。但需要注意到的是,雖然此時詩樂一體,且具有內在的統一性,但樂應當是居于主導地位的。舜命夔典樂,這個“樂”的系統當中就囊括了“詩、歌、聲、律”,它們各自所承擔的功能有所不同。“詩”大概就屬于樂章,依附于樂才能體現出它的價值取向。因此,在先秦詩、樂、舞還未分家時,將“詩”作為審美客體,實際上就是將“樂”作為審美對象。
從舜命夔典樂的目的來看,最終是要達到“八音克諧”的目的。其中“克”“諧”與五行、八卦密不可分。五行講求相生相克,八卦又有陰陽之分。尤其是陰陽二氣,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國語·周語》中記載伶州鳩所說的話:“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說明陰陽本身有著其內在秩序,雙方和諧統一的時候,大自然就是和諧的。《國語·周語》中還記載伯陽父所說:“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若是陰陽失序,則社會自然都會陷入混亂。可見當時的人已經認識到了,天地自然的和諧正是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生存狀態。
通過宗教祭祀等活動來祈求上天澤被,實現“神人以和”,而“樂”與宗教祭祀密切相關。音樂作為調和陰陽、天人的中介,人們對于“和”的追求亦同樣體現在“樂”上。《國語·周語》記載,周景王追求編鐘的極致音高,單穆公言:“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單穆公此語便是為了說明,美感的產生須達到“聽和”與“目正”。“樂”作為審美對象,只有達到了“和”才能使審美主體獲得良好的審美體驗。當“詩”還未與“樂”分離,只作為“樂”的一部分而存在時,“和”必然成了“詩”的內在要求。
“詩”與“樂”的分流在春秋時期就可見端倪。到孔子時,“詩”基本指涉《詩經》的文字篇籍。上博簡《孔子詩論》當中對《詩經》中的一些具體篇章進行論析。第十簡中,孔子以一字論詩:“《關雎》之怡,《樛木》之時,《漢廣》之智,《鵲巢》之歸,《甘棠》之報,《綠衣》之思,《燕燕》之情,曷?”可見,孔子大多是以“情”作為討論《詩經》的出發點。以《關雎》為例,《孔子詩論》中是這樣進行論述的:“《關雎》以色喻于禮”—《關雎》是用愛情來說明禮義;“情愛也”—《關雎》是一首愛情詩;“《關雎》之怡,則其思益矣”—《關雎》書寫和諧,主要是通過它是如何表達思念之情的;《關雎》如何以色喻禮?在這里,孔子承認了《關雎》愛情詩的性質,并以“怡”一字為其定性,用以表達婚姻的和諧。《關雎》為何“怡”,原因則是“終而皆賢于其初者也”,則說明前面是不太和諧的。最初,對淑女的思念十分強烈,然而求之不得,故而不和諧(失落);而后以琴瑟、鐘鼓來禮敬淑女,合乎社會規范,則愉矣。前面是“發乎情”,后面則是“止乎禮義”,即“終而皆賢于其初者”。可見孔子論詩,講求“感性”與“理性”的中和,以“情”發微,而后考察作品之情感是否合乎禮義,在充分肯定個體情感體驗的同時,也關注“義”對情的約束。這種情不單純是指原始的情感體驗,而是經過了理性滌清的情感。
三、“詩”與審美主體身份的演變探索
上文我們從“詩”的表現形式,對主體的審美心態進行了討論。而在“詩”內涵不斷變化的過程當中,審美主體的身份也在不斷改變。當“詩”的內涵未跳出《詩經》之體系,審美主體主要包括了用《詩》者與學《詩》者。
《詩》如何用?這主要與我國由來已久的“詩教”傳統有關。“詩教”一詞最早出于《禮記·經解》:“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孔穎達《禮記正義》對此解釋:“《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詩經》中的詩大多不出于諷頌目的,但無論諷頌與否,均以獻詩的這樣委婉含蓄的方式勸誡君王。“溫柔敦厚”大致就是指的這種風度。
實際上,詩教傳統大致可以追溯到周代。從舜命夔典樂的材料來看,“樂”的目的是“教”,“教”的對象是“胄子”,“教”的內容是“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即培養“胄子”的理想性格,這種性格便可以理解為是一種溫柔敦厚的“和”的理想狀態。
孔子用《詩》也體現在將《詩》作為教育的范本。“詩教”是孔子文學思想的核心。從《陽貨》篇中的“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來看,孔子認為,“詩教”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對國家政治的理想建構,這與西周時期是一脈相承的。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要注重對社會中個體的培養,即修身,將個體的內在修養轉化為內在的道德實踐,即“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然后進入到群體性的社會倫理道德層面,以至于最終達到重建社會秩序的目的。
在孔子這里,“詩教”與個體修身成為君子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詩教”,使一個自然人成為一個具有社會屬性的人,即“文質彬彬”“和而不同”的君子,這與典樂教胄子是一樣的。
當“詩”的涵蓋范圍不斷擴大,逐漸涵蓋《詩經》體系之外的文體之“詩”,其審美主體除了用《詩》者、學《詩》者之外,還將詩歌的創作者涵蓋在內。《詩經》中雖未言及創作者,但有關于詩歌創作的地方共有十二處,可見當時的人們已經萌發了詩歌創作的意識,只是創作者還未真正走到臺前,隱匿在群體之中。《詩經》創作的表現手法我們稱之為“賦、比、興”,按朱自清的說法來看“比興”是詩論上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之一。鄭玄注《周禮·大師》:“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實際正是《詩》教“和”的內在蘊含。鄭玄在《毛詩正義》中釋比興,“比者,比方于物”,“興者,托事于物”。胡寅《斐然集》中記載李仲蒙語:“索物以托情,謂之‘比’,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當時的詩歌創作,已經十分關注物與我之間的關聯。在這里,物(自然)與人之間并不是對立起來的,反而是和諧共生的。只有當外界與我達到和諧的狀態,才能以物來觀照內心世界。
戰國后期,文體意義上的“詩”出現,創作者走到臺前,詩歌創作變得私人化。屈原以蘭花香草喻己,作詩表達一己之情,這種以物觀我的表現手法一直延續,并影響后世的詩歌創作。可見在先秦時期,先民們早已具備了天人合一、物我相照的“和”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