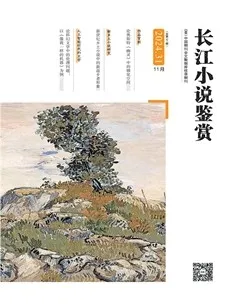庾信《擬詠懷二十七首》的時間意識和情感內(nèi)涵
[摘 要]《擬詠懷二十七首》體現(xiàn)出庾信濃郁的時間意識。時間的單向流動性使得庾信長期置身于動亂與不幸之中,體驗著人生不同階段之間的巨大反差。詩人從客觀世界與個體生命兩個角度觀察到時間的特性與影響,認識到世事滄桑、人生無常,并將其與私人情感聯(lián)系起來,形成《擬詠懷二十七首》獨特的“情感時間”書寫。
[關(guān)鍵詞]庾信" "《擬詠懷二十七首》" "時間意識" "情感內(nèi)涵
庾信在《擬詠懷二十七首》中描寫的相關(guān)時間體驗,是生命個體在歷經(jīng)家國與個人種種不幸后,主觀世界對創(chuàng)傷經(jīng)驗的加工與折射,也是特定時代的士人群體的普遍感受。
《擬詠懷二十七首》作為詩人吟詠情感的作品,詩作中有關(guān)時間的描寫自然攜帶時代特征與生命印記。而這種時間意識的流露,正是因為庾信繼承了魏晉詩歌的生命主題,以文字的方式將自己在時間之流中產(chǎn)生的世事滄桑、人生無常的悲哀以及生命徒耗、年華虛擲的苦痛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
一、《擬詠懷二十七首》對時間的呈現(xiàn)
時間作為一個哲學(xué)概念,指物質(zhì)運動的持續(xù)性、順序性,并具有絕對的客觀實在性。
客觀世界的局勢變化遵循一定的規(guī)律,在時間的推移與影響下,當量變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事物就會產(chǎn)生瞬時的變化。庾信《擬詠懷二十七首》中以“初”“遂”“始”“忽”“一旦”“猶”“已”“正”等副詞來描繪突如其來的變化,示例如下:
長坂初垂翼,鴻溝遂倒戈。(《擬詠懷·其八》)
梯沖已鶴列,冀馬忽云屯。(《擬詠懷·其十二》)
大道忽云乖,生民隨事蹇。……平生幾種意,一旦沖風(fēng)卷。(《擬詠懷·其十四》)
六國始咆哮,縱橫未定交。……折骸猶換子,登爨已懸巢。壯冰初開地,盲風(fēng)正折膠。……楚師正圍鞏,秦兵未下崤。(《擬詠懷·其十五》)
尋思萬戶侯,中夜忽然愁。(《擬詠懷·其十八》)
倏忽市朝變,蒼茫人事非。(《擬詠懷·其二十一》)
這些詩句所指涉的皆是“大道”“人事”這類宏觀的對象,大多與政治局勢、戰(zhàn)爭情況有關(guān)。動蕩驟變的社會環(huán)境給人帶來巨大的斷裂感,刺激并強化了詩人對時間的感受力。對庾信來說,身份地位急轉(zhuǎn)而下、百姓水深火熱、家國危在旦夕等多重打擊突然到來,而他不得不接受身邊的一切幸福正在以極快的速度轉(zhuǎn)向不幸。
置身其中的庾信對突發(fā)不幸的感知卻是持續(xù)的,這種持續(xù)性表現(xiàn)為時間在指定長度內(nèi)按照規(guī)律單向流動。《擬詠懷二十七首》通過使用“不復(fù)”“從此”“無復(fù)”“由來”“平生”加以表現(xiàn),示例如下:
由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擬詠懷·其一》)
壯情已消歇,雄圖不復(fù)申。(《擬詠懷·其五》)
恨心終不歇,紅顏無復(fù)多。(《擬詠懷·其七》)
懷秋獨悲此,平生何謂平。(《擬詠懷·其九》)
李陵從此去,荊卿不復(fù)還。(《擬詠懷·其十》)
始知千載內(nèi),無復(fù)有申包。(《擬詠懷·其十五》)
殘月如初月,新秋似舊秋。(《擬詠懷·其十八》)
懷抱獨惛惛,平生何所論。(《擬詠懷·其二十五》)
出門車軸折,吾王不復(fù)回。(《擬詠懷·其二十七》)
庾信以一句“平生何謂平”來評價自己的人生。在個人漫長的不幸中,“壯情”與“雄圖”隨著時間的流逝變成一種對歸鄉(xiāng)無能的“恨心”。個人得失之外,動蕩的時局中庾信始終不見如申包胥、李陵、荊軻這樣的人物。“千載”“從此”“無復(fù)”諸詞雖有夸張成分,卻反映了庾信無處求助的心態(tài)。
由于時間是一維的,具有單向流動性,因此不同的時間點有前后之分。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庾信前后兩階段人生形成了巨大落差,今昔對比也是庾信在《擬詠懷二十七首》中呈現(xiàn)時間的方式之一,示例如下:
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悲傷劉孺子,凄愴史皇孫。無因同武騎,歸守灞陵園。(《擬詠懷·其六》)
空營衛(wèi)青冢,徒聽田橫歌。(《擬詠懷·其八》)
昔嘗游令尹,今時事客卿。(《擬詠懷·其九》)
智士今安用,思臣且未聞。(《擬詠懷·其十三》)
千年水未清,一代人先改。昔日東鄰侯,唯見瓜園在。(《擬詠懷·其二十四》)
庾信主要是從兩個時間維度上書寫今昔的不同。一方面,庾信從個體生命前后對比的角度,訴說國士待遇與羈留敵國的尷尬處境之間的落差。另一方面,庾信將時間跨度進一步拉長,借助歷史上的英雄人物與僅可追念的歷史遺址,抒發(fā)內(nèi)心的無力與絕望。
時間的存在,主要以四季更替或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輪回等形式被人們感知。在詩作里,庾信尤愛“日暮”“夕”“夜”“曙”“晨”“殘月”“秋”“衰槐”等意象,并通過巧妙組合,使這些時間意象具備某種象征意義或營造出特定意境,示例如下:
搖落秋為氣,凄涼多怨情。……直虹朝映壘,長星夜落營。(《擬詠懷·其十一》)
流星夕照鏡,烽火夜燒原。(《擬詠懷·其十二》)
日晚荒城上,蒼茫余落暉。……陣云平不動,秋蓬卷欲飛。(《擬詠懷·其十七》)
殘月如初月,新秋似舊秋。(《擬詠懷·其十八》)
獨憐生意盡,空驚槐樹衰。(《擬詠懷·其二十二》)
秋風(fēng)別蘇武,寒水送荊軻。(《擬詠懷·其二十六》)
通過所舉詩句不難看出,庾信對于時間意象的選取和呈現(xiàn)大多聚集于光線暗淡的時刻、衰颯的時節(jié)和景物。《文心雕龍·物色》以“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矣”[1]一句指出,自然景物的變化影響著文人的情感變化。荒城日落暗示著南梁國運氣數(shù)的衰落;衰敗的槐樹既暗示作者自己,又代表著由南入北的羈旅詩人的生命力。庾信對冷色調(diào)、破敗之物、凄涼之景的偏愛,正是其悲慨蒼茫之氣的原因之一。
二、《擬詠懷二十七首》的時間體驗與情感內(nèi)涵
魏晉六朝以來,詩學(xué)對時間的探討不斷深化。《擬詠懷二十七首》中時間描寫的創(chuàng)作邏輯為:客觀時間作為動力,影響著事物的繁榮衰落。隨著客觀時間流動,“作為時間觀照者的人以一種情感化或情緒化的方式去打量時間,時間帶上了主觀的情感色彩和心理化特征”[2]。因此,人對時間長短、流速快慢的感知也會有所不同。
1.世事滄桑、人生無常的客觀時間體驗
庾信自幼文采出眾,深受統(tǒng)治者賞識。據(jù)《周書·庾信傳》記載,“子山父子,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3]。但世事無常,侯景之亂、江陵陷落、羈留北地等種種變故顛覆了他的人生,客觀時間強化了他對創(chuàng)傷的感知能力。《擬詠懷二十七首》正是庾信羈留北地時有感于客觀時間、咀嚼個體創(chuàng)傷經(jīng)驗的產(chǎn)物。田曉菲定義道:“創(chuàng)傷具有雙重的時間性,既屬于過去又存在于此刻。而在創(chuàng)傷寫作中,記憶被一次又一次地喚回并且重構(gòu)。庾信處理創(chuàng)傷的方法是不斷地召回自己的文本記憶。每次它們出現(xiàn)在寫作中時,庾信都會在此基礎(chǔ)上重現(xiàn)對這些文本的記憶。”[4]
客觀時間在庾信記憶空間中發(fā)生了扭曲,不斷的記憶喚回使得庾信不同記憶空間的時間體驗,在此刻的時間中產(chǎn)生交織,并得到重塑與加固。在《擬詠懷·其十七》中,庾信選用了“晚”“落暉”“秋蓬”“今年”這四個與時間有關(guān)的詞語,以黃昏落日的姿態(tài)、搖搖欲飛的秋天蓬草,暗喻南梁所剩無幾的國運氣數(shù)。《擬詠懷·其十一》借宋玉《九辯》中“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5]為靈感源泉,引出西魏蠶食梁朝益州等國土的時事。而在《擬詠懷·其六》中,庾信回憶起昔年南梁故主的賞識,因此更為如今自己的貳臣之身感到悲傷。作為同一主題的表達,《擬詠懷·其二十四》中,庾信從“歷史時間”中借東陵侯邵平的典故隱喻自己的生平,反映其身處異地,不甘屈節(jié)的精神寄托。《擬詠懷·其九》則借用了今昔對比的方式,將不同的時間點串聯(lián)起來,以“昔嘗游令尹,今時事客卿”表露出深沉的懺悔思想。庾信在詩中反復(fù)回憶南梁的傾頹之勢、自己的貳臣之身,正是因為他一直受困于世事滄桑的變局之中,久久不能抽離。
為求從痛苦中解脫,庾信形成一套復(fù)古的歷史思維模式,不論是“智士今安用,思臣且未聞”(《擬詠懷·其十三》)抑或“始知千載內(nèi),無復(fù)有申包”(《擬詠懷·其十五》),皆是庾信強有力的控訴和渴求。但在單向流動的時間結(jié)構(gòu)中,時間無法回溯,故庾信想要從復(fù)古的角度追憶過去以實現(xiàn)對當下苦痛的超越,也只會落入人力所不及的無可奈何。
2.生命徒耗、年華虛擲的“情感時間”書寫
庾信有限的生命經(jīng)歷了過多的跌宕起伏,體會過“國破之傷慟,羈旅之愁苦”[6]的復(fù)雜情感,對客觀時間的體驗最終化作了“情感時間”的書寫。生命的短暫與歲月的無情是人類始終需要面對的永恒話題。“衰老和死亡是時間的性相,時間是一切事物的秉性,當然也內(nèi)在于生命本身。”[2]作于晚年的《擬詠懷二十七首》,明顯表現(xiàn)出庾信“嘆老”的心態(tài)。詩中不僅有“自憐才智盡,空傷年鬢秋”(《擬詠懷·其三》)這類直白的感傷,也有如“獨憐生意盡,空驚槐樹衰”(《擬詠懷·二十三》)這類以樹自況的含蓄表達。庾信借“枯木”移根異地后的枯萎狀態(tài)來表示自己的現(xiàn)狀以及憂愁,時間在客體生命的終結(jié)過程中顯露出來。不可抗拒的衰老讓庾信陷入了另一種思想困境,即有限生命被白白消耗的痛苦與無力。
客體生命的終結(jié)引起了庾信的時間焦慮。在“情感時間”的書寫中,庾信將焦慮融進客觀時間,以文字的方式使客觀時間成為私人化的情感表達。這種心境在《擬詠懷·其十八》中表現(xiàn)得格外明顯。庾信提筆一句“尋思萬戶侯,中夜忽然愁”,“中夜”與“忽然”既點出愁緒來臨的具體時間,又指明庾信對此毫無準備。因為毫無準備,愁緒的強度與容量才難以化解。庾信不斷變化空間試圖驅(qū)趕煩惱,因此便有了“書卷滿床頭,琴聲遍屋里”,他試圖以高密度的行動填補時間流逝帶來的龐大焦慮與空虛,以尋求時間存在和個人存在的意義,卻反被時間所制。在無力中,庾信敏感地注意到時間并沒有給“月”與“秋”帶來變化,“殘月如初月,新秋似舊秋”。時間看似無情,因為時間的單線流動性使它不會因為人的主觀意愿而更改流動速度。但“月”與“秋”這兩樣自然事物卻豁免于時間的控制,自然的無限性與人生的有限性形成了巨大反差。兩相對比下,生命個體的渺小以及年華虛擲的情感體驗自然在詩人筆下噴涌而出。
三、《擬詠懷二十七首》時間意識突出的原因
1.功業(yè)意識與創(chuàng)傷經(jīng)歷的刺激
庾信在《擬詠懷二十七首》中表露出的時間意識,與他的功業(yè)意識和創(chuàng)傷經(jīng)歷密不可分。蕭梁王朝一夕敗亡的現(xiàn)實悲劇激發(fā)他對歷史和現(xiàn)實作出深刻的反思,儒士的社會責(zé)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重新喚起他強烈的功業(yè)意識。入北后的庾信愈發(fā)看重自我價值并自覺將自我融入現(xiàn)實之中。庾信在“空營衛(wèi)青冢, 徒聽田橫歌”(《擬詠懷·其八》)中引用衛(wèi)青和田橫的典故,反思自己既不能如衛(wèi)青般征戰(zhàn)沙場,又不能學(xué)田橫五百壯士以死殉國,表露出功業(yè)未就的無力感,流露出希望建立不朽功業(yè)的理想追求。與此同時,庾信也清醒地認識到南梁已經(jīng)滅亡,自己一介飄零之身羈留北朝已成定局。對于當下無法南歸的他,若想實現(xiàn)功業(yè),在北朝安身立命無疑是最好的選擇。根據(jù)魯同群先生研究北朝史和分析庾信詩賦的結(jié)果,“庾信在北朝的仕宦實際上并不得意;不僅如此,他入北之初的政治處境和生活境況還相當惡劣”[7]。此時的庾信已經(jīng)年過半百,但離成就功業(yè)卻仍有很長一段距離。現(xiàn)實的尷尬處境和內(nèi)心的理想追求讓庾信不得不暫時壓抑下至死不能泯滅的鄉(xiāng)關(guān)之思,轉(zhuǎn)頭侍奉北朝。正是國破家亡的經(jīng)歷、功業(yè)的無望使得他深刻地體驗到年華的虛度,從而更感時間流逝帶來的悲哀。
2.魏晉詩歌生命主題的承繼
古代文學(xué)作品中有不少涉及對生命主題的探討,漢樂府與《古詩十九首》中就有很多例子。魏晉詩歌繼往開來,以文人的敏感鋪開了對生命主題的探討。受時代影響,漢魏之際的詩歌充斥著人生短暫的慷慨悲涼,曹操在《短歌行》中發(fā)出感慨,“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8]。曹丕《善哉行·其一》也有相似感觸,“人生如寄,多憂何為?”[9]此時文人對生命的思考仍聚焦于個體在客觀世界中的位置。正始時期,司馬氏的實質(zhì)統(tǒng)治壓迫著士人,士人在精神的自我克制中,承受著時間流逝帶來的苦悶沉郁,為生死主題添加了更多有關(guān)時間的哲學(xué)思考。阮籍在《詠懷詩八十二首》以“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10]書寫苦悶孤獨,以“朝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10]感慨時光易逝,以“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10]嘆惋世事無常。兩晉以降,詩歌風(fēng)格與前代相比又有所不同。西晉文人側(cè)重關(guān)注詩歌形式技巧,于是文人在面對生命命題時的筆觸更加細膩,對于內(nèi)心情感的挖掘更加深入,西晉詩人潘岳在代表作《悼亡詩·其一》中,關(guān)注到了時間給自然物象帶來的變化,以“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11]開篇,低回委婉地抒發(fā)了喪妻后的悲痛心情。東晉陶淵明表現(xiàn)則更為超脫,其《擬挽歌辭三首·其一》中“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12]看淡了對死亡的恐懼與焦慮,指明生命無長短之別,在生命主題的探討上又有所升華。而庾信憑借著個人敏感而獨特的體驗,感嘆時光短暫與世事無常,自然承繼了魏晉詩歌中關(guān)于生命主題的情懷。
四、結(jié)語
時間意識作為庾信《擬詠懷二十七首》的一個側(cè)面,反映了庾信認識客觀世界、個體生命的思維方式。在單向、綿延的時間之流中,由南入北的生命軌跡賦予庾信獨特的時間體驗,庾信在動亂中的矛盾掙扎、悲哀失落代表了亂世士人群體的普遍遭遇與情感內(nèi)核。故在《擬詠懷二十七首》中,庾信一改以往奉和、應(yīng)制之作的綺艷流麗,轉(zhuǎn)從以時間為載體抒發(fā)個人情感,從客觀世界與個體生命兩大維度思考政治局勢變化的外在表現(xiàn)與內(nèi)在原因,吟詠個體生命的焦慮與無力,以感傷的語調(diào)表達細膩的情感變化。而從詩歌的發(fā)展角度來看,庾信繼承并發(fā)展了魏晉詩歌中對生命主題的思考,改變了注重感官刺激的創(chuàng)作習(xí)慣,也為文學(xué)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1]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8.
[2] 詹冬華.中國古代詩學(xué)時間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4.
[3] 令狐德棻.周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1.
[4] 田曉菲,寇陸.庾信的“記憶宮殿”:中古宮廷詩歌中的創(chuàng)傷與暴力[J].上海大學(xué)學(xué)報,2017(4).
[5] 洪興祖.楚辭補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6] 許東海.庾信生平及其賦之研究[M].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
[7] 魯同群.庾信在北朝的真實處境及其鄉(xiāng)關(guān)之思產(chǎn)生的深層原因[J].南京師大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1990(1).
[8] 曹操.曹操集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79.
[9] 曹丕.曹丕集校注[M].合肥:安徽大學(xué)出版社,2009.
[10] 阮籍.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
[11] 潘岳.潘岳集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12]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
(責(zé)任編輯" 夏" "波)
作者簡介:陳自意,福建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文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