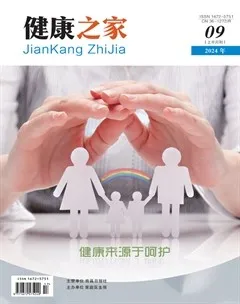基于“器官親和性”論述癌癥轉移相關
摘要:轉移是癌癥最具有破壞性的階段,是導致癌癥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癌癥轉移到特定的器官中,可以被稱為“器官親和性”,研究其特定機制、抵抗腫瘤微環境的不利因素,有利于控制癌細胞增殖、侵襲、轉移,從新的思維角度解決癌癥轉移問題,提高癌癥患者生活質量,延長其生存周期。中醫有“傳舍”理論,從各臟器間獨特關系論述“癌毒”的傾向性,與“器官親和性”相一致。中西醫薈萃結合,可拓寬癌癥轉移的診療思維。主要基于“器官親和性”論述癌癥轉移相關,為臨床診療提供參考。
關鍵詞:癌癥;器官親和性;腫瘤微環境;轉移;中醫藥
癌癥病因復雜多變,早期起病隱匿,晚期進展快,容易復發、轉移,成為威脅人們健康的一大“殺手”。轉移是癌癥進展中最具有破壞性的一環,是導致死亡的重要原因。臨床觀察到癌癥容易轉移到特定的器官上,這一“器官親和性”模式受不同因素影響。鑒于此,對轉移癌細胞機制進行剖析,發現癌癥轉移路徑與腫瘤微環境的變化相關,闡明潛在機制,使患者在治療策略與目標方面獲益。
1 器官親和性淺析
“種子—土壤”假說理論認為,種子“癌細胞”與土壤“腫瘤微環境(TME)”具有相關聯,強調這些器官的內在特性及宿主器官的獨特細胞,轉移遵循了非隨機化的模式。腫瘤轉移器官親和性是指不同的腫瘤傾向于特定的器官轉移,原發腫瘤向何種器官轉移難簡單的解釋為血行轉移、淋巴轉移、播散轉移,如肺和肝的血流充足,有時卻未發現腫瘤轉移。此外,骨是腎癌、前列腺癌等特異性的腫瘤轉移親和性器官[1]。基于器官親和性理論,進一步深入對腫瘤微環境的認識,了解不同器官的轉移路徑,裨益于防治癌細胞對傾向器官轉移,從而精準預測疾病發展,指導臨床治療方案的制定。
1.1 胰腺癌肝轉移
胰腺癌是消化系統常見惡性腫瘤,多為胰腺導管癌,早期不易被發現,且起病隱匿性,早期缺乏典型臨床癥狀,導致大多數患者在轉移后才被診斷出來[2~3]。針對胰腺導管癌轉移器官的調控,肝轉移的器官親和性依賴于P120連環蛋白,P120和E-鈣黏蛋白之間的合作相互作用[4]。單等位基因的P120連環蛋白丟失,可加速驅動胰腺癌肝轉移的形成,雙等位基因P120連環蛋白丟失,消除了胰腺癌細胞肝轉移能力[5]。胰腺癌細胞傾向于肝臟轉移,由于胰腺癌發病隱匿,臨床上可以通過腹脹、腹水、黃疸等肝癌癥狀深入探尋原發腫瘤部位。
1.2 結腸癌肝轉移
結直腸癌好發轉移部位是肝臟,有25%~30%的患者同步發生轉移[6]。結直腸癌肝轉移形成機制與腫瘤、腫瘤相關微生物群有關,腫瘤駐留細胞大腸桿菌誘導腸道血管屏障(GVB)破壞,促進腫瘤細胞血行播散至肝臟[7]。此外,結直腸肝轉移還與腫瘤干細胞、黏附分子、細胞外基質、癌基因和肝臟微環境有關[8]。因此,在針對復發風險高的結直腸癌患者治療策略上,接受肝臟影像學檢查對制定合理的手術策略,以及早期預防肝轉移,提高患者生存率具有重要意義[9]。
1.3 乳腺癌腦轉移及骨轉移
乳腺癌好發轉移于腦、骨。研究表明,晚期乳腺癌骨轉移高達75%左右,其中27%~50%為首發骨轉移,乳腺癌進展期約15%~30%患者會出現腦轉移[10~11]。導致三陰性乳腺癌(TNBC)轉移的主要原因就是腫瘤微環境,利用TNBC細胞(MDA-MB-231),這些細胞被調整為僅轉移到大腦或骨骼組織。MDA-MB-231腦尋找細胞已被證明與血腦屏障處的星形膠質細胞相互作用,導致免疫反應的激活,從而導致化學抵抗和腫瘤生長[12]。腫瘤微環境理論認為,轉移癌細胞可以穿過血腦屏障。另外,骨微環境主要由膠原蛋白I型的細胞外基質組成,其高表達與患者預后差密切相關[13]。
1.4 胃癌肝轉移
由于胃癌細胞的循環擴散性,胃癌極易發生遠處轉移,這也是導致胃癌患者不良預后的主要原因,其中肝臟是胃癌遠處轉移最常見的部位[14]。隨著“種子—土壤學說”的提出,學者們認為肝轉移灶邊緣的肝臟微環境,如肝實質細胞喪失正常分化能力,大量腫瘤相關巨噬細胞的浸潤賦予了腫瘤轉移和侵襲性生長的特性,這些與胃癌肝轉移灶的形成密切相關[15]。此外,轉移的胃癌細胞會引起肝臟損傷和炎癥反應,這也進一步促進了骨髓單核細胞在轉移瘤周圍浸潤、分化、形成腫瘤相關巨噬細胞促進腫瘤細胞擴散。
1.5 肺癌腦轉移
肺癌具有高度侵襲性,非小細胞肺癌(NSCLC)約占所有病例的85%極易出現腦轉移,約50%的NSCLC患者在疾病進展過程中會發生腦轉移,預后極差[16]。由于血腦屏障的存在,大腦一直被認為是腫瘤轉移豁免器官。近年來,有研究顯示腦轉移灶會破壞血腦屏障的完整性,且腦轉移灶的TME能夠誘導腫瘤細胞免疫逃逸,與肺癌的原發灶相比,腦轉移灶具有獨特的TME,針對NSCLC原發灶和腦轉移灶TME的分析發現PD-L1和TIL可作為免疫治療的生物標志物[17]。
2 癌細胞轉移機制
癌細胞轉移過程是由于正常細胞中控制細胞增殖、運動和存活的細胞信號通路的改變。細胞從上皮到間充質(EMT),而癌細胞向遠處轉移會失去此特征,甚至會逆轉,從間充質到上皮,從原發腫瘤單個細胞侵入血管,稱為“循環腫瘤細胞”[18]。腫瘤常常處于缺氧狀態,缺氧誘導因子1a(HIF1a)和上皮上調至間充質標志蛋白,會刺激腫瘤細胞的轉移潛力[19]。多項研究表明,EMT標志物的存在與患者不良預后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包括前列腺癌、肺癌、乳腺癌、肝癌、結直腸癌或膀胱癌等[20~21]。癌細胞轉移與“器官親和性”理論為如何應用相關機制防治癌癥轉移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3 中醫論治癌癥轉移
3.1 中醫理論認識
楊士瀛在《仁齋直指方·卷二十二·發癌方論》中所述“癌者,上高下深,巖穴之狀,顆顆累垂,毒根深藏,穿孔透里”,通過對癌的描述,形象得知癌的幾個特點,即病深、質堅、致病深、發病隱匿、轉移特性。癌癥轉移在中醫學上稱為“傳舍”,“是故虛邪之中人也……留之不去,傳舍于胃腸”描述了人體正氣虧虛,邪毒易侵襲人體留而不去,故易傳于他臟。《靈樞·百病始生》中“虛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則傳舍于絡脈……留而不去,傳舍于經……留而不去,傳舍于輸……留而不去,傳舍于伏沖之脈……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著于脈,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或著孫脈,或著絡脈,或著經脈,或著輸脈,或著于伏沖之脈,或著于脊筋,或著于腸胃之募原,上連于緩筋。邪氣淫溢,不可勝論……”描述了癌毒的轉移過程,體現了癌毒形成后經過孫脈、絡脈、經脈、輸脈等傳播到其余臟器,侵犯其他器官,也闡明了癌毒轉移的路徑有特定的傾向,也體現了“器官的親和性”,多數癌毒也會有特定的器官傳播。《金匱要略》中所描述的“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臟腑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肝木不疏,則影響脾臟的生理功能,脾不升清、脾不運化,治法上應當扶脾土之氣已抑木旺。中醫理論對“傳舍”早已有描述,在治療上可以運用相關理論,把握疾病整體核心、辨證施治、審因用藥,在癌癥轉移防治中具有重要作用。
3.2 中醫藥防治“傳舍”
中醫理論認為,五臟六腑關系緊密,不僅生理相連,病理上也有關系,“傳舍”治療原則應注重整體觀,標本緩急。病機特點以邪氣盛為主,病程日久,機體正氣不足,治療時應祛邪為主兼以扶正。癌毒為特殊毒邪,邪氣亢進、病勢兇猛,且蟄伏深處,頑固難消,故早期以祛邪為主,中藥多用蜈蚣、水蛭、貓爪草、土鱉蟲、白花蛇舌草等清熱解毒之品,也具有抑癌作用。
癌毒容易四處流竄,形成“傳舍”,由于“器官親和性”,五臟六腑“傳舍”防治更具有重要意義。肝旺則克脾土,肝屬木,脾屬土,肝臟疏泄賴以脾臟運化水谷,脾失健運則水停于機體,易出現腹脹、腹水、納差等癥,治療上宜用柴胡、木香、青皮等疏肝理氣的藥物。脾土與肺金在人體水液調節、氣機運動變化發揮重要作用,“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脾氣不升則肺氣無以宣發,水谷精微無以充養全身,可用白術、山藥等藥物顧護脾土;肺生骨,腎主骨,“五藏已具,而后生肉……肺生骨”,骨為肺生,肺朝百脈助心血運行,富含營養物質可以通過百脈運送至骨,故易形成骨轉移,宜用補骨脂、骨碎補等補腎強骨之品;腫瘤中晚期,癌毒侵蝕體內漸深,加之傳舍他臟,正氣虛弱,“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應予以扶正,扶正應當氣血陰陽同調。腫瘤術后患者氣血虧虛,易出現氣短、乏力、食少便溏等癥狀,可運用補氣健脾之法,多用黃芪、黨參等藥物;放化療患者,邪毒傷陰,可見口干咽燥、手足心熱、盜汗等陰虛癥狀,故以養陰生津為主,宜選用龜甲、知母、百合等藥;腫瘤后期,疾病發展,褫奪正氣,陽氣衰微,多表現為畏寒、脘腹冷痛、腰膝酸軟等虛寒之癥,可選用山萸肉、菟絲子等溫中補陽之品。
4 小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癌癥轉移是造成癌癥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現今針對癌癥轉移的治療手段相對局限,患者生存率仍有待提高。從腫瘤微環境方面論述,為“器官親和性”提供理論基礎,闡明癌癥轉移的相關機制,進一步提示了大多數癌癥有特定的轉移器官,這也能作為防治提醒。隨著未來臨床試驗不斷被認證,相關的藥理作用得到驗證,這對于更好地運用“器官親和性”中西醫理論防治癌癥相關轉移具有深遠意義。
參考文獻
[1]陳聯松,章靜波.腫瘤轉移器官親和性研究進展[J].國外醫學(腫瘤學分冊),1987(3):146-150.
[2]岳銘,王理偉,崔玖潔.胰腺癌器官特異性肺轉移機制的研究進展[J].中國癌癥志,2023,33(11):1026-1031.
[3]陳偉偉,劉承利.循環腫瘤細胞在胰腺癌診療中的研究進展[J].中國腫瘤臨床與康復,2018,25(7):890-893.
[4]桂德春,程張軍,周家華.連環蛋白P120在人胰腺癌組織中的表達及其意義[J].東南大學學報(醫學版), 2011,30(5):683-687.
[5]費陽,程張軍,劉緒舜,等.P120catenin在胰腺癌中的表達及其基因多態性的研究[J].中華外科雜志,2009,47(23): 1809-1812.
[6]劉軍,付馬墨陽.結直腸癌肝轉移癌外科治療現狀[J].醫學研究雜志,2020,49(8):1-4.
[7]朱曉文,岳磊,趙文虎,等.微生物通過巨噬細胞RIG-I乳酸化修飾促進結直腸癌肝轉移的機制研究[J].南京醫科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2,42(12):1664-1672.
[8]彭忠,高青.結直腸癌肝轉移分子機制的研究進展[J].重慶醫學,2015,44(30):4289-4292.
[9]王屹.結直腸癌肝轉移瘤影像診斷[J].中華肝膽外科雜志,2020,26(7):500-502.
[10]江澤飛,陳佳藝,牛曉輝,等.乳腺癌骨轉移和骨相關疾病臨床診療專家共識(2014版)[J].中華醫學雜志,2015,95 (4):241-247.
[11]王文藝,顧軍.乳腺癌腦轉移的特點及治療研究進展[J].臨床腫瘤學雜志,2022,27(3):265-272.
[12]夏晨,傅韻,李正東,等.LKB1通過增強間隙連接細胞通訊增加乳腺癌細胞對順鉑的敏感性[J].同濟大學學報(醫學版),2014,35(4):12-18.
[13]李芳芳,范靜婧,馬斌林.三陰性乳腺癌中Ⅰ型膠原蛋白α1鏈高表達對患者預后的影響[J].中華腫瘤雜志, 2020,42(2):5.
[14]白星,程翻娥,楊長沅,等.基于SNAIL信號通路及腸道菌群研究密點麻蜥抑制胃癌肝轉移的作用機制[J].中草藥,2023,54(3):825-833.
[15]王澤瑜,倪博,趙剛,等.轉移灶腫瘤浸潤邊緣非組織特異性巨噬細胞對胃癌肝轉移手術療效的評估價值[J].腫瘤,2022,42(8):542-551.
[16]曹勝男,郗艷,李想,等.能譜CT在預測肺癌腦轉移中的應用價值[J].中國CT和MRI雜志,2023,21(7):49-51.
[17]萬暢,龐靜丹,吳正升,等.非小細胞肺癌腦轉移免疫微環境、臨床病理特征分析[J].臨床與實驗病理學雜志,2023, 39(11):1316-1321.
[18]張秀紅,楊增明.上皮細胞-間充質細胞轉換(EMT)在癌癥轉移、胚胎發育及哺乳動物雌性生殖過程中的作用機制[J].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進展,2012,39(4):307-313.
[19]左海波,陳小伍,朱達堅.缺氧誘導因子-1α在上皮-間充質轉化過程中作用的研究進展[J].廣東醫學,2012,33 (10):1501-1503.
[20]郭益辰,李衛平,楊瑞婷,等.ZEB1、AR、E-Cadherin和N-Cadherin在前列腺癌組織中的表達及意義[J].現代泌尿外科雜志,2023,28(7):627-631.
[21]魏麗榮,滕小艷,夏前林,等.STC1誘導上皮-間質轉化促進肺癌細胞的侵襲和遷移[J].中國癌癥雜志,2020,30 (7):497-504.
——中醫藥科研創新成果豐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