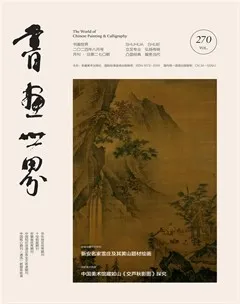從傳統山水畫中找尋藝術給養




創作山水畫一直是我在業余時間持續精進的事情。古代畫家大多是文人士大夫,皆以繪畫為文人余事。古代文人群體憑借深厚的知識底蘊和藝術感知力,鉆研藝術的本質、規律和表現手法,他們既創造了豐厚的繪畫理論,也以個人的創作實踐引領著藝術風格的更新換代。
我的山水畫創作緣于理論研究。幾年前讀古代畫論,后又精讀《石濤畫語錄》,突發對山水畫創作的熱情,這種熱情推動著我去研究繪畫理論、學習繪畫技法。大概從事藝術的人都會有些感性和天馬行空的想法。從那時起,我每讀一位畫家的畫論和作品,總會生發出一些感悟:讀石濤,體會到他人生的苦楚與筆墨的暢快;讀八大山人,感受到他以頑強與命運相搏;讀徐渭,感悟到他既不迎合也不放棄的文人底線……再后來讀田園山水,讀文人隱逸,讀荊浩、關仝、馬夏之變……日子久了,慢慢積累寫出一本冊子,記錄下對古代畫家藝術風格的分析和對他們的學術地位、繪畫價值的思考。
正是這些研究,促使我拿起畫筆開始了山水畫創作。繪畫于我而言并不陌生,大學和讀研期間我都曾有大量時間的創作實踐,也曾高分完成了國畫、油畫、版畫及寫生課的作業。山水畫創作必然離不開習古。多年來我從古人山水中獲取到豐富的滋養。石濤可以說是我的第一位山水啟蒙老師。石濤的筆墨靈活多變、渾厚恣肆,視覺上極富表現力和節奏感,他的《搜盡奇峰打草稿》今天再看依然令我心潮澎湃。在石濤的“指導”下我還撰寫了關于石濤山水創作觀的理論文章,闡述了我對石濤創作觀的理解。石濤是一位“從傳統出走,由造化歸來”的藝術家,他的明代宗室身份決定著他的藝術是以深厚的傳統藝術基因為積淀的。讀他的“一畫論”,我能體會到他的藝術智慧之深和哲學境界之高。在人生旅途的后半段,他隱逸山林,深入造化之境,提出了“我自用我法”的藝術宣言,構建完成了獨樹一幟的創作觀,這也是學界認為的石濤學術“現代性”之所在。石濤對藝術的熱烈追求感染了我,也讓我明白學習山水畫創作需要上溯傳統,摸清傳統藝術的根脈才能真正理解中國藝術的內核。
很多人認為清初“四王”與包括石濤在內的“四僧”有著相反的藝術方向,“四王”追求筆墨程式、致力于傳統筆墨中尋求組合變化的創新,是與強調“蒙養”和“生活”的石濤相反的一路。在我看來,“四王”恰好為我提供了學習傳統筆墨程式的捷徑。“四王”以臨、仿、摹、擬的繪畫實踐總結傳統山水畫程式體系,是傳統山水畫體系下具有總結意義的關鍵環節。“四王”的筆觸溫婉平和、筆墨渾融,在看似陳陳相因的藝術樣式中呈現了生命的光彩,我曾這樣寫道:“讀‘四王’之首王時敏的山水圖冊,在原應感受為索然寡淡的畫面里,有無數灰度級別的筆觸,一眼望去,滿眼的山體樹木猶如被陽光照射的層層密林,又感覺像波光粼粼的水波在蕩漾。我確信這樣的繪畫一定打動過無數人。”隨之我分析了“四王”筆墨程式的利弊:后世普遍認為“四王”在畫壇上核心正統地位的確立,得益于他們所在身份階層延承了自明代以來儒家的士人精神、審美范式,而在我看來,更在于他們用熠熠光彩的筆觸全面歸結了中國繪畫筆墨的核心,達到了后人再難企及的高度。
順著“四王”的藝術脈絡,我又涉獵了董其昌的畫論。董其昌的學術背景剛好處于晚明畫壇的轉向期,晚明各家秉承宋、元不同的畫脈各自為政,慢慢產生了兩種弊端:一是為出新而創造,“承訛藉舛”,不講究傳承根基;二是因藝術品創作商品化嚴重,致使文人畫的濫觴將斷失士人文脈。董其昌恰在此時擲出響亮畫壇的“南北宗論”,厘清了自唐至明之間山水繪畫的傳承脈絡。他倡導“南宗”一路畫脈,重臨摹、重筆墨、重心象、重真率,以此區別文人畫家和職業畫家。我是從董其昌的理論和繪畫中建構起對中國山水畫筆墨系統的整體認知的,切實理解了高品格的山水畫所追求的書寫性,而這種書寫的狀態是可以從營造的意境、描繪的自然造化中透出的。于是,我在臨摹、創作時嘗試“以書入畫”,特別追求渴筆和潤墨的結合,在一幅作品創作時盡力做到一以貫之,避免各種形態的筆觸堆放一氣,進而導致失去雅致沖和的文人畫意。
從石濤的創新精神到“四王”的圖式歸納,再到董其昌的重振文人畫,基本確立了我山水畫創作的方向。藝術發展的規律往往是這樣:當一種技術達到成熟的時候,便會推倒重來,或者另起爐灶。而我的創作體驗亦是如此,每一次創作學習都如同充滿未知和驚喜的翻山越嶺之旅,山間的迷人景色總也看不完、賞不盡,似乎總有更好的風景在前方指引著我去探尋,從明代的沈周、文徵明到元代的趙孟、黃公望、王蒙……進而到五代文人畫鼻祖董源,沿著歷史的脈絡在文人畫家的山水世界中徜徉,汲取著豐富的營養和靈感。每一次新的發現,都如同點亮的一盞明燈,指引我不斷前行。
學習越多越感受到山水畫的魅力,山水畫里的書卷氣清逸淡遠、寧靜脫俗,體現了文人雅士的自在悠然。每一位古代畫家都擁有別樣的氣質。我臨習較多的是黃公望的作品,我曾經購買多個版本的《富春山居圖》,一開始只是反復地看,感覺怎么都看不夠,后來嘗試臨摹了一些《擬黃子久筆意圖》,才稍緩解渴意。學習文徵明的作品同樣如此,他的《蘭亭修禊圖》中茂林修竹、曲水流觴引人入勝,真叫人欲罷不能。沈周山水的“優雅”讓人沉浸于筆墨的世界,每一筆每一畫猶如清泉流淌在山石之間,清爽而有力,看似輕簡的畫面卻透出無盡雋永。新安畫派是幾年前曾經關注的對象,我沉迷其中,臨摹、創作了很長一段時間,也曾對畫派風格形成進行研究。最近整理畫作,我發現梅清的山水畫尤其特別,屬于“骨骼清奇”一路,渴筆淡墨做得是如此極致精彩,云霧繚繞的仙峰、空靈高遠的意境、奇崛巧妙的構圖,似是有著神奇般的魔力無法抵擋。隨著臨仿越來越多,我越發能體會古人山水畫的精妙之處。
傳統山水畫考驗畫家的筆力和意境。筆力是畫家對手中毛筆的掌控能力,是用線用墨的剛柔頓挫、輕重緩急,這關乎山水畫的形態與質感。意境是山水的靈魂所在,也關乎著繪畫能力和格調水平。山水畫境界的提升,需要畫家具有堅實的基礎,而不能像無根之木般飄忽不定、缺乏根基;需要建立在畫家對傳統繪畫技法的深入學習和掌握之上,只有充分理解和傳承了前人的經驗與智慧,才能有所創新和發展;還需要畫家對自然有著深刻的感悟和體驗,通過與山水的親密接觸、用心觀察和思索,才能真正捕捉到山水的神韻和精神內涵。個人的文化修養、審美素養及哲學思考等也是山水畫境界提升至關重要的支撐。只有將這些方面有機結合起來,如同根系牢牢扎根于大地一般,山水的格調和境界提升才會扎實、穩固且具有生命力,才能不斷向著更高層次邁進。
近十年來,我將創作和理論研究并駕齊驅,真正深入傳統、上手創作,并于文字中理解他們的時代和身份。我認真鉆研每一幅經典畫作,分析其構圖、筆墨運用、色彩搭配等各個方面,同時閱讀相關的理論著作和研究資料,試圖從更宏觀的角度去解讀這些藝術作品背后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和歷史意義。通過不斷的實踐和思考,我逐漸架構起相對完整的山水畫體系,這讓我能更加系統全面地認識和把握山水畫藝術的發展脈絡,也為我的創作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和豐富的靈感來源。
當下,中國山水畫科經歷了守護與拓寬的討論后,傳統形態走向現代形態,必然面對拓寬和超越自身語言屬性的現實,而現代性的表現離不開對中國畫內在傳統的繼承和創造。無論是作為美術研究者,還是創作者,唯有親身深入傳統,才能真正理解藝術的精髓所在,將其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在研究中理解作品背后的文化內涵、哲學思考和審美取向,在創作中掌握傳統技法的微妙運用、感悟傳統所蘊含的精神力量,從而理解民族審美的嬗變歷程、體驗藝術帶來的智慧啟迪,大抵這便是承揚傳統的必然之路和藝術精進的絕佳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