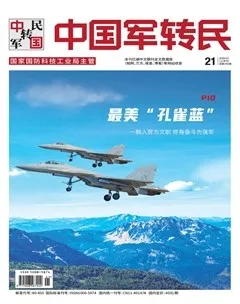俄烏沖突中情報支援新方法研究
【摘要】俄烏沖突爆發以來,俄烏雙方在情報信息領域展開高技術對抗,特別是烏克蘭借助美西方的技術支持,謀求情報支援新方法,構筑戰場上對俄的情報優勢,其中,以“情報眾籌”為代表的情報支援新方法在沖突中的表現尤為亮眼。因此,本文通過對“情報眾籌”概念與歷史的解析,運用文本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緊貼戰爭前沿,闡述“情報眾籌”在俄烏沖突中運用的方式,分析其運用特點,深入剖析“情報眾籌”的情報支援理念和運用方式。
【關鍵詞】俄烏沖突|“情報眾籌”|情報支援
俄烏沖突爆發以來,俄烏雙方均采取新型手段以獲取戰場優勢,讓此次沖突較以往有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既體現在有形的實體戰場,更體現在無形的數字戰場。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技術等新技術飛速發展,情報支援方式也在新技術的助力下有了新的樣式。沖突爆發后,烏政府主導開發多款智能終端應用軟件和互聯網平臺供烏民眾使用,讓每個烏克蘭人都可以隨時隨地拍攝俄軍并上傳至互聯網,而后由烏軍對俄軍實施精準獵殺。這種新型情報支援模式又稱“情報眾籌”(Crowdsourcing Intelligence),讓烏軍可以利用民眾力量實現對俄軍的動態監視、目標指引和毀傷評估,并使俄軍在烏境內的軍事行動屢屢受挫。
一、“情報眾籌”的發展歷史
“情報眾籌”也稱情報眾包,其核心理念是將一個組織需要解決的問題發布到互聯網上,并通過集體智慧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答案。“情報眾籌”并非在俄烏戰場上首次提出并運用,它隨著互聯網、云計算等技術的發展而逐漸成熟。
(一)從商業模式借鑒的理論發展時期
首先,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與普及促成了“眾籌”模式的移植。2001年,Tim Shell與 Jason Richey創立維基百科,在技術上實現了一種自發、開放、民主的精神。2005年美國聯邦調查局Calvin Andrus發表的論文討論將維基百科與博客的模式相結合并運用到美國情報工作中,形成一種更靈活的情報分析方法[1]。2006年,美國《連線》雜志的專欄作家Jeff Howe正式提出“眾籌”的概念,用來定義一種利用群策群力解決開放式問題的方法[2]。其次,從政府政策層面而言,“9·11”事件使美國情報工作面臨的壓力越來越高,美國政府與研究機構開始考慮眾包在情報中應用的可行性。上述Calvin Andrus從理論上提出,維基百科與博客相結合的模式或可用于分類、組織、檢索情報機構內的各種數據、信息、知識,并為開放式的情報問題提供相比結構化分析(Structured Analytic Techniques,SATs)更為靈活的方法。
(二)理論到實踐的試驗式應用時期
在“眾籌”理論的指導下,“情報眾籌”在情報工作中有了較為廣泛的應用,讓“情報眾籌”從理論走向實踐。其催生出美國國家反恐中心的“情報眾籌”平臺Intellipedia與美情報高級計劃研究局(Intellig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ctivity,IARPA)的CREATE兩個大規模項目,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從目前公開的數據看,從2006至2009年,Intellipedia平臺上活躍參與的情報工作者人數由3,000人增至100,000人;內容條目則由28,000頁增至900,000頁,且平均每天編輯的條目有15,000頁[3]。此外,該時期“情報眾籌”也逐漸應用于處理一些實際的情報問題。如2011年利比亞沖突期間,大量利比亞人通過“眾籌”系統Ushahidi發布沖突態勢、照片視頻、位置信息,使得聯合國能利用“眾籌”系統Ushahidi監控2011年利比亞沖突,并為沖突地區的人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三)信息化發達、智能化初步顯現背景下的成熟運用時期
隨著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的飛速發展下,“情報眾籌”的運用也愈發成熟。如一些智庫也運用“情報眾籌”方法開展情報搜集和分析。例如,在對馬航MH-17墜毀事件進行調查時,英國民間智庫“搖鈴貓”(Bellingcat)核心團隊將調查任務分解為防空導彈型號、發射車藏匿地點等若干小任務,在網上發布素材需求,試圖在短時間內獲取媒體報道之外的一手信息。為驗證分析假設,核心團隊繼續發布下一輪“眾籌”任務,整合多來源的其他證據,驗證“拼圖”的完整性和準確性,直到最終認定馬航MH-17航班是被來自親俄武裝力量的俄制“山毛櫸”防空導彈擊落[4]。
二、俄烏沖突中“情報眾籌”的運用
烏軍利用本土作戰的“地利”“人和”以及社交媒體等互聯網平臺,在俄烏沖突中廣泛運用“情報眾籌”方式,產生有效的支援效果。
(一)互聯網平臺投放使用,全民參與情報生產
俄烏沖突爆發后,烏政府主導開發多款“情報眾籌”應用軟件和網絡平臺,讓烏國民可以自由發布俄軍動態,讓全民參與到情報生產之中,如表 1列出了部分烏“情報眾籌”應用及平臺。烏副總理米哈伊洛·費多羅夫主導開發面向烏民眾的“情報眾籌”程序,充分發動國民力量進行情報搜集。在全民“情報眾籌”平臺開發商,烏政府在沖突開始后就發布了一系列“情報眾籌”應用軟件和網絡平臺。例如,由數字化轉型部基于電報(Telegram)平臺推出的“電子敵人”(e-Enemy)應用軟件,用戶在使用該程序時,其會引導用戶瀏覽一系列話題,并輸入他們所看到的俄軍具體信息,供烏克蘭軍方發現、打擊俄軍。除此之外,烏政府還開發了“迪亞”(Diia)、“ePPO觀察者”(ePPO Observer)、“我看見”(Bachu)等“眾籌”網絡平臺,同樣讓烏民眾可以通過手機報告俄軍動向提供平臺。在專用作戰應用軟件方面,美烏雙方合作開發了軍用安卓戰術攻擊包(Android tactic assault kit, ATAK),能夠集成民用數據和軍用通信、態勢感知等模塊,實現在頻譜拒止環境下的情報支援[5]。

(二)與指揮信息系統相連,融入作戰指揮鏈條
俄烏沖突中,“情報眾籌”實現了用戶終端到網絡云端,再到軍方的訂單式情報支援方式。這種專用應用程序動員起來的“情報眾籌”,加上由情報驅動的分隊作戰,便構成了從前端到終端的閉合打擊鏈路。大量智能手機終端用戶充當前端情報搜集設備,在上報敵情狀態信息時,附帶上報敵地理坐標信息。后臺專用的應用服務器通過無線信號網絡同一個個情報搜集設備,并結合數字地圖軟件對情報進行整編處理,形成局部或整體的敵情態勢圖,提供給軍方,供作戰部隊實時進行打擊[6]。如圖 1所示,展示了用戶移動終端到火力打擊的支援過程。因此,在這種依靠“情報眾籌”實現支援作戰的新型作戰方式下,傳統的傳感器變成了公民手中的移動手機,“情報眾籌”平臺變為情報分析加工、作戰資源調度的“云端大腦”,作戰部隊可以即時獲得敵方目標信息。在某種程度上,“情報眾籌”平臺可以在烏軍制空權、通信和指控中心被摧毀的情況下充當C4ISR系統的部分功能,甚至是核心功能。

(三)分析評估“眾籌”效果,提出新的“眾籌”問題
烏克蘭的“情報眾籌”平臺不僅嘗試與指揮信息系統相融合,還運用人工智能技術自動分析識別目標,評估“眾籌”效果及時給出反饋,提出新的“情報眾籌”需求。一是自動識別目標,上傳目標信息。“情報眾籌”平臺依托網絡開源技術,引入智能模塊,對網民上傳的圖片、視頻等進行自動的目標識別與篩選。例如,在Telegram平臺上,烏政府集成人工智能等模塊,讓烏公民可以通過智能聊天機器人發布信息,再由其進行識別和上報[7]。二是評估支援效果,及時給出反饋。“眾籌”平臺在分析識別目標后,上報敵目標相關信息,隨后由作戰部隊遂行打擊任務,并通過軍方、政府等官方渠道評估反饋打擊效果。俄烏沖突中,烏軍通過“情報眾籌”得到相關信息,在作戰部隊、無人機等實施打擊后,民眾亦可繼續上傳目標摧毀程度照片或視頻,輔助評估打擊效果。三是根據新的情報需求,提出新的“眾籌”需求。如果“眾籌”問題未能有效滿足信息需求,或是上輪打擊效果不足且目標依然在移動,那么官方還會繼續提出新的“眾籌”需求以滿足情報需求。
三、俄烏沖突中“情報眾籌”的特點
俄烏沖突中,烏“情報眾籌”的新型情報支援樣式在戰爭實踐中大顯身手,為世人展示了智能互聯網時代情報支援的新方式。
(一)搜集效率上,普通民眾得到充分動員
“情報眾籌”的最主要特點就是通過簡易便攜的手機應用軟件把廣大民眾充分動員起來,通過數量優勢提高情報搜集效率,使俄軍仿佛陷入了“人民戰爭”之中。當傳統情報支援模式強調傳感器的數量、情報流程的必要性,烏“情報眾籌”的情報支援方式卻實現了軍民界限,實現了跨界支援。烏政府將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作為動員手段,方便快捷、覆蓋面廣。一方面,通過輿論引導,“情報眾籌”平臺實現了凝聚戰斗意志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為他們提供了參與戰爭、支援作戰的便捷手段。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烏克蘭“人人都是宣傳員、人人都是偵察員”,廣大民眾通過隨手一拍便可完成一次情報搜集工作。而這種海量情報信息經由后臺甄別、計算后便形成實時或近實時、可提供部隊使用的戰場情報。在這里,軍民界限空前模糊,平民深度介入作戰行動,廣大民眾可以在戰場后方提供有效的情報支援。
(二)效能發揮上,情報支援結構集成高效
“情報眾籌”平臺讓互聯網與指揮控制系統連接起來,使情報支援更加扁平化,指揮控制更加直接化,信息轉化成指令的速度更加高效化。首先,“眾籌”平臺的訂單式支援模式,可以直接賦能于烏軍指揮控制系統,充當烏軍指揮控制系統的部分功能,為烏軍實時或近乎實時提供情報信息。其次,“情報眾籌”平臺使烏軍在作戰實現戰場上的敵情單向透明。尤其是俄軍在哈爾科夫等烏大中型城市的作戰中,烏軍利用地理、民情、社情等優勢,使俄軍在城市作戰中屢屢受挫,其坦克等裝甲目標多次遭到精準打擊,這些都離不開“情報眾籌”的作用[8]。第三,“情報眾籌”運用模式與烏軍軍事改革耦合,構成韌性強的“察打一體網絡”。2014年烏克蘭危機后,烏陸軍進行小型化、模塊化等現代化軍事改革,有效提升了軍隊現代作戰能力[9]。而“情報眾籌”平臺的使用恰好與烏軍改革同頻共振,讓網絡化平臺融入各層級軍事指揮控制體系,在各個層級都能完成所需的情報保障效果。
(三)理念更新上,網絡化智能化平臺接入支援體系
“情報眾籌”模式的運用與發展,代表了智能化網絡化背景下情報支援理念的更新。一是網絡平臺的接入,讓情報與指揮控制更加協調同步。由專用應用軟件動員起來的“情報眾籌”,加上情報驅動的現代化作戰模式,將情報流程和作戰指揮控制耦合起來,使得網絡云端、情報支援、作戰指揮結合起來,呈現出典型的“云—網—端”架構。二是人工智能技術的融入,使情報搜集與分析更加自動化。烏“情報眾籌”平臺融合聊天機器人等功能,在上傳的圖片和視頻進行自動識別,篩選后自動上傳至云端,由烏軍或政府加之運用,再賦能于決策或作戰。三是情報保障體系的更新,使情報支援更具韌性。一方面,在美西方的技術支持下,烏“情報眾籌”不僅可以通過普通的民用電信網絡進行傳輸,還可通過“星鏈”等通訊手段進行傳輸,提高了戰時情報信息傳輸抗摧毀能力。另一方面,烏政府研發的“眾籌”平臺可以在用戶手機沒有網絡的情況下自動備份,只要一有網絡就可以進行數據上傳,保證了情報的及時性。
四、結語
俄烏沖突已經成為先進網絡化、智能化軍事技術的試驗場,在情報支援實踐上,雙方均力圖探索新方法以謀求情報優勢。在以烏政府研發為主題,美西方技術援助的加持下,“情報眾籌”的運用恰好貼合烏軍作戰實際,通過動員廣大民眾、融入作戰指揮鏈、自動化分析反饋等方式,有效彌補了戰場上情報支援體系的不足。因此,在未來聯合作戰情報支援中,必須高度重視智能化、網絡化技術的應用,加速將先進技術轉化為軍事應用成果,為獲取情報信息優勢,打贏高端戰爭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撐。中國軍轉民
參考文獻
[1]ANDRUS D C. Toward a complex adaptive intelligence community[J].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2005,49 (3) : 1-30.
[2]HOWE J.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J]. Wired Magazine,2006(14):5.
[3]夏匯川.眾包在情報工作中的應用及其對我國的啟示[J].競爭情報,2022,18(02):9-16.
[4]李景龍,周偉.基于網絡的開源情報調查方法創新與應用——以英國私營情報調查機構“搖鈴貓”為例[J].情報雜志,2023,42(02): 8-11, 21.
[5]David S. Ukrainians use Telegram Chatbot to track and target Russian troops[EB/OL]. (2022-05-28)[2024-05-30]https://news.hookupcellular.com/ukrainiansuse-telegram-chatbot-to-track-and-target-russiantroops/.

[8]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盧甘斯克軍事專家:烏情報部門正在哈爾科夫州準備待激活的巢穴和秘密軍火庫[EB/ OL]. (2024-04-17)[2024-06-05]https://sputniknews. cn/20240417/1058458439.html.
[9]烏克蘭軍隊去中心化改革:以營連為單位進行作戰[EB/ OL]. (2022-03-30)[2024-06-07]https://mp.weixin.qq.com/ s/gWtK-qPos5PSU47WTA6H6A.
(作者簡介:楊朝運,信息工程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情報理論;高慶德,信息工程大學碩士生導師,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情報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