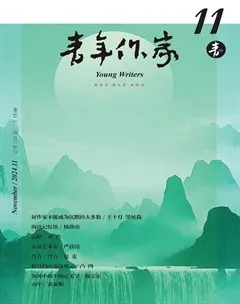海島記憶館
一
才登上回龍沙,兩個孩子就興奮地朝前面跑去。喬敏紅走在于醫生前面,望著眼前突然展現出來的大海,她的心緒既有些激動,又帶著惆悵。在并不算是很遠的前方,蔚藍色的大海被傍晚的霞光映照著,變得金燦燦的,看上去就像是一片流動的金箔。
他們是跨過一條兩邊砌了石塊,但現在并沒有流水的小溪,從村子前面木麻黃樹林里的一條小路走過來的。一個多小時前,他們一家人才到達這個村子。喬敏紅特地選了倒數第二班輪渡,當載著他們的小汽車沿著環島公路行駛時,喬敏紅看到公路旁邊比十幾年前多了許多小洋樓。駛進村子后,她注意到村道上并沒有什么人,路邊一些人家的大門還緊鎖著。她想起姑姑對她說過,現在島上很多人都在市區買了房子,要在夏天旅游旺季時才從城里回來。
紅色的小汽車在他們預訂的“防空一號”前面停下來,望著從屋里出來,站在車門前笑嘻嘻地跟他們打招呼的民宿女主人,喬敏紅心里想,現在村子里沒有多少人,姑姑一家也都不在,即使她不戴墨鏡,島上可能也沒什么人會認得她了。
“哇,好漂亮的大海啊!”5歲的小波喊道。他一直都是一驚一乍的。比他大兩歲的姐姐思思現在已經有了一些小女生的矜持,她不像弟弟那樣興奮,思思只小跑了幾步,就停了下來,在積沙上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前走。
“瑤臺島的風景原來還是很美的啊!”于醫生在喬敏紅身后說。
喬敏紅聽到了丈夫的話,但并沒有轉過身去,也沒有回答他。站在回龍沙上,望著眼前美麗的風景,她感覺到自己的心情愈發憂郁。
當年事情發生時,她比現在的小波還要小,她哥哥喬敏華也才上小學。她記得二樓眠床上那一抹黯淡的白色。她被不同的女人抱著,有時從一個人懷里轉到另一個人懷里,一直到現在,她都還能記起來那些熱烘烘的不同女人帶給她的感覺。屋子內外都是人,到處都是議論、哭泣和詈罵的聲音,整座石頭房子籠罩在一種壓抑的氛圍里。這些年來,一想到這座房子,她就希望它未曾存在過,或者直接從人世間消失。
小波已經跑到了沙山的邊緣,她看到他膝蓋稍微一彎,身體后仰,就從沙坡上滑了下去。滑到沙山下面,小波站起來時,只是一個小小的影子。他站在那里,先是對他們揮手,后來又把兩只手合攏放在嘴上對他們喊叫著什么。海風把他的聲音吹散了,雖然聽不太清楚他在喊什么,但喬敏紅明白,小波是想要他們也都滑下去。
“你去陪他們玩一玩吧!”喬敏紅對丈夫說。對于醫生這次特地請假陪她到瑤臺島來,她嘴巴上沒說,但心里還是懷著感激的。
“好,那我一會兒就過來。”有些不放心地看了看她,于醫生對喬敏紅說。
喬敏紅看著丈夫走到沙山邊,和女兒思思一前一后也都滑了下去。他們在沙山下面玩耍時,喬敏紅沒有動,她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在她面前,金光閃閃的海面上,風力發電機一個接一個地在海面上延伸過去,它們巨大的葉片緩慢旋轉著,刺破了眼前瑰麗的天空。
喬敏紅用手搭著涼棚,順著海邊一點兒一點兒地找過去。她看到的都是顏色鮮艷外面貼著瓷磚的新蓋的小洋樓。除了對回龍沙這一片地貌還有一點點記憶,喬敏紅覺得,眼前的一切都已經發生了變化。
就在她覺得不可能再找到那座房子,心里已經絕望了的時候,突然間,她看到了它。在印象中,那房子一直孤零零地佇立在村子最外沿的地方,可現在,它被包圍在幾排新房子中間。如果不是它用石頭砌成的外墻和紅色瓦頂是那么與眾不同,她也許會認不出它來。望著那房子被兩棵灰綠色的大樹遮擋了一部分的外觀,喬敏紅又記起她最早看到的那篇公眾號文章的標題:《一個漁村老人的愛情記憶》
她蹙了蹙眉頭,又一次在心里面感受到憤怒。可在那一瞬間,她心里同時還冒出來一絲遲疑,她不知道在那房子里她將遇到怎樣的情況。在到瑤臺島之前,喬敏紅的腦海里可從來沒有浮現過這樣的念頭。
于醫生帶著兩個孩子從沙山的另一邊爬了上來。高瘦開朗的他是喬敏紅的第二任丈夫。看著他和兩個孩子的身影,喬敏紅想起那個只和她在一起生活了幾個月的第一任丈夫。他們還沒有辦酒,只是領了結婚證,她把事情告訴那個男人時,他明顯害怕了。她知道他是擔心她的血液里也包含著瘋魔的基因,雖然她知道自己并沒有。
汲取了經驗,在和于醫生確定關系前,她決定先把那件可怕的事情告訴他。原先她以為會說很久的一個話題,沒想到只用十幾分鐘就說完了。就像卸下了一個沉重的包袱,她轉過頭去,不再望著比她大10歲的于醫生。咖啡館的大玻璃窗下面,車輛行駛經過遠處的高架橋時,閃爍的車燈幻化成一片紅色的光斑。
“他真有間歇性精神病嗎?”沉默了一會兒,于醫生問她。
“我也不確定。”她誠實地回答說。在她記憶中,那個人有時候脾氣暴躁,會沖她母親發火,有時候也會打她和她哥哥,但似乎從來沒有人說過他精神不正常。
事情發生后,那個人就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喬敏紅模模糊糊地記得,他中間出院過,好像還曾經被送進過一個寺廟,只不過后來又被送回到精神病院里。
于醫生朝她走過來,身上的襯衣被風鼓得滿滿的。他一邊走,一邊望著喬敏紅,背對著夕陽,他的身影鑲嵌在晚霞的金光里。
看著丈夫的眼睛,喬敏紅稍稍戰勝了剛才心里面產生的波動。“我已經找到那房子了。”她小聲地對于醫生說,努力不讓他看出自己內心的波瀾。
“很好啊,我明天會陪你一起過去的。”于醫生對她說。
兩個跟在后面的孩子也跑過來了。
“媽媽,我們想要到海里去游泳!”
小波一邊跑,一邊對她喊道。
“好,如果你一直都很聽話,明天就讓爸爸帶你們去游泳。”喬敏紅努力把微笑堆到臉上。她蹲下來,朝兩個孩子張開了手臂。傍晚的余暉照在小波和思思的臉上,把他們的臉也都染上了一層紅色。
“雖然這片沙坡上現在有這么多腳印,但等到晚上,它就會自動變得光滑而平整,就像絲綢一樣。”懷著童年時代對回龍沙的記憶,朝“防空一號”走回去的路上,喬敏紅對兩個孩子說。她的語氣里帶著些驕傲,好像這一片沙坡能這么神奇地變化,倚靠的是她個人的法力。
“我不相信。”小波側著頭,甕聲甕氣地回答說。
“我也覺得不可能。”姐姐思思跟著弟弟說。這其實是他們的家教,于醫生和喬敏紅告訴過孩子,對沒有見過或是不符合邏輯的東西,都不能隨便相信。走在一邊,于醫生只是笑笑地看著喬敏紅和他的兩個孩子,并沒有摻和進來。
“明天早上到這里來看看,你們就會相信了。”喬敏紅對兩個孩子說。
二
1951年冬天,海峽對岸的炮艦毫無征兆地在夜晚漆黑的海面上出現。抵近沙灘后,炮彈就像是響尾蛇的紅信子那樣一顆顆從伸縮的炮膛里吐了出來,擊中這個村子的坑道和民房,經過一番硝煙彌漫、鮮血迸濺的爭奪,孤懸在東海上的這個島嶼失守了,幾天以后才被馳援的隊伍奪了回來。十幾年時間里,由于不斷有來自對岸的襲擾,他們這里從一個荒蕪的小漁村變成了海防前哨,“在我們腳底下,還有海邊的沙灘上,到處都有防空洞和高射炮炮臺。”
這天晚上,端菜上來時,“防空一號”的傅莉香給客人們介紹了這個村莊的歷史。這幾年時間,瑤臺島開始把當年留下的戰爭痕跡當作是獨一無二的旅游資源加以宣傳,除了海邊的陽光、沙灘,現在,這個漁村的戰壕、地道,還有廢棄的高射炮炮臺也受到了更多人的關注,戰地漁村的聲名已經逐漸為外人知曉。
“現在還不是旅游旺季,再過一個月,這里就熱鬧了。到時候沙灘上烏壓壓的,全都是帳篷和涼傘。”傅莉香把手往沙灘的方向一指,仿佛伴隨著她的手勢,沙灘那里剎那間就會出現芝麻豆子般擁擠的人群。
讓年紀還不到30歲的傅莉香驕傲的是,她也曾為這個漁村旅游業的發展增加了一個新看點。是她幫助喬亞明建起了那個海島記憶館,也是她把記者帶到了喬亞明那里,那個記者回去后寫了文章,然后又有不同的媒體轉載,喬亞明那個記憶館才越來越有知名度,甚至就連重訪瑤臺島的馮將軍都點名要去參觀。
這一天晚上,傅莉香也想對這一批客人介紹下海島記憶館,但這四個客人中的女主人好像并沒有在聽,顯得有些心不在焉,她只能努力克制住了自己。
傅莉香對他們講的地道、碉堡和防空洞,喬敏紅小時候也去過,她覺得這些地方并沒有傅莉香講得那么傳奇和神秘。聽傅莉香提起海島記憶館,喬敏紅的臉色馬上就變了,盯著手上的筷子,她決定如果這個不懂得察顏觀色的女人若再繼續講下去,她就叫于醫生帶著他們一起搬到鎮上去住。
感覺到有什么不對勁,過于熱情的傅莉香準備走了,不過出于對自己家鄉的驕傲感,在離開前,傅莉香又轉身對客人們說,“如果你們想要去什么地方參觀,我可以給你們帶路。”
“暫時就先不用了。”察覺到喬敏紅情緒的變化,于醫生委婉地回絕了她的好意。
避開“防空一號”傅莉香的視線,第二天下午,喬敏紅和于醫生沒有從村道上走,也沒有再經過那一片木麻黃防風林,他們沿小溪旁邊一條運海帶的機車路朝海灘走去。海邊的風帶著濃烈的咸腥味,海浪泛著白沫,一波接一波地拍在沙灘上,發出連續不斷的寂寞的“嘩——嘩——”聲。沙灘上,幾個看著也像是游客的人正在玩沙子,太陽照在他們身上,在沙地上拉出幾道長短不一的影子。
從沙灘上望過去,那座原來屬于造船場的石頭房子不像喬敏紅昨天傍晚在山上看到的那樣矮小了,房子旁邊的那兩棵木麻黃也顯得特別高大。喬敏紅聽舅舅說過,那個人買下閑置的造船場,原來是準備翻建成住宅的,可錢還沒有攢夠,就出了事情。
正對著小路的圍墻上,釘著一塊牌子,被太陽曬得有些開裂了的船板上用綠油漆寫著幾個雖然歪扭,但也有些味道的美術字:海島記憶館。喬敏紅不知道這是不是那個人自己寫的。
還沒走到房子門口,她就覺得脖頸上沁出了涼汗。黑洞洞的房間里有些冰涼,透過大門和窗戶灑下來的光線,喬敏紅看到大廳沿墻擺滿了展示架,墻壁上也掛滿了相框,布置成了一個展覽館的模樣。喬敏紅往屋子里探頭張望,卻沒有看到她想要找的那個人。
“有人在嗎?”于醫生喊了一聲。屋子里沒有人應答。稍微等了一小會后,于醫生又喊了一聲。見還是沒有人回答,他們就走進去,先在那些柜子前參觀起來。
柜子里的展品倒是很豐富,除了年代久遠的油燈、海碗、羅盤等漁村器物,還有戰爭時期留下的炮彈和照片,屋子更里面一些,還可以看到那個人用貝殼做的各種東西。
“他的手很巧嘛。”于醫生小聲地對喬敏紅說。
喬敏紅記得那個人給她做過風箏,還給她哥哥做過彈弓。她剛要回答,這時候,從他們身后面傳來一聲咳嗽。轉過頭去,喬敏紅看到一個頭發花白的老人站在屋子門口,正朝他們這邊看過來。
這就是那個人!喬敏紅一眼認了出來。她正想要朝他走過去,卻又站住了。和那次在第四病院見到他時相比,他的頭發更白了,背也彎了下去。喬敏紅心里涌起來一陣傷感,但她馬上又記起了眠床上面那抹白色的影子。
慢慢地,那個人走到他們面前,喬敏紅清楚地看到他臉上的皺紋。
“你們是來參觀的嗎?”那個人問他們說。
“我們看到這里掛著記憶館的牌子,有些好奇,就想進來看下。”喬敏紅用手扶了下臉上的墨鏡,控制住自己的情緒,裝著不認識那個人的樣子說。
“嗯,很多人都來這里參觀的。”那人朝他們點了點頭。
“你這些東西做得很不錯嘛。”于醫生指著展架上面的貝雕對那人說。喬敏紅瞪了丈夫一眼,她心里想,她是不會對面前這個人說任何一句好話的。
“很多來這里參觀的人都這么說。”那個人嘿嘿地笑著,顯出高興的樣子。
他帶喬敏紅和于醫生往房間更東頭走去。樓梯口的墻壁上,有一些用水粉或油漆畫的畫,喬敏紅看到,這些圖畫里都有一個女人的形象,在一個展示柜上方,還掛著一幅很特別的畫作。喬敏紅想起來,自己曾經在好幾個公眾號上看到過它。站在這幅作品下面,她才真正看明白,它原來不是用顏料,而是用很多小海螺的厴蓋拼成的。畫面上的女人用手扶著頭上的斗笠,從她的腰部,背景上厴蓋的光澤幻化出模糊的光圈,使得她看上去就像是從那片金光中走出來似的。
“這個人是誰?”喬敏紅問那個人說。
“她是我妻子。”那人充滿愛意地望著墻上的圖像。喬敏紅知道,他對來采訪的記者也是這么說的,她在“戰地漁村”公眾號上的文章里讀到過同樣的話。
他的妻子?!喬敏紅心里感到一陣疼痛。
“你妻子現在在哪里?”喬敏紅小聲地問,好像她二十多年的痛苦都凝聚在這一個問題里。
“很多年以前,她就已經去世了。”那個人說。
“那時候她應該很年輕吧?”喬敏紅問道,“她是怎么死的?”
“心臟,”那個人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她的心臟有毛病。”
“可我知道的不是這樣。我聽人說,你妻子是被你掐死的。”喬敏紅冷冷地說。
那人身體顫抖了一下。
“誰這么誣陷我?這怎么可能?”他使勁搖著頭,“她是我妻子,我怎么會做這樣的事?”他的聲音變得有些尖利。
“你可以騙自己說那事情沒有發生過,可是,你不能騙別人,尤其是不能對記者這么說。”喬敏紅恨恨地說。
“我說的是事實。”
“你在撒謊!”
“你是誰?你憑什么對我說這些?”那個人聲音大了起來。
面對著那個人,喬敏紅摘下了臉上的墨鏡。
“你認得我嗎?”她控制住自己的情緒,用很輕的聲音問。
“你是——”
那個人望著她,眼睛里流露出困惑的神情。
“我是喬敏紅。”她用顫抖的聲音說。
“啊,你是我女兒——”
那個人大叫一聲,往前跨了一步,好像想要抱住喬敏紅。喬敏紅連忙后退幾步,她伸出手掌,攔住了他。
“對不起,我沒辦法讓自己叫殺人犯作父親。”
“你干嗎要叫我殺人犯?你干嗎要說是我掐死了你媽媽?有誰會掐死自己妻子呢?”那個人垂下手臂,喃喃地說。
“我們就不討論過去的事情了。我這次來瑤臺島,只是想告訴你,不要再搞這個記憶館了,也不要再對別人說你和媽媽當年怎么怎么好,那全是不真實的謊言。這樣說對媽媽以及所有知道事情真相的人是不公平的,也是一種侮辱。”喬敏紅說。
“我和你媽媽不好嗎?我們好不好難道我自己不知道嗎?”那個人在展示柜旁邊的一把竹椅上坐下來,用兩只手抱住了腦袋。
“這些年來,我一直想著她,我畫她,用貝殼給她做各種各樣的小玩藝。我每天都想著她,給她點蠟燭、上香,而你呢?你和你哥哥為她做了什么?”他用手捂著臉哭了起來。
望著眼前這個男人,喬敏紅意識到自己確實并沒有每天都想著母親。他對母親也許真的比她做的要更好,她有些忐忑地想。不過,她漸漸清醒了過來。是他掐死了母親,他現在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謊言和矯飾。
“求求你,把這個展覽撤了,至少把與媽媽相關的這個部分撤掉,不要再對別人說你們有多么恩愛了。”她換了一種近于哀求的語氣對那人說。
“我不會把展覽撤掉!我沒有說謊!事情就是這樣的!”那個人突然間從椅子上跳起來,大聲地叫著。他閉著眼睛,還用雙手捂住了耳朵。
“不,不是這樣——”喬敏紅也高聲叫了起來。
“冷靜點,你冷靜點。”于醫生走過來,對喬敏紅說。他摟著那個人的肩膀,把他拉到了一邊。
“你把這個展覽撤了,我給你一筆錢。”他對那個人說。
“一筆錢?!”
“對,一大筆錢。”
那個人好像被腦子里那一大筆錢可能會有的樣子給迷惑住了,他的眼睛望著于醫生,但又好像沒有在看他,而是透過于醫生看到了他身后的虛空。
“我要錢干什么?”
“你可以用它到外地去玩玩,用它買你想吃的東西,想穿的衣服,甚至可以給自己蓋一座房子。”
“你想要用錢來收買我?你們是誰?你們到底想要干什么?”
好像有一股勁頭突然上來了,那個人跺著腳,揮舞著手臂指著于醫生大罵,他越罵越起勁,越罵越難聽。
“我們先回去吧。”看到那個人已經完全失控,于醫生尷尬地對喬敏紅說。
他們倆人跌跌撞撞地朝外面走去。穿過那些展柜走到門口時,喬敏紅回過頭來,看到那個人還在他們身后,他用手指著,暴怒地蹦跳著,在那里叫罵。
三
看著那兩個落荒而逃的男女溜出大門,他正在揮舞的手腳慢了下來。這個時候,他反應過來,戴眼鏡的那個男人是他女婿,而更早之前,他在海灘上看到的和他們在一起的兩個孩子應該就是他的孫子和孫女。
在進第四病院前,他曾做出種種奇怪的動作和表情,這些表情和動作在關鍵時刻拯救了他。到第四病院后,他看到了更多行為奇怪的人。不過這幾年,他已經很少做出這些發狂的表情和動作了。
說起來,他有些被自己給嚇到了。他根本沒想到,這么久了,這些動作仍在他身上潛藏著,仿佛它們已經內化在他的身體里,在他需要——不,是在他受到刺激時,它們就能如此輕易地被召喚出來,甚至連召喚都不需要,就自己跑了出來,似乎他身體里面隱匿著一個他無法控制的自己。
他又跺了一下腿,大聲地叫了幾下。那在別人聽起來肯定不正常的聲音穿過打開的窗戶擴散到了外面。他仿佛看到正離開這里的那兩個人都顫抖了一下。他的聲音穿過他們的身體后,又朝著海灘,向大海和海面上漂浮著的白云飛去。
這樣的景象真美啊!
走到樓上,在自己平常制作貝雕的工作臺前坐下來,他又一次念叨起女兒的名字。喬敏紅——他已經很長時間沒有看到她了。上一次見到她,是他正要從第四病院被放出來的時候。那時候,他已經習慣了用在病院時的姿勢走路,他咿咿呀呀地說話,用不是那么正常的眼神看東西,病院外的人可能會覺得別扭、難受,但其實他非常暢快。他感覺到極大的自由,甚至成為某種不為外人所知的快樂。
讓他覺得難受的是喬敏紅的眼神。十幾年前,喬敏紅用恐懼又帶著些嫌惡的眼神望著他。一直到現在,他都還記得女兒那時候的表情。他知道自己的樣子在她看來是會有一些可怕的。
喬敏紅讓他想起了喬敏華,和喬敏紅一樣,他也已經很久沒有見到喬敏華了。他聽他姐姐說,喬敏華大學畢業后就出了國,他現在在加拿大,幾乎不回來。除了隔一段時間會給他寄一點錢,他的兒子和女兒全躲著他。
他知道他們躲著他是因為什么原因。他知道孩子們恨他。孩子們的舅舅,還有現在已經過世了的老岳母也恨他。他們不愿意和他接觸,他覺得他們希望他一直被關在第四病院里,直到老死。
他嘆了口氣,看了看工作臺上已經快要完成的一個貝雕,那是用上百個大大小小的貝殼拼出來的一只老鷹。他是在第四病院的一張長條桌后面學會做手工的。在那里,他們做的是會飄雪的水晶球,還有駕著雪橇的圣誕老人,站在炮艇上,眼睛上蒙著骷髏頭遮眼布的海盜。他很喜歡把那些塑料做的小部件用膠水粘接在一起,再給它們刷上顏色。他記起自己曾經住過的寺廟,他在那里學會了畫畫和寫毛筆字,想起這些,他仿佛聞到了僧寮里揮之不去的香、墨水和顏料的味道,還有后山上草木被太陽曬過散發出來的氣息。
天色變得昏暗,他把工作臺上的臺燈打開,伴隨著燈光帶來的刺激,他感覺自己的心情又變得有些狂躁起來。
他想起他妻子,記起來那具在自己手里面癱軟掉的身體。即使是在第四病院里,一些時候,他也會明白自己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過錯。他確實感到過悔恨。他躺在地上,用手捶打自己的胸膛,撕扯已經變得很臟、打結的頭發。他抗拒吃飯,任由自己變得虛弱,直到病院里強制給他喂食。那時候,在眼前浮現出來的幻象中,他常常會看到那男人喝過酒,踉踉蹌蹌地走回到家中。
她不喜歡他喝得太多。一些時候,她會用冷漠來表達她的反感,但他并不在意她的感受。事情到底是怎么發生的,那男人并不是很清楚。他不懂得女人的脖子竟比一根海草還脆弱,不懂得人會癱軟得像一條海帶,可以任由他隨意塑形,等那男人明白過來時,一切都為時已晚。
他從工作臺前面站起來,有些迷狂地在屋子里轉圈。那個男人不是你,他告訴自己說。那男人在第四病院里,這里沒有那個男人。他轉了一圈又一圈,然后在擺放在窗臺前的那個柚木搖籃里躺了下來。那是一個頂部有著兩根長柱子的拜占庭風格的搖籃,四面欄桿上,纏繞著葡萄藤和葉子的紋飾。他躺在里面,兩只腳掛在搖籃尾部的欄桿上晃蕩著。
在黑暗中,他又一次看到了她。和樓下那幅他用海螺厴蓋拼成的圖畫上一樣,她站在海邊,用手扶著頭上的斗笠。傍晚的陽光灑在海面上,使得她看上去就像是正從一片金燦燦的光芒中走出來。
樓下的那些東西,他一開始并沒有太在意,只是隨意堆放著,一直到那個叫傅莉香的女人給他提出了建議。他記起傅莉香在他這里看到他撿來的那些老物件、炮彈殼,還有他的貝雕、圖畫時驚訝的表情。
“你可以辦一個展覽館的。”嘴巴很大,笑起來露出一口白牙的傅莉香對他說。他并不認識傅莉香,后來才知道她原來是劉金治的孫女。劉金治在他們村子里大名鼎鼎,和海峽對岸打仗時,劉金治是女民兵隊長,她曾經在海邊的山洞里抓到過從海里潛水上來的“水鬼”。
他不知道傅莉香為什么要把他的貝雕和圖畫,特別是那幅用海螺厴蓋拼成的畫像,拍下來發給別人看,但是他喜歡傅莉香的那一口白牙,所以他任由她和鎮上的人運來一些柜子,把自己的東西都擺放在里面展覽。傅莉香找來一塊舊船板,她本來是讓他在上面寫“愛情記憶館”的,但寫的時候,他想起了劉金治,不知道為什么感覺有些害怕,就把“愛情”兩個字改成了“海島”。
雖然對這樣的改動不太滿意,但傅莉香還是時不時地過來看他,幫他做一些事情。有一次,傅莉香帶過來一個背照相機的人,那個人在他屋子里拍啊拍的,把他給嚇著了,但傅莉香卻告訴他說,你很快就要出名了。
再到這里來時,傅莉香把手機伸到他面前,她指著上面的文字告訴他,有很多人喜歡他做的東西,還有他畫的畫。傅莉香還說,很多人被他對妻子的感情打動了。
一開始他不懂得傅莉香說的是什么,后來他就明白了。他知道他對自己的妻子很好,她去世后他一直思念她,他畫畫和做貝雕主要就是為了表達這些思念。
他記起來那個由很多人陪同到這屋子里來過的頭發灰白的老將軍,傅莉香后來告訴他,馮將軍曾經在兩岸炮仗時擔任過指揮官。老將軍對記憶館展出的那些彈殼和防空洞照片贊賞有加,夸獎他是一個有心人。聽了傅莉香的講解,在那幅海螺厴蓋畫像前,老將軍轉過頭去對著他身體有些佝僂的夫人微微頷首。
老將軍回去以后,過了十來天,傅莉香幫他從鎮上拿回來一個木頭盒子,那個包裝結實、沉甸甸的盒子里裝的就是那棵后來被他擺放在海螺畫像下面的紅珊瑚。
“這是那天來這里的將軍托部隊首長轉送給你的。”傅莉香有些激動地對他說,“就連將軍和他夫人都被你對妻子的感情打動了,他們希望這棵紅珊瑚能給我們的展覽館增加一些有價值的內容。”
回憶起這些,躺在搖籃里的他咧開嘴笑了。一切都停留在最美好的時刻,被遺忘的只有那段黑暗的歷史。如果說過去那個男人不懂得珍惜是真的,那現在,她是那個男人存在的全部理由也是真的。在過去,他也有點兒不太確信她長得是不是和他在圖畫上畫的一樣,時間太久了,她的容顏在他記憶中已經有些模糊,但現在他相信她就是他畫出來的這個樣子。在有些昏昏沉沉的思緒里,他覺得她一直保持在她最年輕、最美的時候也并沒有什么不好。說到底,人都是會去往那個世界的,他自己早晚也要到那里去和她見面。
躺在搖籃里,他覺得這搖籃就是海面上的一艘小船,一個漂流著的,正漸漸沒入到海中的棺柩。他沉入了睡眠。
醒過來的時候,窗外的天空已經變成了淡藍的顏色。從海上升起來的那輪月亮從窗戶照進來,他睜著眼睛,看到頭頂上,搖籃旁邊的空地上,到處都是一片一片的白。恍恍惚惚地,他想起來劉金治的葬禮。那個葬禮可真隆重啊!傅家的子孫跪在棺前哭成了一片,起靈時,被拋灑起來的紙錢在空中飄飄揚揚地飛著,就是這樣一片白色。
從第四病院回來后,有一次他在海邊小路上碰到了劉金治。那個有些嚴肅的老太婆盯著他,最后搖了搖頭。“你啊,做了那樣的壞事,以后死了都沒有人會為你哭一聲的。”劉金治對他說。
想起劉金治說的這句話,他心里有些難受。
四
這天晚上,傅莉香幫喬敏紅一家人做了好幾道海鮮,她把餐桌搬到二樓的大陽臺上,讓他們一邊欣賞晚霞一邊用餐。餐桌上的海味都很鮮美,螃蟹尖角里都是紅膏,九節蝦被沸水灼熟時尾巴一下子張得很大,可看著面前這一桌美食,喬敏紅卻一點兒胃口也沒有。
她一邊幫兒子把螃蟹的大螯剝開,一邊聽于醫生和兩個孩子說話。在孩子們面前,她不敢表露出自己的情緒,但事實上,她多少還是顯得有些低落。
二月份時,喬敏紅偶然在手機上讀到那篇文章,一開始,她并沒有太在意,但讀進去以后才發現這篇文章與自己有關。發現那文章之后,她不時在網絡上搜索“喬亞明”這個名字,結果吃驚地發現,有關那個人的文字越來越多。“讓人感動的老輩愛情故事”“愛能夠戰勝時間,超越永恒”“用淳樸藝術定格永恒之愛”……雖然大多數文章只是轉載的,但各個媒體和公號都在他們的推文里登出了那個人的照片和作品,聲稱這就是那一代人“最最感人的愛情”。
真可怕啊!她在心里面想,這個世界是怎么了?他們怎么能把那個人當成是愛情的楷模?她不明白那些記者和做公眾號的人為什么不到村子里去調查一下,了解下那個人的妻子到底是怎么死的?還是說他們去了,村里人對此諱莫如深,沒有人再愿意說出事情的真相?
看到那一篇文章,喬敏紅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給她姑姑打電話。從瑤臺島鎮政府退休后,雖然幾個孩子早就到城里面去生活了,但她姑姑一直還住在島上。姑姑是一個好心人——講起這一點,喬敏紅不知道為什么又有些不喜歡她——她在院子里面養鴨子,同時也花時間照顧那個人。姑姑就像是那個人的保護神。只不過去年夏天,姑姑在給她養的那一大群鴨子拋撒鴨食時不小心從露臺上摔了下去,六十五歲的老人家髖部和小腿骨折,后來被用快艇和救護車接力送到了城里。出院以后,她表哥就不讓姑姑一個人再住在島上了。
“你瞧這文章里說的都是一些什么啊?”在把內容簡單復述給姑姑聽以后,喬敏紅抱怨說。
姑姑那頭沒有反應。
“喂——”喬敏紅擔心電話是不是掉線了。
“我在聽呢。”姑姑說,“這么小一篇文章,我想不會有多少人去關注。”
“和篇幅大小沒關系,和多少人關注也沒關系,我是覺得不能這樣扭曲真相。”
在她又一次表明自己的看法后,姑姑同意去了解下情況,問問那個人網絡上那篇文章究竟是怎么回事。可過了很久,沒有任何一點結果。喬敏紅意識到,姑姑也許比她更早知道文章的事情,只不過姑姑沒有對她說。
她還給在多倫多的喬敏華發了封電郵。
“母親知道她的死被人這樣篡改,就是在墳墓里,她也會生氣得站起來的。”喬敏紅在電郵里對哥哥說。
“無論怎么樣,他都是我們父親,是他把我們帶到這世界來的。由他去吧,無論他怎么做,只要不再傷害人,我們就不必管他。”喬敏華回復說,“現在的科學如此發達,靈魂已經沒有可以依附的地方了。我們必須明白,母親死了就是死了,她不可能再感到憤怒,更別提什么在墳墓里站起來了。至于我們兄妹的感受,說到底也并不重要,我們要學會忘記自己是誰。”
喬敏紅被哥哥的回復給嚇到了。她意識到,在哥哥看似清晰的表述里,包含著一種深層的冷漠。當年在上海工作時,哥哥還會在春節時偶爾回瑤臺島一次,離婚以后,他春節也不回來了,后來更是去了加拿大。除了會通過姑姑不定期地給那個人匯一些錢,哥哥和瑤臺島其實已經沒有任何聯系。
她提醒哥哥互聯網的記憶會如何流傳下去,但這封郵件再發過去,哥哥已經不回復她了。“抱歉,我沒有時間,也不想在這事情上糾纏下去了。過去的一切就都讓它過去吧。”一個多星期后,喬敏華才用如此簡短的一段話回復她,結束了他們之間的那次通信。
把餐后水果端上來時,一直都很喜歡說話的傅莉香又熱情地問他們下午都去了哪里。“我們去游泳了。”小波搶著回答說。“這時候海水還有些涼呢。”傅莉香驚嘆道。“他們那不能叫游泳,只不過是在海邊玩了一會兒海水。”于醫生笑著解釋說。
看著傅莉香那張既熱情又愚蠢的臉,喬敏紅眼前又浮現出那個人下午對著他們嚎叫時瘋狂的表情。她實在沒有心情和傅莉香聊天,沒有吃完晚餐,就一個人提前上樓了。
在面朝大海的房間里,喬敏紅抬頭望向窗外。此刻,晚霞已經退去,月亮還沒升起,無邊的天幕上有些空蕩蕩的。
那人在第四病院時,她和哥哥只去看望過一兩次,后來舅舅就不讓他們去了。“這就是現世報。”舅舅對他們說。
其實,她自己也不想去。對舅舅和姑姑的矛盾,喬敏紅小時候的辦法是回避,她盡量不攪和到里面去。那個人要從第四病院出來時,喬敏華不肯回來,在姑姑的要求下,她和姑姑一起去了趟醫院。那時候天氣乍暖還寒,她穿著件薄羽絨服,但還是感覺冷。
考上大學,能靠獎學金和做家教的錢維持生活后,學哥哥的樣子,她也不怎么回來了。她很用功,幾乎把所有時間都用在讀書上。當考上研究生,同學們都向她祝賀時,只有她明白自己心里的恐懼與不安。睡不著覺的深夜,她常常聽著周邊的鼾聲和自己的心跳,無奈地望著宿舍的窗子一點一點變白。
在樓下,丈夫和傅莉香小聲地聊著什么,兩個孩子在樓梯上跑上來跑下去,更晚一些時候,她聽到他們在底樓和傅莉香的家人說話。一個大嗓門的男人,可能是傅莉香的父親答應兩個孩子明天帶他們坐船到海上去。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一兩聲犬吠,海風呼呼地吹著,襯托得漁村的夜晚有些凄涼。
她一直回避這段歷史,只告訴兩個孩子外公外婆都去世了,但是這一次,她感覺自己無法回避。一開始,她還以為這是在給自己一個面對真相的機會,根本想不到事情會弄得這么糟糕。
洗過澡,把頭發吹干,喬敏紅心神不寧地在沙發上坐下來,她面前的茶幾上,擱著于醫生帶過來的聚斯金德的《香水》。她好幾年前就已經讀過這部德國人的奇書,但這天晚上看到它,還是拿起來信手翻了一下。
喬敏紅翻到的是格雷諾耶被帶到行刑臺去的那一節。她一段段很快地讀著,腦海里浮現出書中描寫的那個怪異的場景:格雷諾耶看過去只是安靜地站著,面帶著微笑,觀看行刑的人卻無法控制自己。大家都被格雷諾耶的香水催眠了,男人們激動萬分,女人們也忍受不住,不聲不響地暈倒了。廣場上所有人都在最隱秘的幻想中用自己最強烈要求的方式,撫摸著自己的身體。
“所有人都被催眠了。”喬敏紅嘆了口氣,把書擱到一邊。
五
兩個孩子終于和于醫生一起上樓了,聽到他們的腳步聲,她走到門口,略有些嚴厲地讓兩個孩子趕緊去洗澡。望著自己的妻子,于醫生溫柔地告訴她不要著急,他會把兩個孩子安頓好的。
回到他們的大房間時,于醫生看到喬敏紅還沒有睡。房間里只亮著一盞床頭燈,喬敏紅斜靠在立起來的枕頭上,薄被子拉到了下巴上面。在昏暗的燈光中,于醫生看不太清楚她臉上的表情。
“你怎么還不睡覺?”假裝什么都不懂,于醫生問妻子說。
剛才在樓下,那個叫傅莉香的女人跟他聊瑤臺島掌故,說著說著就說到了海島記憶館。傅莉香驕傲地告訴他,是她最先發現了村里一個老人會做貝雕,后來在他家里,她又看到了他收藏的不少東西。當時她才從一個鄉村旅游示范點參觀學習回來,正想做一些事情,就以村里的名義幫老人申請到了鎮上的支持,還幫他做了很多宣傳。
“現在,這個記憶館已經成了我們村的一個網紅打卡點。”傅莉香驕傲地對他說。
雖然下午就已經去過那里,但于醫生沒有說。在傅莉香的描述里,那個人被描繪得既善良又有才華,還對亡妻十分深情。
等傅莉香說完,于醫生沉默了一會兒,問了個問題:“那老人家有沒有孩子?他就一個人住在那記憶館里面嗎?”他知道這個問題必然會涉及喬敏紅兄妹,打定主意想要聽聽傅莉香會怎么說。
聽于醫生這么問,傅莉香心里有一點小小的慌亂。她聽她父親說過,喬亞明妻子去世時,喬亞明也受了很大刺激,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城里的醫院和一個寺廟里調養,一直到十幾年前才回來。她聽說過喬亞明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可從來都沒看見過他們回來。這事情里頭,似乎有什么不對勁的東西,傅莉香自己也曾這么想過。
可沒有人去管這些,她也不愿意想得太多。傅莉香想要活得快樂,她愿意生活沿著一條美好的軌道朝前駛去,“愛情記憶館”——雖然后來被喬亞明寫成了“海島記憶館”——就是這條軌道會通往的美好的地方。
“他有兩個孩子。他們都很有出息,對他也很好,只不過回來得少一些,因為他們工作都太忙了。”傅莉香用對普通游客說的話來回答于醫生。一般來說,她這么回答也就夠了,沒有人會刨根究底地再問下去。
“是這樣啊?!他的孩子在哪里?他們很少回來,是不是因為他們的感情不好?”于醫生故意用一種漫不經心的口吻說。
“怎么會呢?他們都很孝順。如果我沒有記錯,他兒子好像在加拿大,女兒是在深圳。他們每個月都會給老人家打錢,假如他需要更多,只要掛一個電話,他們馬上就會把錢給他匯過來。老人之所以沒有去和他們住在一起只是因為他喜歡這里,喜歡他和他妻子一起生活過的地方。”傅莉香說。
她說的起碼在她的認識中是真的,因為喬亞明確實對她這么說過。傅莉香自行腦補了一些東西,后來漸漸地確信,所有這些都是真實的存在。
“那也許是我搞錯了。”于醫生對傅莉香說,“剛才聽你講起這個海島記憶館,我想起來我認識的一個人——哦,我忘記告訴你了,我就是從深圳過來的——那個人跟我說,她認識在瑤臺島上搞記憶館的這個老人,只不過她說,那老人的妻子是被她丈夫某一次酒后失手掐死的,和你說的情況有些不一樣。”
“您朋友是誰,他說的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傅莉香生起氣來,她對于醫生說,“但如果他誣蔑他人,無中生有地誹謗我們村的喬亞明老人,那我們是不允許的。說一個人殺人得有法律依據,您回深圳以后,請再問問清楚。要告訴您朋友不能亂說啊!那么多媒體報道過我們的記憶館,就連著名的老將軍都帶他夫人來參觀過,這些都不是假的,大家也不是那么好被糊弄的。”
于醫生本來還想要再說些什么,但望著傅莉香激動的手勢和表情,他知道對方肯定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就算他把自己和喬敏紅的身份亮出來,他們也沒辦法證實自己說的就是真相。在村里這么做,他估計除了自討沒趣,不會有任何作用。
越沒頭腦的人就越覺得自己正確,越沒頭腦的人就越容易感覺快樂,近幾年來,他常常會有這樣的感覺。想到這里,于醫生決定不再和傅莉香多說什么了。
“你說,一個人怎么可能把他的罪孽全都忘光,還要往自己臉上貼金?!”喬敏紅沒有回答于醫生,她抬起頭來,對丈夫抱怨說。
于醫生在妻子身邊坐下來,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手里。
“一個人只要一直浸泡在謊言里,就會把假的當成真的。”
“那怎么辦?就任他這么荒唐下去嗎?”
“要我說,也許我們該把這事情放下了。”于醫生把喬敏紅垂在眼睛前面的那縷頭發拂到她耳后。“不管事情的真相有沒有被扭曲,它對我們的生活都不會有根本上的影響,你沒必要非得計較這個事情。”
“這么說難道還是我錯了?”喬敏紅生氣地望著丈夫。依據在一起生活的經驗,她知道于醫生這么說,差不多意味著他在心里面已經準備放棄這件事情了。
“你沒錯,是他們錯了。只不過我們現在改變不了這里的情況。”
喬敏紅搖了搖頭。于醫生本來想要把自己在樓下和傅莉香的對話講給她聽,但想了想,他還是忍住了。
“那個人和網絡上那些海島愛情故事的傳播者已經成了一個整體,大家都在有意無意地參與到其中去。你有沒有覺得,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兩個人,而是一個龐大的‘無物之陣’?”于醫生說。
于醫生站起來,從放在茶幾上的煙盒里拿了一支煙。他把煙叼在嘴巴上,但并沒有點燃,只是把打火機拿在手上。
“可我真不甘心就這樣任由他顛倒黑白。”喬敏紅說。
“他年紀已經很大了,你就是由著他折騰,他又還能再折騰多久呢?你想想,再過十年,或許都不要十年,又有誰還會記得這些事情?后人看待我們現在,只會像我們現在看待古代一樣,他們看到的將會是一個整體,沒有人會去關注這些微小的細節,所以你并不需要特別在意。”于醫生安慰她說。
“你干脆直接說人生是沒有意義的算了。”喬敏紅把頭轉向另一邊,不再看著她丈夫。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人類的生命確實并沒有多大意義。”于醫生說。
他摁了下按鈕,把手上那個打火機打著,然后認真地凝視著,好像他從來都沒有看到過燃燒的火苗似的。把煙點著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讓煙從鼻腔進入到肺里,然后再從嘴巴里吐出來。
“面對這么荒唐的事情,難道我們真的就毫無辦法?”喬敏紅恨恨地說。
“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可是人生短暫,說實在的,你不要把時間耗費在這上面,我們盡量讓自己活得優雅就可以了。”
看著于醫生那副通透、世外高人般的樣子,喬敏紅越發感到難受,那種被挫敗了的痛苦的感覺又一次在她心里升騰起來。她垂下眼瞼,不想再說話了。
“要改變這事情,我知道該怎么辦,你應該也知道,只不過那樣做不一定合適。說真的,我們犯不著把精力消耗太多在這事情上面。”看到喬敏紅的樣子,于醫生俯下身來對她說。
喬敏紅咬著牙,她覺得淚水馬上就要奔涌而出了。
“時間會解決所有問題的。”于醫生拍著她的肩膀說,“我們睡吧,明天還要去給你母親上墳呢。”
背對著丈夫,喬敏紅假裝已經睡著了。側躺在靠窗的那一側,她放任自己的眼淚洶涌而出,濡濕了一大片枕巾。于醫生講的從理性角度來說并非完全沒有道理,可她就是不能接受。
無論怎么樣,她想,明天還是要再到那里去一趟,她想要去和那個人談談,雖然結果不一定樂觀,但她還是一定要去。
伴隨著窗外的潮汐聲,下半夜的時候,她迷迷糊糊地睡著了。在那輪澄澈的月亮的照耀下,喬敏紅感覺自己好像是行走在透明的水底。大海的聲音在她頭頂,那一輪明晃晃的月亮也在她頭頂。在散發著晶瑩光亮的海水中,她看到一些美麗的銀魚從她身前游過。突然間,在一棵很大的紅珊瑚樹旁邊,她看到了母親,就像是從那幅用海螺厴蓋拼起來的畫像上走下來的一樣,母親身上散發著金色的光芒。
“媽媽。”喬敏紅叫道。
母親臉上的表情有些痛苦,她好像想要對喬敏紅說什么,可才剛剛張口,喬敏紅就醒了過來。
回想起這個夢,在夢里還沒來得及看清楚的母親,喬敏紅心里越來越堵。她感覺胸膛里好像有一團火想要燃燒,甚至想要把什么東西徹底地毀滅掉。如果這個世界突然間就這樣被燒毀,喬敏紅想,她也不會感到有什么遺憾。
六
第二天早上,天才蒙蒙亮,喬敏紅和于醫生就走在了去往羊甲蹄的小路上。喬敏紅背著挎包,于醫生拎著個塑料袋,里面裝著香燭、紙錢之類的東西。掩門出發前,喬敏紅想,等他們回來,兩個孩子應該都還沒有睡醒。
之所以起得這么早,是因為于醫生不想帶兩個孩子一起去掃墓。在來瑤臺島之前,他就勸喬敏紅說,這一家族記憶最好在他們這代人手上就終結,不必讓下一代心里再有陰影了。
雖然懷有困惑,但喬敏紅還是同意了于醫生的意見。這一次來瑤臺島,兩個孩子都不知道這島嶼與他們有什么關系,他們都以為這只不過是一次普通的全家出游和度假。
漁村里此時只有一兩盞燈火。喬敏紅和于醫生沿著海灘,朝到處都是巖石和龍舌蘭的羊甲蹄方向走去。遠處的海面上,風力發電機長長的葉片就像巨人的手臂一樣緩慢轉動著。太陽還沒有出來,好像它正在他們看不見的地方與黑暗搏斗,天空中那一縷極淡的紅色也因此顯得特別珍稀。
“防空一號”里,小波比平時更早醒過來。他揉了揉眼睛,發現自己并不是睡在熟悉的床鋪上,睜著眼睛望了一會兒天花板上的吸頂燈,他這才想起來,原來他不是在自己家里,而是在一座海島的小旅館里。小波突然感覺很興奮,他一骨碌爬起來,用手去捏睡在他旁邊的思思的鼻子。把姐姐弄醒后,小波又笑著跳下床鋪,趿拉著拖鞋跑到外面。他試著擰了下他父母房間的門把,發現門并沒有從里面反鎖,輕輕推開一道縫,他探進頭去,這才發現父母親都不在里面。
他們居然沒有叫他和姐姐,就兩個人自己偷偷出去了。一開始小波非常難過,有點兒想要哭起來,但在房間里晃蕩了一會兒,他又變得高興起來。
“爸爸媽媽都出去了,我們也出去玩吧!”小男孩跑回到他和姐姐的房間,大聲對思思說。
兩個人小聲商量了一會兒,決定到樓下去看看昨天晚上那個大嗓門的男人在不在。如果在,他們就可以開船到海上去了。
傅莉香正在廚房里切菜,看到他們從樓上下來,她告訴兩個孩子于醫生他們去看日出了。傅莉香讓兩個孩子等一會,他們父母親一回來就可以吃早飯了。
小波眨巴著眼睛,點了點頭,問傅莉香那個會開船的男人在哪里。
“他到海邊去了。”傅莉香對小波說。
“那他什么時候會帶我們到海上去?”
“下午吧,他會帶你們一家人一起出海的。”傅莉香把煤氣灶的火打開,準備開始炒菜。
趁傅莉香沒注意,兩個小孩從院子里拿了兩塊滑沙板溜了出去,他們不想在旅館里等著吃早飯,想要先出去玩一玩。也許在海灘上,他們能碰到那個開船的男人,也有可能會碰到他們的爸爸媽媽。
昨天他們在海灘上玩了一整天。那座小沙山并沒有像喬敏紅說的那樣在夜晚自動恢復光滑和平整,“就像絲綢一樣”。望著沙山上到處亂糟糟的腳印,喬敏紅顯得有點兒窘,她略顯尷尬地對他們說,“按道理應該是會的”。和思思一起往海邊跑去時,又一次看到在他們面前出現的那一座沙山,小波忍不住笑了起來。
踩著滑沙板,小波和思思從回龍沙上滑下來,然后又從沙山側面繞上去,再一次滑下來。這樣來來回回玩了好幾趟,他們在夜里積蓄的能量才被消耗掉一點點。玩膩這個游戲后,兩個孩子把滑沙板扔在一邊,朝更前面的海灘走過去。
他們在海灘上撿了一會兒貝殼,但撿到的海螺和海星個頭都不是很大。一些時候,他們會看到白色的海鳥從空中掠過,它們個頭很大,而且會突然間俯沖下來,在海水里抓住什么東西,然后就飛得不見蹤影。海水正在退潮,小波和思思的光腳丫踩過濕漉漉的沙灘,在上面留下兩行淺淺的腳印。
他們用濕沙堆了一個城堡。正在給沙堡挖護墻河時,一個個頭矮小,穿著件半新不舊T恤的老頭兒突然間出現在他們身后。
“你們堆的這個房子看上去不錯嘛。”老頭子站在那里,雙臂抱在胸前,望著那個形體龐大的城堡評價說。
“這城堡非常結實,可以抵擋外星人的進攻。”小波對老頭子說,他姐姐思思在一邊笑著。
老頭子蹲下來,仔細欣賞了沙堡的城樓和圍墻。聽著老頭子夸獎他們,小波和思思都很驕傲。
“我有一個很好看的貝殼。”站起來以后,老頭子突然對他們說。他從口袋里掏出來一個花紋華美的虎斑貝,把這貝殼用手托到了兩個孩子面前。
小波手快,一下子先拿到了這個大虎斑貝。思思也湊了上來,他們兩個都被貝殼上面的花紋迷住了。
“哇,這貝殼好漂亮!你能不能送給我?”小波試探著問老頭子說。
“不行。”老頭子一把把虎斑貝又從小波手里搶了回去,放回到自己的褲袋里。眼睜睜地看著那個大貝殼消失了,小波心里好不情愿。
“我家里還有很多好看的貝殼,如果你們喜歡,我可以帶你們去看看。”老頭子對他們說。
“我們不能去。我媽媽交代過,不能跑得離這座房子太遠。”思思說,她指著沙山后面的一座房子,它在木麻黃防風林上面露出來一個尖頂和一個小小的十字架,那是村里的天主教堂。
“哦,沒有關系,我是你們外公,你們媽媽這會兒就在我家里等著你們呢。”老頭子說。
“不可能。”兩個孩子異口同聲地叫起來。
“我們沒有外公。”小波說。
“對,我媽媽說,我們外公老早就去世了。”思思也接著說。
老頭子突然間好像有些想要哭出來的樣子。
“她說得不對。”過了一會兒,他有些嚴肅地對他們說,“我女兒叫喬敏紅,她就是你們媽媽,我說得沒錯吧?”
兩個小孩愣住了。
“你是不是騙子?”小波警惕地問。
“你們仔細看一下,我和你們媽媽是不是長得很像?”老頭子有些不高興地說。
仔細打量站在他們面前的這個老人,小波覺得,她媽媽的鼻子和老頭子真的很像,思思也覺得,老頭子的眼睛和她媽媽一樣,都小而有神。
“可是,媽媽從來都是跟我們說外公已經死了。”思思說。
老頭子抬起眼睛,痛苦地望向天空。過了一會兒,他低下頭來,看著兩個孩子。
“那是因為我們之間有一個秘密。”老頭子說,“你們到我家里去,我就把這個秘密告訴你們。”
他們三個人從海邊,也就是前一天下午喬敏紅和于醫生走過的那條路朝記憶館走去。喬敏紅和于醫生去記憶館的時候,喬亞明就遠遠地跟在他們身后。他每天都會到海灘上去,很早就看到了在那兒玩耍的這幾個人,只不過那時候,他根本沒想到他們竟會是他女兒一家人。
思思不遠不近地跟在老頭子后面,好像擔心他萬一耍什么花招,她隨時就可以逃跑。小波則勇敢地走在前面,在老頭子指點下,他一路蹦跳著,最先跑到了那座堅固而又很有年代感的石頭房子前。
站在房子門口,小波朝里面探了探頭,又轉過身來。
“你騙我們,我媽媽不在這里。”他對老頭子大聲喊道。
“她剛才就在這里。”老頭子辯解說。他把兩個小孩帶進了屋子里。里面展示的那些東西很快就吸引了孩子們的注意力,他們在陳列柜前面東看看,西看看,開始時,在小波腦海里,還時不時地飄過一絲要找媽媽的念頭,但他很快就抵御不住眼前的誘惑,把媽媽并不在這里的事情忘到了九霄云外。
“你說的好看的貝殼在哪里?”突然間,小波記起來他來這里的目的,問老頭子說。
“樓上多得很,我們到樓上去吧。”老頭子說。
七
樓上的房間有些凌亂,工作臺上放著一只快要完工了的老鷹,還有各種各樣的工具。工作臺旁邊的桌子上,擺著一個玻璃柜子,里面有尖刺魚骨狀的骨螺,有馬丁長鼻螺,還有像團扇一樣的海樹,這些東西一下迷住了兩個孩子。
“這條蛇做得真好看啊!”小波指著一條用貝殼拼起來,昂著脖子,從嘴里吐出紅信的小蛇說。
“這只孔雀更好看!”思思拉著他,走到另一張桌子前,那里有一只也是用貝殼拼起來的藍孔雀,孔雀正在開屏,張開的尾翼上色彩斑斕。
“哇,這里還有一個這么漂亮的珊瑚!”小波指著另一個柜子上的紅珊瑚,驚喜地叫姐姐快過來看。他看到的就是將軍贈送給記憶館的那棵紅珊瑚,它原來擺放在樓下,早上被老頭子搬到樓上來了。
兩個小孩子到處亂看時,老頭子就斜靠在他那個搖籃里抽煙,他的頭倚著搖籃的柱子,腳蹺在護欄上,身體隨著搖籃的晃蕩舒服地搖擺著。
小波轉了一圈,他很喜歡那個紅珊瑚,可那東西看上去大了些,他怕老頭子不給,就想跟老頭子要那個漂亮的虎斑貝。和小波一樣,姐姐思思也在心里打著小算盤,不過,思思想的不是白要,她想要跟老頭子買那只用貝殼粘成的藍孔雀。她口袋里有一些錢,如果那只孔雀不是太貴,她也許買得起的。
“你可以把剛才那只貝殼送給我嗎?”小波走到搖籃前,問老頭子說。
“不能,我從來不送東西給別人。”老頭子擺了擺手。
聽他這么說,小波嘟起了嘴巴,很不高興。
“那你可以把這個賣給我嗎?”思思把藍孔雀捧在手上,問老頭子說。
“我也從不賣東西給別人!”
這個時候,小波突然間想起老頭子在海灘上說的秘密。“那你現在就告訴我們你剛才說的秘密是什么。”小波對老頭子喊道。他想,等聽完這個秘密,他和思思馬上就離開這里,回“防空一號”去找爸爸媽媽。
“你們不要著急。我這些東西從來不送人,也不賣給別人,不過,我可以送一兩件給我外孫和外孫女。”老頭子沒有理睬小波。他從搖籃里坐起來,晃蕩著身子對他們說。
小波和思思驚喜地互望了一眼。
“那我們就先謝謝你了。”思思有禮貌地說。
“你們不要客氣。”老頭子閉上眼睛說,“我這會兒累了,全身骨頭都覺得酸痛。你們能不能先給我搖搖搖籃?”
兩個孩子點了點頭。
“這搖籃是我爺爺從海上撿回來的。我父親在里面睡過,我在里面睡過,你們媽媽也在這里面睡過。”老頭子說。
兩個孩子聽得瞪大了眼睛,他們望著這個風格獨特的搖籃,一個用手去摸那根拜占庭風格的柱子,另一個用手摳了摳欄桿上浮雕的葡萄。
老頭子把拖鞋甩在地上,兩條腿都縮進了搖籃。他的個頭本來就不高,蜷縮著腳,他整個人在搖籃里面躺了下來。
“你們搖啊,幫外公好好搖啊!”他在搖籃里面大聲叫道。
思思和小波站在搖籃旁邊,小波握住頭部那端的柱子,思思扶著腳那頭的欄桿。兩個人搖晃著那個大搖籃。老頭子閉著眼睛在里面躺著,嘴巴哼哼著,臉上是一副很享受的表情。
“你現在該告訴我們那個秘密是什么了吧?”小波對老頭子說。
好像受到了驚嚇,老頭子突然睜開眼睛,望著他們。
“你們媽媽說你們沒有外公外婆,這不是真的,誰不是父母親生下來的呢?”老頭子對他們說。
“媽媽不是說我們沒有,她是說我們外公外婆已經死了,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思思糾正老頭子的話說。
“她在說假話!”老頭子說,“你們外公現在不是好好地就在你們面前嗎?”
“你怎么證明你是我們外公?”小波問。
“不是外公,我會送東西給你們嗎?”老頭子反問道。
“那媽媽為什么要那樣說?”小波疑惑地問。
“你們外婆去世時,她沒有哭,因為這件事情,你們媽媽被我狠狠地打了一頓,所以她在心里面記我的仇。”老頭子又從搖籃里面坐起來,“你們講講看,你們的外婆,她的媽媽去世了,她應不應該哭?”
“應該——”小波表態說。
“所有人都應該為親人去世感到難過。”思思也表態說。
“你們兩個都很懂事。你們比你們媽媽懂事多了。”老頭子對他們點了點頭,重新在搖籃里面躺下來。兩個孩子就仿佛接到了指令,又一人一頭扶住了搖籃兩端。
“要是你們外公死了,你們會不會哭?”老頭子問他們說。
“會。”
“我們會哭。”
兩個孩子一前一后說。
“那你們哭哭看。你們要真的會哭,你們想要什么我就送什么給你們。”老頭子說。
聽他這么講,兩個孩子朝不同的方向望去,他們分別看到了自己喜歡的藍孔雀和紅珊瑚,小波又望了望老頭子的褲兜,他一直想要的虎斑貝還在那里面。
咽了下口水,小波率先抽抽嗒嗒地假哭起來,思思也跟著弟弟開始假哭。一開始,他們都有些不好意思,哭得小心翼翼的,也沒有什么聲音。過了一會兒,他們兩個人對望了一下,都有些尷尬地笑了起來。
“你們哭得太小聲了。你們要哭得大聲,哭得有眼淚,我才會把東西送給你們。”老頭子在搖籃里面說。
在他的鼓動下,兩個孩子收斂起笑容,慢慢地大聲哭起來。不到一會兒,他們眼眶里就真的有了眼淚。
“哭啊!你們大點聲哭啊!誰哭得最大聲,我就把我最喜歡的那棵紅珊瑚送給他!”伴隨著他們的哭聲,老頭子在搖籃里面高興地喊道。
兩個孩子真的越哭越大聲,他們一邊哭,一邊按老頭子的要求叫著“外公啊——外公——”,老頭子閉著眼睛躺在搖籃里,咧著嘴興奮地享受著他們的哭聲。
人的情緒好像會互相感染,自動升級,這一天早上,兩個孩子越哭越難過,越哭越傷心,到了后來,他們已經控制不住自己,真的沉浸在悲傷的感覺中。孩子們拖得長長的哭聲飄出了那座石頭房子,飄過房子旁邊的那兩棵木麻黃樹,最后又順著海風飄到了更遠的地方。
八
喬敏紅和于醫生在羊甲蹄山上走岔了路。花了好長時間,他們才找到寫著喬敏紅母親名字的墓碑。于醫生拔掉墳上的雜草,喬敏紅把墓碑上那個名字用紅油漆重新描了一遍。在給母親燒紙的時候,喬敏紅又一次感覺到慚愧和懊惱,她原來是想要把事情處理清楚后再來掃墓的,可現在,事情最后到底會怎樣,她心里并沒有數。
蹲在紙錢燃起的那簇火焰前,喬敏紅想起晚上曾經在自己夢里出現過的母親,她是以那個人用海螺厴蓋拼起來的形象出現的:母親戴著斗笠,看上去像是籠罩在一片金光中,但她臉上的表情是那么痛苦。喬敏紅難過地想,母親并沒有留下照片,去世時自己又太小,她現在真的連母親長什么模樣都記不起來了。
從羊甲蹄兩側長滿荊棘的小路往回走時,喬敏紅和于醫生遠遠地聽到了從村子上空飄過來的哭聲。
“這是什么聲音?”
她疑惑地站住,豎起耳朵仔細傾聽。
“是不是村里有老人去世了?”
于醫生也聽到了那拖得很長的哭聲。
隔著很遠的一段距離,兩個孩子的哭聲又和平時的聲音不太一樣,喬敏紅和于醫生都沒能聽出來這就是小波和思思的聲音,但在回去的路上,疑惑和不安還是像一團陰郁的黑云,一直籠罩在他們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