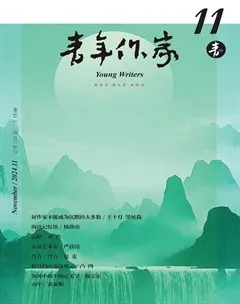離歌
一
在尚未遠逝的往昔時光里,我的家鄉川西平原橫無際涯的田園村舍和形形色色的舊式農具曾經是極為尋常卻又別具風味的物象,它們長短互補,協力作為,共同構成具有時代辨識度的傳統農耕生活標識。彼時,以“東方紅”耕犁拖拉機和腳踏式滾筒谷麥脫粒機為先遣的農業機械化跫音已由遠而近。如果把舊式農具比作田野上嘈嘈切切錯雜彈撥的一曲離歌,那曲調實在是十分老派了。樂章已轉入尾聲部,弦韻依然錚琮婉約,卻有了余音裊裊的況味。
那些鐵制、石制、木制、竹制甚至草芥編制的農事器具,品類枚不勝數,形制千奇百怪。勢如弓弩,或貌似月牙,或狀若指爪,或獨木一痕,或如楷書提鉤,或一軸連心。它們既是昔日歲月里拙樸的鄉土物像,又構成原始田園詩情畫意的豐饒意象。它們大多身形局促,單薄伶仃,甚至微小到竟可一握,與宏大、壯觀、慓銳、重器一類溢美之詞沾不上瓜葛,但卻各自身懷獨門絕技,暗蓄種種潛能。一旦被熟諳農事的莊稼人信手操持、因物施用,借助某個支點,某個角度,某個順勢而為的機巧,輔以人力恰到好處的助推與把控,它們即刻蓄勢爆發:耕耙、掘挖、栽培、斫削、刈割、擔挑、推拉、碾磨、捶搗,無所不能。四兩撥千斤,由微至漸,是它們的看家本領和拿手好戲。千百年來,田野上的每一季萬物生長,農家倉廩每一輪五谷豐登,都少不了它們的鼎力奉獻。
翻開歷史的籍冊,逆著時間之流追根溯源,你不能不對這些舊式農具肅然起敬:它們作為鄉間農事的實用器物,與我們的祖先已經風雨同舟數千載。“彎彎犁頭水牯牛”的農耕方式,起源于距今5000多年前。“耒耜”的發明者是偉大的神農氏(炎帝)。據《周易·系辭下》記載:“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以今人眼光審視,耒耜的雛形粗陋至極:一根尖頭木棍,加上一段短橫梁,使用時把尖頭插入土壤, 用腳踩橫梁使木棍深入,然后翻泥松土。但在遙遠的上古時期,這卻是炎帝驚鴻一瞥下的靈光乍現,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睿智創舉。耒耜由中原地區推而廣之,神農氏率先垂范,教化部落族人躬耕土地,播種五谷,從而結束了先民漫漫歲月漂泊無定的游牧生活,開啟了原始農耕文明的悠悠先河。繼而,是石器、鐵器、瓷器之類農具的陸續發明和應用,牛馬的馴化和田間馭使……
屏息聆聽,每一枚舊式農具在大地上的每一聲叩擊,都縈響著中華農耕文明亙古傳承的悠悠神韻。
二
大約是十多歲的年齡吧,我對家鄉那些舊式農具的加工制作產生出濃厚的興趣。憑借智竇初開的鄉村少年天然的嗅覺和獵奇的目光,我幾乎洞悉到各式鄉土農具來路的蛛絲馬跡,并深為個中蘊含的種種意趣所折服,陷入難以自拔的癡迷。
木犁,無疑是集體化生產年代農具中的扛鼎之物。在我們永興公社四大隊二生產小隊,幾十戶人家,近百畝耕地,很長時間僅擁有兩柄老舊的犁頭。第三柄新木犁,一直等到那個瑞雪紛飛的冬季才姍姍來遲。
木工房設在四面透風的曬煙房里,師傅是單槍匹馬的魏木匠。那些日子,鄉村小學正放寒假,我成天泡在那間曬煙房,饒有興趣地守著魏木匠,看這個滿額皺紋、雙手粗糲的老漢怎樣把一團榆木疙瘩搗鼓成一副彎彎犁頭。魏木匠的工具攤放在帆布口袋上,一覽無余,無非是幾枚斧、鋸、刨、錘、鑿。榆木疙瘩是生產隊提早派人上青嘴山精挑細選砍伐回來的成材樹干,長成自然弓弧形狀。在池塘里浸泡兩月,又待其慢慢陰干,木質的張弛度恰到好處。眼下,它如同一只溫馴的小獸,靜靜伏臥在木馬架上,期待魏木匠點化。魏木匠瞇縫著雙眼,將木材細細打量一番,卷起袖口,不緊不慢動作起來。先是鋸掉多余的枝節,剝鏟厚厚的樹皮,然后揮動斧頭,因循榆木本身的曲線,斫出木犁的粗略輪廓,再換用刨子,沿著犁弓、犁底的平面和脊背小心翼翼地推刨。隨著節奏疏朗的霍霍之聲,刨花連綿翻卷飄落,地上泛開馨香撲鼻的木屑波浪。犁弓和犁底由兩個獨立部件合成,沒用一寸鐵釘和一滴化學粘膠,魏木匠鑿一個孔口,削一段木榫,將二者天衣無縫嵌為一體。犁底端頭精心琢成尖嘴蝙蝠狀,方便日后套裝鐵鏵。扶手末端剜成略微的半弧,這樣,耕作時田把式穩握一柄,即可驅使千鈞畜力。此外,又格外配制一副馭牛的駕擔、軛絆、千斤板,以及一段“腳跟棒”……如此復雜的工藝,魏木匠沒用墨盒彈畫一根墨線,手邊也沒有一張設計圖紙。每一個環節早已爛熟于心,他只需要一邊動作,一邊稍加冥想,工藝流程就如山澗清流般順暢自然,款款有致。魏木匠做犁耙的手藝遠近聞名,他家是專制犁耙的世家。當然,魏木匠也許并不清楚木犁制作的太祖師爺可以追溯到神農氏那里,他是個沒上過學堂的文盲,不會生出那樣的懷古幽思。魏木匠手上動作不急不躁,是慢工出細活的節奏。做一個把鐘頭,他會閑息一會兒,抽一管葉子煙,跺跺腳,搓一搓凍僵的耳朵鼻頭,看看飄舞的雪花;偶爾還打破年歲上的疏隔,跟我呱嗒幾句。然后,悠悠地繼續他的匠心演繹。就這樣,從下料到完成最末一道工序,打一副木犁,魏木匠整整耗用了六天時光,直到雪后日霽,直到田野里厚厚的白絮融化殆盡。陽光下,新木犁身骨上每一寸線條都那樣柔和舒展,打磨細滑的木料泛動著玉器一樣的光澤。不得不說,看上去,那實在是一柄盡善盡美的好犁頭。
木器農具中,制作相對輕而易舉的是削鑿扁擔和鋤柄。這些家家戶戶的必備農事家當,對用材似乎沒有特別講究。田埂上和村院邊隨地可見的桑、柳、槐、杉、黃楊、雜木之類,只要能取到三五尺長沒有疤痕的端直枝干,即可取為制作扁擔的坯料。鋤柄的用料需要稍微硬邦一點,檀木或是榆木、棗木皆可,也是鄉野尋常之物。做工甚為簡單,斫、鑿、削、刨,幾道工序即成。可是,真要制作出一條能省力的柔韌適度的好扁擔,一根鋤地勞作不蹭手傷皮的好鋤柄,卻并非一件易事。得遇上所選的樹木生長到最好的年輪,而用作坯料的那一段枝干剛柔度恰到好處,沒有蟲蛀疤癤;此外,還要依憑制作者做工上對粗細厚薄的分寸拿捏。故此,鄉人把能制作和擁有一條可心的扁擔、一柄如意的鋤頭當作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機緣。偶有所得,滿心歡喜,愛不釋手。趕緊用小刀在扁擔頭深深鏤刻上自己的尊姓大名,以防別人混淆或被眼熱者“順手牽羊”。
石器農具的打造,是一個格外艱辛而且枯燥乏味的過程。一只石磙、一扇碾輪、一副磨盤、一口碓窩,村里的那位胡茬花白的老石匠(抱歉,我實在記不起他的名字了)總是先從親自選料開始。他為此足跡踏遍了全生產大隊的溝河坡坎,甚至尋到幾里地以外的亭江水畔。老人最喜歡的石料是青石或麻黑色花崗巖,瓷實且剛硬,做出來的石器經碰磕,耐磨損。老人雕鑿大宗石質農具,往往在野外某處一眼選中一墩石頭,就地開工,一連數天,在露天場地一鏨鏨地雕琢。老人下手的力道拿得很穩,石面上密密麻麻的凹凸痕紋粗細均衡,線條輻射勻稱,絕不會因粗疏而鑿出一點豁缺。直到一件石器琢磨告成,才請人搬運到某家院子或某個集體場地安裝投用。我除了偶爾路過湊上前瞄一眼,沒有耐性守著老石匠,聽他從早到晚一錘一鏨撥弄出來的單調綿長的金石聲。我的關注點在于那些石器被抬回來安裝投用之時。那一瞬間,亙古沉默的石頭恍若注入了神力,躍然活泛起來。農家屋檐下,兩扇磨盤唇齒咬合,下靜上動,默契地悠悠旋轉,細碎的米面隨之從磨隙如雪霰紛落;剛分蘗的小麥苗壟間,石磙跟著牯牛屁股后面滴溜溜打滾壓青,力道恰如其分;水碾坊里,被木軸牽引的碾輪借助水勢循環周而復始,咿咿呀呀,哼一曲古老的歌謠。
竹器農具,它們投胎到鄉人院落,顯然是更為隨機的散淡之事。幾乎每一個成年的鄉間男人,都能無師自通編織這類物什。這方面,同院鄰居卿二爸是我尤為佩服的高手。一天勞作之余,消夜之后,但凡月明星耀的夜晚,卿二爸總是抽一條長腿板凳坐在院壩中央,夜光像夢幻的水露覆灑在身上,盈汪在腳下。卿二爸用篾刀把從自家竹林盤砍來的毛竹破節成條,一層層地剔去頭黃篾、二黃篾,再剝成粗細的絲縷。然后,以黃篾為骨架,青篾作經緯,十個指頭一陣令人眼花繚亂的盤繞,竹子的精靈隨之舞蹈,幻化,蝶變……籮筐、篩簸、背簍、箢篼、曬席、連枷、竹耙,五花八門的竹制農具或粗陋,或玲瓏,一件一件從卿二爸的手中變魔術一樣誕生。除了滿足自給,卿二爸農閑去李家碾趕集,會用擔子挑上幾件,賣了錢供娃娃交學費和換些油鹽醬醋的家用。
而草編蓑織定然是村婦們的專利,因為這類的手工少不了翹著小指頭穿針引線,那需要一種上天賦予的女性陰柔特質。在村子院落間信馬由韁奔走的日子里,我像瀏覽連環畫一樣,津津有味品賞了這樣的一幅幅場景:
春日暖陽下,有婦人在院中鋪了門板織蓑衣。從山里剝來的棕櫚樹皮晾曬梳理得油光水滑,攤在門板上,像是剪裁規整的布料。婦人用大號的錐針引著搓捻的棕繩,伏著身子,把毛茸茸的棕樹皮一片片串綴起來,一層層縫合嚴實,衣擺上收下敞,再鎖一圈緊扎的領口,一件斗篷狀的蓑衣便成了模樣。女主人會為家中每一個男勞力量身定做一件這樣的衣裳,從此,每逢風雨連天的日子,男人們下田耕犁勞作,身上就有了嚴實的庇護,就可免卻濡濕傷寒的襲擾。蒙蒙煙雨之中,一個個穿蓑戴笠的身影佇立于田畈之間,酷似古代披掛鎧甲征戰沙場的剽悍將士。
炎炎夏日,年輕媳婦坐在一團樹蔭里,懷里奶著孩兒,手中捋著金黃的麥草。麥草取自田疇秸垛,是新麥脫粒后的余物,還散發著田野植株的幽幽清香。年輕媳婦把麥草秸一條條除盡殘葉,反復搓揉、捏扁、拉直,然后,像早先做姑娘時給自己編麻花辮子那樣,將麥秸捋出幾縷頭緒,翹著蘭花指纏繞編扎,再將草辮兒一圈一圈盤起來,往上拱出一彎穹窿,最后,連綴細密的針線。趁著好心情,或許又在帽檐用彩線繡兩朵蓮花或一對喜鵲。一頂草帽,就這樣像碩美的蘑菇朵冉冉綻開。
鄉間制作農具,棚場動靜最大的是鐵匠鋪。壟畝躬耕,與泥土直接對話,十有八九靠鐵,更準確地表述,是鐵與木聯袂而成的銳器。種種锃亮剛硬的金屬農具,統統出自鐵匠鋪。當年,故鄉唯一一家鐵匠鋪開在李家碾下場口。我們從鄉下去趕集,跨越一條路基高壘的小火車鐵軌,再繞過一座水碾坊,便有激越的叮當之聲如雷貫耳。一溜低矮舊陋的瓦頂棚房坐落在街口路邊,門柵上掛個招牌,墨筆書寫著“永興公社鐵器社”幾個大字。看得出,寫招牌的人一筆一畫下筆很努力很用心,但一行字卻實在丑得不敢恭維。陣陣熱氣裹挾著濃重的粉塵,從空洞的窗口往路面一浪浪卷撲而出,路過的人稍不留神就被煙渣瞇了眼瞼。少年人毫不在意,好奇心驅使我多少回趴在窗戶上往里看稀奇。作坊里凸起一座古墓般的爐臺,一千多度的高溫烈焰在爐膛里呼哧呼哧吐著火舌,焰光紅里透白,亮得讓人不敢直視。鐵匠兩人一組散布在作坊鋪滿渣屑的地坪上,他們輪流用長臂鉤鏟從爐膛中拽出煅燒夠了火候的坯料,橫呈于敦實的砧臺,一人蹲下,用鉗夾翻轉挪移通紅的熟坯,一人蹬著弓箭步,口中嘿哈吼著號子,按著節奏,奮臂猛掄錘敲砸。紅光一點一點從坯料上隱退。再回爐煅燒,再錘砸。鐵器漸漸成型,最終完成鑄造:寬鋤、窄鋤、斧頭、鐮、鍬、鏟、耙……一枚枚被扔進水池淬火,激起幾縷青煙。泫然出水時,每一枚都泛著烏青色的冷光。
后來才知道,鐵匠要鍛造一把成器的物件,一些考究的細節遠非我兒時粗枝大葉晃眼所見那么簡單。做一把鋤頭或刀斧,需要用到兩種金屬。首先是用柔韌而延展自如的軟鐵打造物件整體形狀。爾后須在刃的部分添加碳性鋼,以增加鋒利硬度,這正應了那句民間諺語:“好鋼用在刀刃上。”兩種金屬在工匠手工錘煉下渾然互融,構成合金體,了無任何“拼湊”的痕跡。這樣精妙奇巧的匠藝,在那間簡陋作坊里,不過是匠人們舉手投足之間的尋常功夫。而鏵犁頭的來路又另辟蹊徑,它由工匠先熬煉好生鐵水,再澆入預制好的翻砂模具。鐵水冷凝之后,鑄制的鏵犁頭脫穎而出,形如展翅欲飛的銀色羽雁。
勞作中的鐵器社工人,他們一概身系皮圍裙,大多光著臂膀。星星點點的火花不斷迸濺在他們肌膚上,卻沒一個人驚怪躲閃。特殊的作坊冶煉環境,塑造了一尊尊雕塑般剛毅的粗獷軀體,他們擁有超乎常人的堅韌與抗御能力。鐵匠鋪畢竟不是風和日麗的太平之地,曾聽大人說,某年某天,一個16歲的學徒在爐臺前不幸被一粒飛濺的鐵水花濺到手腕上,虻蟲一樣咬住動脈。殷紅的熱血頓時像決堤般噴濺而出,令學徒和在場所有人大驚失色。熟諳醫道的人事后喟嘆:如果當時孩子不要自亂方寸,及時死死掐住出血口前端,再有別人迅即用繩索幫他緊勒小臂,將他平躺急送醫院,人八成有救,頂多廢一只胳膊。然而,面對突降的險厄,小學徒完全抓狂了。他狼一樣哀嚎著奪路往鎮衛生院狂奔,導致心脈搏動加劇,噴涌的熱血如一尾長蛇,跟著他一路蜿蜒。剛跑過半截街,血已流盡,人頹然倒地,氣絕身亡。一場意外,雖然足夠驚悚,卻在人們街談巷議和搖頭惋惜一些日子之后被漸漸淡忘。鐵匠鋪的運轉并沒有被擾亂,每一天,不絕如縷的叮當錚響仍然是街鎮平寧生活的執著伴奏。盡管干的是工人活計,也按月領薪資,鐵匠的本質身份卻仍然脫不了“農民”的皮殼。人民公社把這群能工巧匠從各生產大隊調集上來,讓他們聯合從事鐵制農具加工,滿足集體生產的需要,但是公社無權變更他們的身份“所有制”。生產隊大小春決算分配前,他們得把工資交回隊里抵計工分,如此,方能分配到一份農村口糧。
三
舊時鄉間的農具,就是這樣一件一件從普通莊稼人和鄉村匠人手中源源產出。它們是土生土長的物類,與后來的機器制式化產品相比,顯得愣頭愣腦,甚至難掩細節上的某些粗鄙。即便是同一類農具,它們的品相也是千差萬別。其個性化的造型,與制作和使用者的不同境況和內心意圖息息相關。比方說,高個子的農夫必然需要修長的鋤棍和扁擔,嬌小的村姑下田刈割谷麥不會揮舞一把大號鐮刀,彪形壯漢墾荒鑿石掄甩的肯定是一柄重磅鐵錘。
各式農具一旦“成器”,便隨時聽從征召,與鄉人共赴田間地頭,成為那個年代農業“生產力”的重要一分子。彼時,僅僅用“勞動工具”來界定它們的屬性是遠遠不夠的。它們附體于莊稼人,化身為他們延伸的手足、拓展的肩臂、可折疊的腰身、成倍放大的體力和能持之恒久的耐力。它們挺身在前,竭力為躬耕者遮擋烈日寒風霜露雨雪,代為承受其肌膚肢體的磨礪與艱辛,幫助躬耕者抵達單憑肉身不可能抵達的勞作愿景。
當年在故鄉,我發現,每一位鄉人都對他長期使用的農具情有獨鐘。無論挑、背、鋤、刈、推,他們順手操起的家伙什,總是慣用的那一個。他們說,嘿,這家伙跟我投緣,順手,合心!細瞧鄉人常用的農具,長日的肌膚摩挲會洇出一層烏黑,器質中透著濃重的汗水味和某位農人的特殊體味。那些頗有年頭的鋤镢,把柄部分已經浸潤了包漿,有絲縷紋路隱約可見,分不清是凸顯的木紋還是拓印的指紋。
人與物日久情深,農人對他們心愛的農具是敝帚自珍的。在生產隊集體出工的田間勞動場景里,我曾看到有鄉人挑糞的扁擔用到綻了裂痕仍不離不棄。在裂口處襯上一段木片,用絲麻密密纏繞,就像接骨療傷那樣,讓一根扁擔的壽命得以延續。某個黃昏,我還曾看到二生產隊的林隊長在溪邊青石板上打磨一柄鋤頭。那鋤頭掘到土中硬物,傷得不輕,鋤刃有一半卷了口。林隊長抖掉卡子,將鋤板卸下來,低伏腰身,雙手摁著鋤板,反復地、使勁地磨礪,直到石板被磨出乳汁一樣的石漿,直到卷口漸漸復歸平展,鋤刃重新煥發灼灼鋒芒。
收工以后,農具跟隨各自的主人從一天的艱辛勞作中抽身出來,跟人一樣,一下子變得松弛,不再像奮勇發力時那般緊繃繃的樣子。鄉人在溪溝邊洗濯自己的手腳,同時也會為農具們凈身,把它們裹身的泥團和污穢淘洗干凈,讓它們也落得通體清爽。回到家院里,鄉人會井然有序、分門別類擱置農具。籮筐套著扁擔放在糧囤旁,鋤頭一順溜倒掛在柴屋架桿上,鐮刀鉤啄在房門后,蓑衣斗笠則像水墨畫一樣張掛在堂屋墻壁上。我少年時幾乎逛游過二生產隊的所有鄉鄰院子,從未見過哪家人對自己的農具輕浮地胡亂扔放。
一個成年勞動力一年到頭需要在田地里像陀螺一樣連軸轉,忙乎不休。而農具們則是依順農時的更迭輪番上陣。因此,它們往往就有些日子是處于“半寐”狀態的。犁頭大展身手的日子在每年大小春耕墾期,鐮刀籮筐扁擔和石磨盤在糧食收割季節最是吃勁,鋤頭出勤率相對最高,因為田野里有關掘挖的農事實在是數不勝數;但寬鋤窄鋤尖頭鋤,也總還有輪番派用場的間隙。在農具的輪休期,鄉人通過一些溫情脈脈的方式讓它們享受呵護保養。完成耕作的犁頭鋤頭,會被懸在干燥的土墻半腰,以免受潮遭蟲蛀。過了收割季,鐮刀要用干燥的稻草包裹起來,防范銹蝕。曬席用過后要疏松裹卷,擱置到通風透光的瓦檐之下……
白駒過隙,世事滄桑。如今,新農村大田耕種已全面實現機械化、智能化。故鄉成立了農業公司,土地實行集中經營,大多村民都不再自營耕地。那些舊式農具,在鄉村原野上已失去用武之地,它們的蹤影正在悄無聲息地從歲月的沙漏中消逝。但是,這種消逝似乎還帶著一些不甘,留著種種牽掛。近日偶爾回鄉,去一些村舍走親訪友,每每看見,某些舊時農具依然固執地存留在鄉人屋舍的一隅,上面蒙了厚厚的塵埃。有一回,聽一位表親說,他年逾八旬的老父親,至今丟不掉一個習慣:除開雨雪日,每天早晨一起床,老人總要扛把鋤頭去田野里走一圈,盡管這片田地的經營管理權屬已與他無關。老人就這么扛著鋤頭在田野里無所事事地走動,時不時,下意識地在田邊地角扒拉幾鋤。“失地”迄今已過六個年頭,老人這樣的行舉一直不曾中斷。
【作者簡介】潘鳴,四川省德陽市人,作品發表于《四川文學》《青年作家》《散文》等刊,著有散文集《花間一壺茶》《故鄉不老》;現居德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