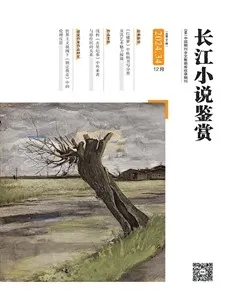約翰·伯格小說《G.》中唐·璜形象的拉康式重寫研究
[摘 要]約翰·伯格的小說《G.》以實驗性敘事風格和對社會歷史的深刻剖析而著稱。主人公G.是現代版的唐·璜,游蕩于歐洲各地,在不斷的情感經歷中逐步走向自我覺醒。本文探討伯格如何通過拉康精神分析的視角重寫唐·璜這一經典形象。首先,伯格增補了童年經歷,剖析G.作為私生子在父母長期缺席、監護人忽視及缺乏社會互動的情況下,固著于“理想自我”。其次,伯格賦予G.成年后行為以拉康式動因,特別是“父之名”的除權與亂倫禁忌的打破,使G.表現出對權威和社會秩序的持續反叛,并通過引誘女性回應內在的匱乏。最后,伯格通過增補G.的身份認同危機,揭示其在欲望驅動下的無根漂泊與身份迷失。伯格的重寫打破了傳統唐·璜形象的單一性,賦予其新的哲學與倫理內涵。
[關鍵詞] 《G.》 " 唐·璜 " 拉康 " 精神分析
[中圖分類號] I06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34-0057-04
唐·璜這一形象自16世紀以來,已成為西方文學與藝術中的經典符號。從特佐·德·莫林那的《塞維利亞的嘲弄者》到莫里哀的戲劇、莫扎特的歌劇,再到后世眾多改編,唐·璜作為放蕩不羈、蔑視道德與宗教的浪蕩子形象廣為流傳[1]。約翰·伯格的小說《G.》在1972年獲得布克獎,主人公G.被視為唐·璜神話的現代復現[2]。伯格通過重塑這一形象,突破了唐·璜單一的傳統刻板印象,將其塑造為一個多維的、充滿心理沖突的復雜角色。G.不僅是引誘者,更是一個深陷心理問題和身份認同危機的主體,其行為不僅展現了個人的道德困境,也揭示了社會秩序的瓦解。本文將探討伯格如何通過拉康精神分析視角重寫唐·璜這一經典形象,揭示其復雜的心理動因與身份危機。
一、增補童年經歷
在傳統敘事中,唐·璜通常以成年后的放蕩不羈和蔑視權威示人,仿佛這些特質與生俱來。傳統故事往往聚焦他與社會秩序的沖突,卻忽略了其性格形成的早期背景。在《G.》中,伯格不僅描繪了G.成年后的行為,還通過補充童年經歷,揭示了早期生活對他性格和行為的深刻影響。
1.私生子身份與父母的長期缺席
主人公G.的私生子身份不僅象征著他在社會中的邊緣地位,還對他的心理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G.的父母,意大利的果脯制造商翁貝托和他的美國情人勞拉,在G.尚未出生時就因撫養問題產生了激烈沖突。勞拉堅定地剝奪了翁貝托的撫養權,堅稱:“我打算按照自己的方式撫養我的孩子,而不是按照你的方式……你沒有任何權利參與他的成長。”[3]因此,G.從出生起便生活在單親家庭,父親完全未曾參與他的撫養和成長。
雖然勞拉最初決心獨自撫養G.,但現實很快打破了她的承諾。在G.的嬰兒時期,勞拉通過母乳喂養試圖與他建立深厚的情感紐帶,這也是G.通過母親的注視和互動逐步形成“理想自我”的關鍵時刻,由此獲得對自我認知的基礎。然而,隨著勞拉對G.的情感投入逐漸減少,轉而專注于自己的事業,她決定將G.送至倫敦鄉下交由堂兄弟姐妹撫養,母子的情感聯系隨之疏遠,探視也逐漸減少。
母親的缺席對G.的心理成長產生了巨大影響。拉康的“鏡像階段”理論指出,嬰兒通過與母親的互動逐步構建自我意識,母親的回應在此過程中至關重要[6]。勞拉的逐漸疏離使G.未能在這一關鍵階段完成穩定的自我認同。他的自我意識固著在“理想自我”階段,即一個虛幻的、理想化的形象,而這一形象難以與現實契合。因此,G.從小就感受到一種持續的“欠缺”,這一情感源于他嬰兒時期未能獲得足夠的情感支持與認同。
2.監護人的忽視與社會互動的缺乏
當G.被母親勞拉送到喬斯林和比阿特麗斯的農場后,雖然環境改變了,但他未能得到應有的關愛與指導。喬斯林和比阿特麗斯作為監護人,本應承擔起照顧和教育的責任,但各自的心理困境和生活局限使他們難以勝任這一角色。姨母比阿特麗斯的生活幾乎全部圍繞著日漸衰敗的莊園展開,內心封閉,生活單調,難以與G.建立情感聯系。舅舅喬斯林則代表著沒落貴族精神的殘余,固守著狩獵和馬術等傳統,象征著他對往日榮光的頑固堅守以及對現實的逃避。作為象征性父親的角色,喬斯林表現得無力且矛盾,未能為G.提供真正的情感支持和引導。更為復雜的是,喬斯林與比阿特麗斯之間的亂倫關系,給年幼的G.帶來了弗洛伊德意義上的“原初場景”心理創傷(即目睹父母交媾)[4]。盡管當時的G.尚無法理解這一情境,但它已在潛意識中埋下了困惑和不安。
此外,監護人的忽視導致G.在兩歲到五歲期間多次更換家庭教師,無法與任何人建立穩定的、健康的情感聯系。五歲時,海倫小姐進入G.的生活,成為他的情感寄托。G.對海倫小姐的依戀逐漸加深,甚至接近早熟的“戀愛”。伯格寫道:“五歲或六歲的男孩如果失去了父母,沒有任何親近的養父母或兄弟姐妹,他可能會因為孤獨而墜入愛河。”[3]在這種情感孤立中,G.將海倫小姐視為唯一的“他者”,并通過她構建自我認同。“鏡像階段”理論指出,個體通過他者的“鏡像”來建構自我認同[5]。由于父母長期缺席,養父母情感冷漠,海倫小姐彌補了G.對母愛的空缺,成為他認同的對象。然而,這種依戀關系并未得到正確引導。當海倫小姐突然被替換時,G.沒有得到任何解釋或情感撫慰。“男孩不尋求解釋,也沒有人給他解釋。”[3]這一事件使得G.的情感發展再次遭遇創傷,也因此使G.的自我認同依舊停滯在“理想自我”。
在倫理混亂與情感疏離的環境中,G.未能獲得應有的情感支持與社會互動,使其自我發展固著于“理想自我”,加劇了他內心的孤獨與“欠缺”,并為他成年后的行為埋下了伏筆。伯格通過增補童年的書寫,深刻揭示了G.這一角色的復雜性,為理解唐·璜這一經典人物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二、賦予成年行為以拉康式動因
傳統的唐·璜行為常被視為天性的自然流露——蔑視權威、追逐欲望、引誘女性。然而,G.成年后的行為并非單純的放蕩與反叛,而是其深層心理動因的外在顯化。伯格通過拉康的精神分析視角,深入刻畫了G.的內在動因,尤其聚焦“父之名”的除權與亂倫禁忌的打破。
1.“父之名”的除權
主人公G.的成年行為與“父之名”的除權緊密相關。根據拉康的理論,父親通過“父之名”的介入打破嬰兒與母親之間的二元關系,發出禁令,限制嬰兒對母親的欲望,從而引導其進入象征秩序。“父之名”作為能指,象征著法則和禁忌,通過語言引導個體融入社會結構,建立與他者的聯結[6]。父親在“象征界”中的作用至關重要,它決定了個體如何通過符號體系適應社會規范。
G.的生父翁貝托和“養父”喬斯林都未能有效履行這一父性職能,導致G.缺乏必要的象征性引導,未能認同社會規范。翁貝托在G.的成長過程中長期缺席,而喬斯林雖然作為“養父”存在,但他在父性功能上的失敗尤為明顯。喬斯林沉迷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逐漸衰落的貴族傳統,試圖通過狩獵等儀式將貴族父權的象征傳遞給G.,但這種努力注定無效。
在狩獵情節中,喬斯林與G.的互動揭示了其父性功能的崩潰。當喬斯林對獵犬說話時,他的聲音堅定而溫和,而對G.時卻顯得猶豫不決[3],這反映了喬斯林對G.的忽視和不信任。當喬斯林試圖通過“hup!hup!”的呼喚讓G.融入貴族狩獵傳統時,G.卻“依然像之前一樣,冷漠地回復,沒有他舅舅那種密謀般的熱情”[3]。喬斯林的呼喚象征著“父之名”的召喚,但G.的冷漠反應表明了他對喬斯林及其所代表的“象征界”傳統的拒絕。喬斯林的父權象征在G.面前的失效,不僅揭示了他個人層面的失敗,也反映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歐洲貴族父權象征的整體衰落。
G.在童年和少年時期,未能通過翁貝托或喬斯林完成象征性“閹割”,因此無法完成對“父之名”的認同并形成穩定的“自我理想”。這一缺陷使他在成年后對社會秩序和父權權威產生持續反抗。
2.亂倫禁忌的打破
根據拉康的理論,象征性“閹割”是主體進入象征秩序的關鍵環節。若這一環節未能完成,俄狄浦斯情結將持續存在,個體的欲望無法得到有效規訓。此外,“父之名”的除權使主體無法在與母親的欲望關系中被正確命名[6]。在G.的成長過程中,由于父性功能的缺失,他與比阿特麗斯和喬斯林之間形成了俄狄浦斯式的“三角關系”。在多個場景中,G.對比阿特麗斯的依賴與好奇流露出他對母性欲望的迷戀,如他對喬斯林反復提出“你為什么不贊成比阿特麗斯姨母的婚姻”[3]等挑釁性問題,預示了后來亂倫行為的發生。
G.與比阿特麗斯的亂倫象征著他與“象征界”秩序的徹底決裂。亂倫禁忌作為這一秩序的核心被打破,意味著G.從此無法維持穩定的主體身份。“這次遭遇徹底摧毀了他們兩個人。他們原有的關系將永遠不再存在。”[3]從此,G.脫離了“象征界”秩序,成為游離于其外的邊緣人。更為重要的是,這一事件喚醒了G.的欲望意識。通過亂倫,他意識到引誘女性可以暫時填補內在的“欠缺”。自此,G.由困于母性欲望的少年轉變為成年唐·璜,欲望成為他生活的核心動因,促使他走上無盡的欲望追逐之路。
三、增補身份認同危機
在經典文學中,唐·璜通常被刻畫為一個放蕩不羈、藐視社會規范的誘惑者,其叛逆身份似乎無可置疑:他是一個徹底的反叛者。然而,在伯格的《G.》中,G.不僅繼承了唐·璜的叛逆與引誘行為,還揭示了一種更深層次的自我認同危機。這種危機源于他未能通過象征性“閹割”認同“父之名”,從而使他始終游離于社會秩序之外,成為一個“無根”的存在。
1.反抗傳統權威與秩序
G.對傳統權威與社會秩序的反抗體現在多個層面,尤其在舞會復仇情節中達到高潮。G.帶著努莎,這位社會底層的斯拉夫女子,出席了一戰前的最后一場慈善舞會,此舉不僅是為了發泄未能成功引誘瑪麗卡的挫敗感,更是對上流社會“蓄謀已久的”的挑戰,同時表達了他對即將崩潰的奧匈帝國權威的蔑視。
對G.而言,引誘女性不僅為了滿足欲望,更是挑戰權威、尋求自我認同的手段。當他未能成功引誘瑪麗卡并侮辱她的丈夫哈特曼時,便選擇在更公開的場合揭露上流社會的虛偽。G.帶著努莎進入上層社交場合,打破階級和種族的界限,故意違反禮節,挑釁哈特曼夫婦。“他先向努莎介紹哈特曼先生和哈特曼夫人。”[3]這一舉動明顯表露出他對上流社會禮節的蔑視。接著,他帶著努莎在舞池中肆無忌憚地起舞,完全無視賓客們的憤怒和嘲諷,用挑釁的姿態表達反叛。賓客們試圖通過舞蹈和音樂暫時逃避戰爭的陰影,G.的行為卻刺穿了這種虛假的平和。
G.與努莎共舞,巧妙侮辱了象征奧匈帝國權威的精英階層。“他想通過侮辱和反抗他們來表達這種厭惡感。但他明白,公開侮辱或威脅他們,甚至喊叫或開槍,只會讓他們覺得可笑,并進一步確認自己的立場。”[3]G.深知,單純的憤怒無法真正撼動權威,因此選擇狡猾的挑釁來表達他的反抗。這種反抗背后隱藏著深層次的身份認同危機與未解的欲望沖突,反映了G.內在的迷失和對象征秩序的疏離。
2.四處游蕩與對國家和政治的冷漠
根據拉康的理論,“父之名”的除權會使個體失去與社會的聯結感,導致主體無論身處哪個群體,都無法擁有歸屬感,反而感到被排斥在外[6]。G.正是這樣一個“游離者”或“局外人”。由于未能認同“父之名”,他始終徘徊在象征秩序之外。G.并不關心國家或社會責任,而是被內在欲望驅使,四處漂泊,追尋冒險。
一戰爆發后,G.回到倫敦,雖然物質條件優越,但他始終感到不安與焦慮:“他急于離開倫敦,正如他最終總是急于離開自己所在的任何城市一樣。”[3]這種焦慮源于他內在的身份認同危機。G.的內心空虛無法填補,而他與比阿特麗斯的亂倫記憶和罪惡感進一步加劇了這種不安,迫使他不斷遷徙,追尋新的欲望目標。當G.接受威爾莫特-史密斯的間諜任務,前往的里雅斯特時,這一決定并非基于政治或國家利益的考慮,而是為了逃離倫敦的壓抑,尋找新的冒險。正如伯格寫道:“令威爾莫特-史密斯驚訝和不安的是,G.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提議,沒有要求進一步解釋。”[3]G.的行動完全由欲望驅動,他坦言:“我不相信那些偉大事業。”[3]到達的里雅斯特時,盡管戰爭陰影籠罩,G.卻感到興奮:“他無法想到自己正身處敵國領土……他有一種受控的興奮感或緊張感,這種感受本身或聯想都讓人愉悅。”[3]每一座城市、每一場冒險對他而言,都是欲望的舞臺。最終,他卷入了危險的間諜活動,并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四、伯格拉康式重寫唐·璜的意義
伯格通過精神分析的視角探討了G.內在的心理動因及社會背景,重寫了經典的唐·璜形象,為這個廣為流傳的人物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相較于傳統的唐·璜形象,伯格打破了過去的扁平化和刻板印象,塑造了一個更為復雜、充滿心理沖突的角色。此外,這一重寫使唐·璜不再僅僅是傳統道德教訓的象征,而且具有了欲望倫理學的深層意蘊。
1.打破扁平化與刻板印象
在傳統文學和藝術中,唐·璜常被簡化為一個追求享樂、最終因放縱受懲的浪蕩子。然而,伯格在《G.》中突破了這種單一化塑造。他筆下的G.并非僅僅為了享樂而引誘女性,而是源于內在的“欠缺”以及與“象征界”的斷裂。G.的引誘不僅是對欲望的滿足,更是對內在匱乏的回應。他的行為背后藏有未解的欲望與情感創傷,而非簡單的道德挑戰。通過對G.心理的剖析,伯格賦予了這一形象更多層次感和生命力。
此外,伯格解構了傳統道德框架,避免了簡單的道德懲罰。與唐·璜被拖入地獄的結局不同,G.的死亡象征他游離于“象征界”之外的邊緣人命運,而非道德上的勝利。通過重塑G.的復雜心理,伯格為這一經典形象注入了新的深度,使唐·璜成為一個充滿矛盾與欲望的現代人物。
2.超越傳統道德教訓的欲望倫理學意蘊
G.不僅繼承了唐·璜的引誘者特質,伯格還通過拉康的精神分析視角賦予這一角色更復雜的倫理內涵。通過重塑這一角色,伯格突顯了拉康的“不要向你的欲望讓步”這一倫理學命題。盡管G.的生命以悲劇告終,但他的最終轉變標志著對欲望的重新認識,超越了傳統唐·璜故事中的簡單道德教訓。
“不要向你的欲望讓步”意味著主體不應屈從于欲望,而應直面欲望的真相,認清“象征界”和“想象界”中幻象所支撐的欲望滿足的虛幻性和不可能性[7]。伯格展示了G.從屈從欲望到覺醒的過程。最初,G.作為典型的唐·璜式人物,通過引誘女性和挑戰權威追求虛幻的自我確認,試圖掩蓋內在的匱乏。然而,在的里雅斯特目睹的革命,促使他反思自己的欲望,并逐漸意識到過去的引誘和征服只是虛幻的滿足。在小說的結尾,他逐漸擺脫了自身欲望的束縛,并積極參與到游行示威的人群之中。他的死亡不僅是傳統道德中的懲罰,更是他通過重新定位欲望和承擔責任所走向的必然結局。
五、結語
約翰·伯格在《G.》中通過拉康精神分析的視角重塑了唐·璜這一經典形象,使其突破了傳統道德教訓的框架,展現出新的復雜性與生命力。通過增補童年經歷,并深入剖析成年行為背后的心理動因與身份認同危機,伯格揭示了G.的內在沖突與游離狀態。G.的故事不僅象征著欲望與反叛,更引發了對欲望、身份和社會責任的深刻思考,為唐·璜這一經典形象賦予了全新的哲學與倫理意義。
參考文獻
[1] 楊利亭.唐·璜形象流變考:一個浪蕩子的前世今生[J].臨沂大學學報,2024,46(4).
[2] 斯珀林.約翰·伯格的三重生命[M].李瑋璐,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3] Berger J.G.[M].London:Vintage,1991.
[4] 霍默.導讀拉康[M].李新雨,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22.
[5] 拉康.拉康選集[M].褚孝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
[6] 王潤晨曦,張濤,陳勁驍.鏡子、父親、女人與瘋子:拉康的精神分析世界[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3.
[7] 吳瓊.雅克·拉康——閱讀你的癥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責任編輯 "夏 "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