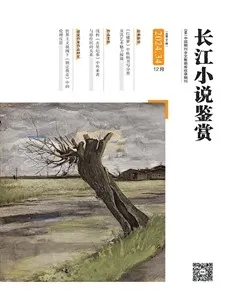《傷心咖啡館之歌》中殘疾人物的多重異化
[摘要]二十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美國(guó)南方社會(huì)處于轉(zhuǎn)型過(guò)渡時(shí)期,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方面發(fā)生明顯轉(zhuǎn)變的同時(shí)也給當(dāng)?shù)厝藥?lái)了巨大的精神沖擊。美國(guó)南方殘疾女作家卡森·麥卡勒斯的作品多以殘疾人物、怪誕情節(jié)等為特點(diǎn),借此表現(xiàn)美國(guó)南方人在轉(zhuǎn)型期沖擊下的焦慮感,其短篇小說(shuō)《傷心咖啡館之歌》正是一部反映此主題的作品。本文立足于殘障研究,從性別、道德、情感三方面解讀小說(shuō)中的殘疾人物,深刻體會(huì)麥卡勒斯筆下殘疾人物的存在意義與作用,揭露美國(guó)南方舊社會(huì)瓦解后轉(zhuǎn)型時(shí)期的殘疾人物在現(xiàn)代性焦慮下映射出的性別身份、道德操守和情感表達(dá)異化的社會(huì)狀況。
[關(guān)鍵詞]《傷心咖啡館之歌》 " 殘疾人物 " 多重異化 " 性別 " 道德 " 情感
[中圖分類(lèi)號(hào)] I106.4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 " [文章編號(hào)] 2097-2881(2024)34-0067-06
一、引言
卡森·麥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被認(rèn)為是二十世紀(jì)重要的美國(guó)南方女性作家之一,作為一位飽受病痛折磨的殘障作家,她的作品中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殘疾人物,以凸顯二十世紀(jì)美國(guó)南方人在社會(huì)轉(zhuǎn)型時(shí)期的不安與絕望。
《傷心咖啡館之歌》(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是收錄在同名小說(shuō)集中的一篇短篇小說(shuō),主要講述了美國(guó)南方新舊社會(huì)轉(zhuǎn)型時(shí)期斗雞眼愛(ài)密利亞小姐、駝背羅鍋李蒙和精神殘疾馬文三個(gè)殘疾人物之間復(fù)雜的三角戀故事。
《傷心咖啡館之歌》自出版以來(lái)備受學(xué)界關(guān)注。學(xué)者早期大多關(guān)注的是文本中怪誕的風(fēng)格和精神隔絕的主題。隨著二十世紀(jì)七十年代女權(quán)主義批評(píng)等后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的興起,麥卡勒斯的小說(shuō)開(kāi)始被納入女權(quán)主義批評(píng)等領(lǐng)域。到了二十一世紀(jì),學(xué)界對(duì)麥卡勒斯及小說(shuō)的研究越來(lái)越深入,一些學(xué)者從殘疾人物等角度來(lái)研究麥卡勒斯筆下“畸形的”南方社會(huì)。
近年來(lái),隨著民權(quán)運(yùn)動(dòng)的興起,殘障研究進(jìn)入了西方文學(xué)批評(píng)的舞臺(tái),并逐漸引起了廣大學(xué)者的關(guān)注。楊國(guó)靜指出,“殘障包含身體功能和結(jié)構(gòu)上的‘殘損’(impairments)、個(gè)體生活或行動(dòng)所面臨的‘活動(dòng)受限’(activity limitations)、個(gè)體參加社會(huì)生活所遭遇的‘參與受限’(participation restrictions)三個(gè)維度”[1]。也就是說(shuō),文學(xué)中的殘障研究更多是從社會(huì)和文化的角度對(duì)作品中出現(xiàn)的殘障角色或殘障作家進(jìn)行深入研究。麥卡勒斯本人在她的文章《開(kāi)花的夢(mèng):寫(xiě)作筆記》中認(rèn)為,她選擇描繪的“怪誕人物”是“那些身體上的無(wú)能象征著他們精神上無(wú)法愛(ài)或接受愛(ài)的人”[2]。她認(rèn)為,選擇殘疾人物不僅更能表達(dá)出作品中“精神隔絕”的主題,同時(shí)也映射出美國(guó)南方社會(huì)轉(zhuǎn)型給人們帶來(lái)的沖擊。
《傷心咖啡館之歌》中,人物出現(xiàn)了多重異化,例如愛(ài)密利亞小姐的性別異化,李蒙表哥和馬文的道德異化,以及三個(gè)殘疾人物的情感異化。本文立足于殘障研究,從性別、道德、情感三方面解讀小說(shuō)中的殘疾人物,深刻體會(huì)麥卡勒斯筆下殘疾人物的意義與作用。
二、性別身份的異化:南方淑女之死
南北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之前,在以家庭為單位的經(jīng)濟(jì)制度下,“‘神話’光環(huán)下的南方是一片伊甸園樂(lè)土,其標(biāo)志性的畫(huà)面是溫馨的大家庭、舒適的種植園生活和優(yōu)雅的南方淑女”[3]。
南北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之后,形成了新南方社會(huì),奴隸制被取締,種植園經(jīng)濟(jì)逐漸被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取代,“南方神話”不復(fù)存在。麥卡勒斯作為二十世紀(jì)美國(guó)南方的代表作家之一,其生活和寫(xiě)作的年代正是舊社會(huì)逐漸瓦解后的轉(zhuǎn)型時(shí)期。她作品中的殘疾人物形象比如啞巴辛格、有偷窺癖的二等兵威廉姆斯、因中風(fēng)偏癱的老法官等人物都傳達(dá)出一種新舊社會(huì)交替間的恐懼感與不安感。這種恐懼與不安來(lái)自舒適自得的種植園經(jīng)濟(jì)與“南方家庭羅曼斯”的瓦解,以及南方紳士與南方淑女形象的消逝。與此同時(shí),比夫、米克、愛(ài)密利亞這類(lèi)性別界限模糊的人物面臨性別異化的問(wèn)題。《傷心咖啡館之歌》中,本該是南方淑女的愛(ài)密利亞小姐在現(xiàn)代性的沖擊下,被麥卡勒斯刻畫(huà)成一個(gè)斗雞眼且男子氣概明顯的殘疾人物,進(jìn)一步佐證了“南方神話”的幻滅和往日南方淑女形象的顛覆。
《傷心咖啡館之歌》開(kāi)篇就描寫(xiě)了破敗、冷寂的南方小鎮(zhèn),小鎮(zhèn)的正中心有一棟全鎮(zhèn)最大的房子,這棟房子主人的臉看起來(lái)“蒼白、辨別不清是男是女,臉上那兩只灰色的斗雞眼挨得那么近”[4]。這就是小說(shuō)中的女主人公——愛(ài)密利亞小姐。
從外表看來(lái),愛(ài)密利亞是一個(gè)異于常人的、長(zhǎng)著斗雞眼的、身體有殘疾的角色,在崇尚紳士、淑女的南方小鎮(zhèn)中,她顯然是一個(gè)另類(lèi)。愛(ài)密利亞的另類(lèi)之處不只體現(xiàn)在她的畸形表征上,還體現(xiàn)在她的雙性同體上。不同于“南方神話”光環(huán)下對(duì)女性的要求與期待——成為溫柔、優(yōu)雅、順從、服務(wù)于家庭的南方淑女,愛(ài)密利亞這一形象的出現(xiàn)恰恰體現(xiàn)南方社會(huì)轉(zhuǎn)型時(shí)期女性對(duì)固有身份形象的顛覆。
愛(ài)密利亞具有十分明顯的男性特征,“她是個(gè)黑黑的高大女人,骨骼和肌肉長(zhǎng)得都像個(gè)男人。她頭發(fā)剪得很短,平平地往后梳,那張?zhí)?yáng)曬黑的臉上有一種嚴(yán)峻、粗獷的神情”[4]。她每天的裝束就只有“工褲和長(zhǎng)筒雨靴”[4]。到了做禮拜的時(shí)候,她會(huì)換上深紅色的連衣裙,但“這裙子掛在她身上,樣子很古怪”[4]。湯姆森(Garland-Thomson)提出,愛(ài)密利亞的服飾習(xí)慣被人們認(rèn)為是“通過(guò)異裝癖和拒絕規(guī)范界限所創(chuàng)造的新的權(quán)力形式”[5],即從外形特征和日常穿搭來(lái)看,成功的愛(ài)密利亞更像一個(gè)男性,這種新型的“權(quán)力形式”對(duì)男性乃至男權(quán)社會(huì)造成了威脅。愛(ài)密利亞小姐的雙性同體特征還體現(xiàn)在她作為一個(gè)女性卻會(huì)對(duì)婦科類(lèi)疾病產(chǎn)生羞愧感。當(dāng)有人因?yàn)閶D科病找上她時(shí),“她的臉就會(huì)因?yàn)樾呃⒍稽c(diǎn)點(diǎn)發(fā)暗,她站在那兒,彎著頸子,下巴頦都?jí)旱搅艘r衫領(lǐng)子上,或是對(duì)搓著她那雙雨靴,簡(jiǎn)直像個(gè)張口結(jié)舌、無(wú)地自容的大孩子”[4]。
《心是孤獨(dú)的獵人》中,比夫的雙性同體被等同于“藝術(shù)意識(shí)”,而愛(ài)密利亞的雙性同體卻被認(rèn)為是“怪誕的、怪異的、古怪的”,這種想法使雙性同體這類(lèi)范例變成了一種“壞”現(xiàn)實(shí),因?yàn)榇藭r(shí)的雙性同體和愛(ài)密利亞小姐都被貼上了“怪胎”的標(biāo)簽[5]。無(wú)論是從有缺陷的外表還是從明顯的男性化特征來(lái)看,愛(ài)密利亞小姐都是一個(gè)異類(lèi),這從側(cè)面說(shuō)明現(xiàn)代性帶來(lái)的沖擊使愛(ài)密利亞與“南方淑女”的概念相悖。
在兩性的關(guān)系中,女性一直處于男權(quán)制度壓制之下他者的位置,因而女性又常被認(rèn)為是“殘缺的男性”(mutilated males),只能作為“畸者”(monstrosity)存在[6]。女性和殘疾人都被視為社會(huì)中的他者或者沒(méi)有任何話語(yǔ)權(quán)的邊緣人物,因?yàn)椤岸呔灰暈閷?duì)標(biāo)準(zhǔn)或規(guī)范的背離”[6]。愛(ài)密利亞小姐本身的女性形象就是一種“殘缺”。
在美國(guó)舊南方社會(huì)中,廣泛意義下這種“殘缺的男性”應(yīng)該恪守“南方淑女”的本分,但愛(ài)密利亞很顯然并沒(méi)有做到。同樣是殘疾人的美國(guó)南方女性麥卡勒斯,在刻畫(huà)和她相同身份的殘疾女性時(shí)摻雜了自己對(duì)舊南方社會(huì)貶低女性、殘疾人以及女性殘疾人的一種質(zhì)疑和反抗。
愛(ài)密利亞繼承了父親的產(chǎn)業(yè),獨(dú)自經(jīng)營(yíng)著釀酒坊、鋸木廠等,她還自己灌豬肉腸、做木匠活,“她成了方圓幾英里內(nèi)最有錢(qián)的女人”[4]。在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興起的南方新社會(huì)中,愛(ài)密利亞堪稱(chēng)實(shí)現(xiàn)美國(guó)夢(mèng)的完美典型。她的富有和成功也挑戰(zhàn)了男權(quán)制度,“愛(ài)密利亞身上的男性氣質(zhì)是南方小鎮(zhèn)乃至整個(gè)父權(quán)制社會(huì)二元性別觀的集中體現(xiàn)”[7]。
愛(ài)密利亞作為小說(shuō)中唯一的女性主人公,代表了一種反常態(tài)的邊緣人。南方社會(huì)轉(zhuǎn)型時(shí)期,舊社會(huì)所期待的“南方淑女”形象已經(jīng)不復(fù)存在,愛(ài)密利亞的生理性殘疾與身體殘疾更加加速了這類(lèi)形象的消逝,愛(ài)密利亞的性別身份被異化,小說(shuō)中,“帶有男子氣質(zhì)的‘女強(qiáng)人’逐漸取代了傳統(tǒng)的‘南方淑女’”[3]。
三、道德操守的異化:李蒙與馬文的道德缺失
麥卡勒斯作品中出現(xiàn)的殘障角色具有隱喻意義,例如怪誕和殘疾人物表現(xiàn)的是新舊社會(huì)轉(zhuǎn)型時(shí)期“身份形成過(guò)程中的焦慮”[5]。研究麥卡勒斯的學(xué)者曾從美學(xué)角度指出,麥卡勒斯是通過(guò)“身體缺陷隱喻‘精神上的相互隔絕’”[8]。米歇爾和辛德研究法國(guó)批評(píng)學(xué)家安托萬(wàn)·德巴克(Antoine de Baecque)的“物質(zhì)隱喻理論(theory of the material metaphor)”時(shí)認(rèn)為,身體被控制在固定意識(shí)形態(tài)的過(guò)程中實(shí)際上會(huì)被嵌入象征意義中,例如“畸形代表著惡意的動(dòng)機(jī)”[9]。《傷心咖啡館之歌》中,駝背羅鍋李蒙和精神殘疾的馬文正代表了他們道德層面的惡意。
駝背羅鍋李蒙的道德異化主要表現(xiàn)在對(duì)愛(ài)密利亞的忘恩負(fù)義和對(duì)馬文的盲從上。《傷心咖啡館之歌》中,麥卡勒斯對(duì)李蒙的身體殘疾進(jìn)行了細(xì)致的描寫(xiě):“那人是個(gè)駝子,頂多不過(guò)四英尺高,穿著一件只蓋到膝頭的破舊襤褸的外衣。他那雙細(xì)細(xì)的羅圈腿似乎都難以支撐住他的大雞胸和肩膀后面的那只大駝峰。他腦袋也特別大,上面是一雙深陷的藍(lán)眼睛和一張薄薄的小嘴。”[4]
作為小鎮(zhèn)的外來(lái)者,李蒙初次出現(xiàn)時(shí)因?yàn)樯眢w殘疾被稱(chēng)為“走散的牛犢”[4];最后加入決斗,從柜臺(tái)跳下來(lái)時(shí)他被形容“生出一副鷹隼翅膀”,他“鳥(niǎo)爪般細(xì)細(xì)的手指”[4]死死抓住了愛(ài)密利亞。李蒙的殘障形象被動(dòng)物化,而他也被描繪成“一個(gè)兼具人性和動(dòng)物性的混雜物”[8]。
通常殘障形象都有隱喻道德缺失的作用,例如查恩斯將理查三世的身體畸形視為“道德畸形的表征”[10]。同樣,李蒙的殘障特征也具有隱喻道德異化的功能。美國(guó)殘疾研究學(xué)家湯姆森在《非凡的身體》中指出,道格拉斯區(qū)分殘障群體的第四種方式就是將其貼上“危險(xiǎn)標(biāo)簽”。湯姆森認(rèn)為,《傷心咖啡館之歌》中表哥李蒙這一形象的出現(xiàn)實(shí)際上就是一種“對(duì)社會(huì)秩序釋放的危險(xiǎn)力量”[5]。
證明李蒙是危險(xiǎn)的最有力的證據(jù)就是小鎮(zhèn)的平靜因他的到來(lái)而被打破,尤其是愛(ài)密利亞的生活被攪得天翻地覆。愛(ài)密利亞對(duì)李蒙悉心照顧與明目張膽地偏愛(ài),李蒙卻因?yàn)轳R文去過(guò)亞特蘭大、坐過(guò)大牢而向馬文倒戈,最后“他們干了一切他們想得出來(lái)的破壞勾當(dāng)”[4]。
從李蒙的道德素質(zhì)來(lái)看,他的身體殘障演變?yōu)椤耙环N特殊的道德上和身體上的丑陋”[11]。由此可見(jiàn),麥卡勒斯借李蒙的殘疾諷刺了轉(zhuǎn)型時(shí)期的美國(guó)南方人的道德喪失。
心理畸形者馬文的道德異化表現(xiàn)在對(duì)社會(huì)規(guī)約的違背和對(duì)李蒙、愛(ài)密利亞的戲耍方面。在這個(gè)復(fù)雜的三角關(guān)系中,愛(ài)密利亞的前夫馬文不僅是造成愛(ài)密利亞最終悲劇的罪魁禍?zhǔn)祝切≌f(shuō)中道德缺失的代言人。馬文的畸形之處在于他心理的畸形,而他的心理畸形從最開(kāi)始就有跡可循。
愛(ài)上愛(ài)密利亞之前的馬文一直游手好閑,口袋里還裝著一只風(fēng)干的耳朵,而這只耳朵的主人“與他用剃刀格斗,被他殺了”[4]。少年時(shí)期他就虐待小動(dòng)物,還被人發(fā)現(xiàn)“他僅僅為了好玩,便把松林里松鼠的尾巴割下來(lái)”[4]。性格扭曲但長(zhǎng)相帥氣的馬文卻毫無(wú)理由地愛(ài)上了像男人一樣、長(zhǎng)著斗雞眼的愛(ài)密利亞,與其短暫地維持了為期十天的婚姻,最后又憤怒地離開(kāi)。荒誕而不可理喻的人物形象更加印證了馬文異常的心理和精神狀態(tài),這種獨(dú)立于主流之外的人物常常被認(rèn)為“有道德或心理缺陷”[12]。
在與愛(ài)密利亞的關(guān)系中,作為整本書(shū)中最具有男子氣概、本應(yīng)該是一個(gè)“父親的形象”[13]的馬文受到了男性權(quán)威的挑戰(zhàn),下定決心要報(bào)復(fù)愛(ài)密利亞。“被拋棄的丈夫、被羞辱和閹割的馬文·馬西”[14]離開(kāi)小鎮(zhèn)后原形畢露,搶過(guò)加油站、糟蹋了最嬌美的姑娘,“他身上有一種無(wú)法形容的卑劣的品質(zhì),這就像一股臭味一樣牢牢地依附著他”[4]。馬文一系列違背社會(huì)規(guī)約的犯罪行為最終也受到了相應(yīng)的懲罰,從大牢里出獄回到小鎮(zhèn)后,他逐漸滲透到愛(ài)密利亞的生活中,最終伙同李蒙打敗了愛(ài)密利亞,卷走了她的財(cái)產(chǎn),對(duì)那個(gè)充滿平靜幸福的咖啡館和制造財(cái)富的釀酒廠進(jìn)行了徹頭徹尾的破壞,最終逃之夭夭、銷(xiāo)聲匿跡。《奇怪的身體:麥卡勒斯小說(shuō)中的性別與身份》中,薩拉指出,種種跡象表明馬文就像是“一個(gè)純粹的‘惡作劇者’”[14],心理畸形的他通過(guò)戲耍李蒙和愛(ài)密利亞而得到樂(lè)趣和快感,進(jìn)一步證實(shí)馬文在道德層面的異化。
四、情感表達(dá)的異化:三個(gè)殘疾人物之間的病態(tài)聯(lián)系
從麥卡勒斯的生活經(jīng)歷來(lái)看,她對(duì)美國(guó)南方存在一種復(fù)雜的情感,既想逃離、突破南方的局限,又因病痛不得已回到了家鄉(xiāng)佐治亞州,在她的作品中也可以發(fā)現(xiàn)她時(shí)而逃離南方時(shí)而又回歸南方的“一種矛盾情結(jié)”[3]。纏綿病榻的麥卡勒斯將這些復(fù)雜的情愫融入其筆下各式各類(lèi)的殘疾人物中,因此“她的許多角色都在不同的層面上探索精神和肉體之間的界限,從性格和外表的關(guān)系(包括種族的影響)到身體和情感紐帶之間的關(guān)系”[15]。
《傷心咖啡館之歌》中,作者的創(chuàng)作主題仍然是“孤獨(dú)與精神隔絕”,麥卡勒斯通過(guò)對(duì)斗雞眼愛(ài)密利亞、駝背羅鍋李蒙和心理畸形的馬文之間復(fù)雜、多重的情感關(guān)系的描寫(xiě),進(jìn)一步刻畫(huà)出她對(duì)美國(guó)南方的矛盾情愫和對(duì)現(xiàn)代化的不安焦慮。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聲稱(chēng)道德畸形的人“缺乏自然的情感”[16],小說(shuō)中的李蒙體現(xiàn)了培根的觀點(diǎn)。對(duì)愛(ài)密利亞的示好和愛(ài)意,李蒙覺(jué)得理所當(dāng)然;對(duì)馬文的粗魯和無(wú)禮,李蒙又覺(jué)得這是一種獨(dú)特的魅力。身患?xì)埣驳睦蠲杀砀缫怀霈F(xiàn)就因?yàn)槠滠浫酢?ài)哭的性子被小鎮(zhèn)上的工人稱(chēng)為是“真正的莫里斯·范恩斯坦”[4],而莫里斯·范恩斯坦是小鎮(zhèn)上一個(gè)愛(ài)哭的猶太人,所以李蒙被認(rèn)為是“缺少男子氣概,哭哭啼啼”的人[4]。 Kittay在《殘疾研究關(guān)鍵詞》中對(duì)殘疾領(lǐng)域中的“依賴”(Dependency)進(jìn)行詮釋?zhuān)岢鰵埣彩钱a(chǎn)生“依賴”的原因之一,而“情感依賴表現(xiàn)出軟弱”[12]。
小說(shuō)中的殘疾人物李蒙一開(kāi)始因?yàn)槠渫鈦?lái)者的身份和殘疾的身體而依賴愛(ài)密利亞小姐,后來(lái)又轉(zhuǎn)而依賴對(duì)他更有吸引力的馬文,這都體現(xiàn)出駝背羅鍋李蒙自身的軟弱性。與缺少女性特征的愛(ài)密利亞類(lèi)似,李蒙表哥恰好缺少了男性氣概,而一個(gè)極具男性氣質(zhì)的馬文毫無(wú)意外地吸引了李蒙的注意力,從一定意義上來(lái)說(shuō),李蒙對(duì)馬文產(chǎn)生了一種病態(tài)的崇拜心理。
然而,馬文對(duì)待李蒙毫無(wú)尊重可言,他多次稱(chēng)呼李蒙為“斷脊梁的”[4],也會(huì)時(shí)不時(shí)地對(duì)李蒙扇一巴掌、踢一腳,李蒙變成了馬文的小跟班,卻仍甘之如飴。從麥卡勒斯對(duì)李蒙這一殘疾人物的刻畫(huà)表明,殘疾人士在當(dāng)時(shí)“優(yōu)生學(xué)”的大背景下受到了“污名化”影響,在社會(huì)中依舊沒(méi)有任何話語(yǔ)權(quán)。作者通過(guò)對(duì)身體殘疾且不受尊重的李蒙表哥的描寫(xiě),使讀者更深刻地體會(huì)出“現(xiàn)代性對(duì)美國(guó)南方傳統(tǒng)生活方式造成的巨大沖擊”[17]。
雖然麥卡勒斯在小說(shuō)中更多地關(guān)注那些在身體上有明顯“異常”的人物,但是不可否認(rèn)的是,正是外表英俊但心理畸形的前夫馬文“給愛(ài)密利亞和李蒙之間建立的微妙平衡帶來(lái)了邪惡和破壞”[15]。
從精神分析學(xué)的角度來(lái)看,多琳將“馬文·馬西對(duì)愛(ài)密利亞小姐的愛(ài)解讀為一種在主體性建構(gòu)中被壓抑的欲望的變相出現(xiàn)”[13]。“主體性建構(gòu)”與“被壓抑的欲望”近乎完美地解釋了馬文對(duì)愛(ài)密利亞的病態(tài)情感。一方面,愛(ài)密利亞不同于往日“南方淑女”的形象,她富有、獨(dú)立,在小鎮(zhèn)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她的男性化力量勇敢地反抗了父權(quán)制,本應(yīng)該處于他者地位的愛(ài)密利亞甚至逐漸變成了小鎮(zhèn)中的主體。對(duì)馬文這樣的典型南方男性來(lái)說(shuō),排擠或征服這樣的女性成了他們重構(gòu)自身主體性的方式之一。
另一方面,在新婚之夜,“一個(gè)新郎無(wú)法把自己心愛(ài)的新娘帶上床,這件事又讓全鎮(zhèn)都知道了,其處境之尷尬、苦惱可想而知”[4],愛(ài)密利亞從婚床上走出來(lái),一如既往的強(qiáng)大;而馬文既無(wú)法滿足自己的欲望,又變得很無(wú)助[13]。在短短十天的婚姻里,馬文仍舊無(wú)法改變愛(ài)密利亞、無(wú)法滿足自己“被壓抑的欲望”,最后他因愛(ài)生恨,又在李蒙的“幫助”下打敗了愛(ài)密利亞,奪回了曾經(jīng)喪失的男性地位。
五、結(jié)語(yǔ)
二十世紀(jì)上半葉的美國(guó)南方社會(huì)在政治、經(jīng)濟(jì)等方面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社會(huì)轉(zhuǎn)型帶來(lái)變化的同時(shí)對(duì)以麥卡勒斯為代表的南方人來(lái)說(shuō)也形成了一種沖擊。
本就對(duì)美國(guó)南方懷有矛盾情結(jié)的麥卡勒斯在這樣的沖擊下產(chǎn)生了深深的不安感與焦慮感。從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殘疾人物的刻畫(huà)和細(xì)膩的寫(xiě)作手法考察的是“內(nèi)在和外在生活之間的關(guān)系,個(gè)人心理和身體之間的關(guān)系”[15]。
小說(shuō)中怪誕的情結(jié)和殘疾人物的刻畫(huà)都傳達(dá)了一種現(xiàn)代性焦慮,即社會(huì)生活中的多重異化和“各種各樣的緊張關(guān)系”[5],例如女性氣質(zhì)與男性氣質(zhì)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
殘障研究作為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以來(lái)新興的文學(xué)前沿研究,其研究意義更多的是從殘障作家或殘障角色的視角觀察整個(gè)社會(huì),通過(guò)現(xiàn)象看社會(huì)本質(zhì)。
《傷心咖啡館之歌》中,不論是雙性同體的愛(ài)密利亞、身體殘疾的李蒙還是心理畸形的馬文,都是麥卡勒斯對(duì)轉(zhuǎn)型期美國(guó)南方社會(huì)的真實(shí)描摹,作品中殘疾人物的異化實(shí)際上就是整個(gè)社會(huì)異化的縮影。小鎮(zhèn)的破敗、生活的動(dòng)蕩以及人物的異化都呼應(yīng)了小說(shuō)標(biāo)題中的“傷心”。
參考文獻(xiàn)
[1] 楊國(guó)靜.西方文論關(guān)鍵詞 殘障研究[J].外國(guó)文學(xué),2021(2).
[2] McCullers C.The Mortgaged Heart [M].Boston:New York,2005.
[3] 田穎.南方“旅居者”:卡森·麥卡勒斯小說(shuō)研究[M].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22.
[4] 麥卡勒斯.傷心咖啡館之歌[M].李文俊,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
[5] Garland-Thomson R.Extraordinary Bodies:Figuring Physical Disability in America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7.
[6] 鄭潔儒.情感、性別和倫理——評(píng)戈?duì)柕摹?9世紀(jì)小說(shuō)中的殘障敘事》[J].外國(guó)文學(xué),2021(2).
[7] 林斌.《傷心咖啡館之歌》的“二元性別觀”透視[J].外國(guó)文學(xué)評(píng)論,2003(4).
[8] 張申華.《傷心咖啡館之歌》中的怪胎秀與現(xiàn)代性反思[J].國(guó)外文學(xué),2022(4).
[9] Mitchell D T,Snyder S L.Narrative Prosthesis:Disability and the Dependencies of Discourse [M].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5.
[10] 王晶.論理查三世畸形身體中的動(dòng)物他性和國(guó)體隱喻[J].外國(guó)文學(xué)研究,202244(1).
[11] Reiss B,Serlin D.Keywords for Disability Studies [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5.
[12] Kittay E F.Dependency[M]//Keywords for Disability Studie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5.
[13] Fowler D.Carson McCullers’s Primal Scenes: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M]//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Carson McCullers.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09.
[14] Gleeson-White S.Strange Bodies:Gender and Identity in the Novels of Carson McCullers [M].Tuscaloos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03.
[15] Roney L.Beyond the Pale:Chronic Illness,Disability,and Difference in the Fiction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Carson McCullers,and Flannery O’Connor [D].State College: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2001.
[16] Deutsch H.“Deformity” [A].Keywords for Disability Studies [C].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5.
[17] 林斌.“精神隔絕”的多維空間:麥卡勒斯短篇小說(shuō)的邊緣視角探析[J].外國(guó)文學(xué),2018(3).
(責(zé)任編輯 "陸曉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