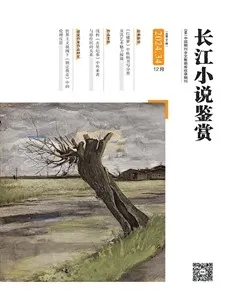成長小說視域下《黑色棉花田》中主人公的認知圖式建構
[摘要]《黑色棉花田》是美國經典成長小說,小說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講述了凱西一家如何在一個充滿種族歧視與不公的社會中艱難求生,努力維護他們的正直、尊嚴與獨立精神的故事。在當時的美國南方,即使美國政府廢除了奴隸制度,但種族觀念根深蒂固,黑人無法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改變生活,來自白人群體的壓迫和蔑視無處不在,有的人妥協后卑微求生,有的人則通過自己的努力反抗時局的不公。主人公凱西在經歷一系列生活的巨變后,逐漸形成自己的自我意識,完成了對自我身份認知的圖式建構,勇敢地捍衛自己的尊嚴和生活。
[關鍵字]他者 "成長小說 "認知圖式 "種族矛盾 "身份困境
[中圖分類號] I106.4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34-0077-04
米爾德里德·泰勒是非裔美國作家、美國兒童文學界代表人物,1943年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遜市,成長于俄亥俄州的托萊多市。她從小就喜歡聽祖父講述他在密西西比州的生活經歷。出于對家族的熱愛與自豪,泰勒開始書寫美國南方黑人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所經歷的艱苦歲月,想要補上教科書中缺失的黑人故事。于是泰勒創作了洛根家族——一個勤勞、團結、有愛的家族,同時將自己家族的教育理念融入其中。幾十年來,洛根家族的故事影響了全球許多家庭,人們從中看到了愛、勇氣與尊嚴,也領悟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愛的教育。
《黑色棉花田》主要講述了美國南方土地上黑人的群像生活,其中凱西·洛根一家都是黑人,自豪地住在密西西比州,在這片土地上,他們的父輩通過努力擁有了自己的土地,本該生活安定的他們卻經歷了各種形式的種族歧視,為了活下去還不得不為自己的土地而戰。凱西雖然生活在奴隸制被廢除后的美國南方,但社會對黑人的不公與壓迫依然存在,在親身經歷了各種磨難后,她依然選擇和家人朋友站在一起,堅守自己的土地,最終在一系列的挫折與磨難中完成自我認知的蛻變。
一、認知理論圖式
圖式是認知科學的一個基本概念,指一種經過抽象或概括了的背景知識或認知架構,即“人腦中的知識單位”[1]。現有的理論均強調人的認知是主客觀相互作用的結果,是主體在與客體相互作用過程中主動建構出來的。在布迪厄看來,人對社會的感知從來都不是簡單的機械反映,而是包含了“建構性原則”的認知活動。圖式就是為人類提供“建構性原則”的認知架構[2]。研究表明,圖式具有習得(因人而異)、無意識、惰性、系統性、整體性等特性,它們并非天生,而是人的主觀能動性在與外部現實互動過程中,經過抽象、固化,逐步衍生而形成。由于它們基本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自動發生作用的,人們幾乎感受不到它們的存在,難以用理性去約束它們[3],但隨著外部環境的巨變,可能會對圖式產生影響。圖式的系統性、整體性體現在它們形成之后,可起到一種集約化的信息處理器或認知裝置的作用。遇到新經驗,只需很小的信息輸入,就能整體激活過往經驗,幫助人們闡釋、推理、展望,并規劃行動[4]。
圖式種類很多,與文學現象息息相關的是一種蘊含著人類需求和社會經濟因素的特殊圖式——認知情感圖式。Beck等認為,基礎的認知情感圖式由特定的人類需求、相應社會情境的認知片段、相應的基本價值信念和本能的防御策略等構成[5]。
本文的主人公凱西是當時社會背景下被視作他者群體的孩子,是弱勢群體中的弱勢者,但她的認知圖式還處在未完全成形的階段,在主觀能動性和外界環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加以時間的推進,圖式會被確立,除非有極其巨大的變故,她的認知圖式一般不會有很大的改變。在被奴隸制度深深影響的美國南部地區,黑人曾經是被販賣的奴隸,是被殖民的群體,被販賣意味著他們曾被當作物品,物品被視作主體的附庸,因而黑人群體一直將自己視作他者。他們在長期的奴役下不具備一個主體應有的完整認知,黑人孩童們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一旦缺少正確的教育和引導,他們依舊會認為自己是白人群體的附屬品、不折不扣的他者。凱西的處境與大多數黑人不同,民權運動后相對寬松的話語環境和家人、朋友的愛,使她在童年時期便具有較強的主體意識,因而在受到一系列的挫折后雖然產生過動搖與困惑,最終仍然不斷完善自我身份的認知圖式,成功蛻變。
二、身份認知圖式建構之旅
布迪厄認為,認知圖式的建構過程不是人生來就有的,而是在成長過程中,在與外部現實的互動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確立的。人成年以后會發現,童年時期一些很小的事都會給自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童年經歷對一個人的認知圖式建構來說舉足輕重。基礎的認知情感圖式由特定的人類需求、相應社會情境的認知片段、相應的基本價值信念和本能的防御策略等構成。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社會以及家庭以外的人接觸后,主體的觀念會受到沖擊,一開始,人會形成一種自我防御措施,面對不公,人會試圖通過反抗來維護自己的權益直到后來認清現實,明白了自己是誰;到最后勇敢冷靜地繼續生活。
1.生根——面對強權,心有畏懼
凱西是故事的主角以及主要敘述者,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對所遭受的所有不公待遇是不滿的,這源于家庭給他們的勇氣和對自己權益的維護意識,他們沒有麻木地生活,在看到“新書”時會提出不滿,并直面老師的懲罰:“我說,克洛克小姐,能不能給我換一本課本。”[6]凱西一直在經歷這些不公,她能看到身邊小伙伴的反應,是受害者也是觀察者,身處其中,凱西會思考自己身處這種不公環境的原因。但是彼時的凱西還不懂,她會畏懼老師,這是一個孩子的本能。但在老師懲罰小家伙的時候,凱西會和他站在一起,直面懲罰。他們正視不公,并且敢于在大家都沉默不語的時候大膽提出來:“看,克洛克小姐,看看上面寫的吧,他們把沒人要的書給了我們。”[6]對孩子來說,老師就是權威的象征,凱西畏懼克洛克小姐的懲罰,甚至擔心克洛克小姐會向媽媽告狀,因為此時的凱西也不能確定自己做得對不對,只是遵從自己內心最基礎的判斷,說出實情,表達不滿,這種反抗很符合孩子的行為模式,雖然沒有足夠的力量和勇氣,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斷。母親的認可使凱西的心中對公正的評估標準被確立,能夠意識到自己被欺辱后表達不滿是合理的,爭取公平與認可的意識在心中生根發芽。所以后來和一幫孩子謀劃了報復事件,這只是孩子的戲弄,但報復成功給了他們巨大的喜悅:“實際上我們根本無法抑制住內心的成就感。只要彼此對視一眼,我們就會笑得趴在桌上,直不起腰來。”[6]但這種喜悅還是被內心的恐懼吹散,因為從小的教育以及孩子本身對事情判斷的不成熟,導致他們不知道事情會怎么發展,“可我無法控制自己,那恐怖的車燈一直浮現在腦海里。我渾身發著抖,一直等到天亮才迷迷糊糊地睡著了”[6]。此時的凱西雖然明白了自己的遭遇是不公正的,明白了自己也是一個具有主體意識的人,但現實環境的殘酷以及長久以來的弱勢地位依舊是戴在她身上的枷鎖,她會在反抗后恐懼懲罰,擔心自己和家人會為自己的反抗付出難以估量的代價,此刻的凱西內心已經建立了基本的是非評判準則以及基礎的防御機制。
2.萌芽——認清現實,自我反抗
報復事件后,平靜的生活持續了一段時間,但之后發生在同一天的兩次屈辱事件給了凱西巨大的挫敗感,凱西和奶奶一起進城的那天,先是遭遇了白人商店老板的無視和區別對待:“你這個小黑鬼,站一邊去,再等會兒吧。”“把她給我帶出去。”“讓你媽媽好好教教她,讓她知道自己是個什么東西,否則就永遠別出現在我的店里。”[6]自我意識剛覺醒的凱西并沒有想到自己會被如此區別對待,一開始她安慰自己可能是因為自己孩子的身份而受到輕慢,后來同為孩子的白人受到了優待,自己的抗議被所有人忽視,甚至被稱為“小黑鬼”,黑人群體也沒有人幫助她,好像是她的不守規矩破壞了和諧一樣,本就形成了防御機制的凱西無法做到視而不見、忍氣吞聲。憤憤不平的凱西成了人群中的異類,這件事情還沒有平息,在大街上被羞辱和奶奶的妥協退讓讓凱西徹底崩潰,凱西不小心撞到白人女孩莉蓮后被要求站到馬路中間道歉,同時被人們侮辱:“你都不看路,到馬路上去好了。像你這樣的黑鬼,怎么能弄臟我們高貴的白人。”[6]這種當眾羞辱對一個成年人來說都是巨大的打擊,更何況是個十歲的孩子。此時凱西的信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她開始質疑這個社會,質疑自己原本的認知。凱西的母親沒有放任事態的惡化,她鼓勵凱西說出了一天的屈辱遭遇,而不是讓孩子忍受屈辱,雖然不能幫孩子報仇,但至少讓凱西有機會發泄委屈。與此同時,母親向孩子解釋了奶奶的委曲求全:“你和奶奶在一起,她只是做了不得不做的事情。相信我,大小姐,她跟你一樣,心里有一萬個不愿意。”[6]她告訴凱西,白人為什么會這樣,她知道凱西遲早要自己獨自面對這個世界的殘酷和黑暗,從小就教育凱西,可以讓她提前認清現實,這樣可以更好地保護自己。“凱西,白人是人,黑人也是,世界上的每個人,無論何種膚色,都是平等的。”[6]雖然無法改變現實的不公與黑暗,但母親可以讓凱西心存希望,不自輕自賤,她告訴孩子人人平等,即使無法改變現實,也不能忘記自己是誰。
基礎的防御機制不足以保護她,甚至是令自己驕傲的爸爸和大伯也無法改變現實,遇見不公平的事情不能不顧一切地反抗,否則會付出不可預估的代價,但母親同時讓她明白,不公的現狀不是黑人的過錯,黑人和白人一樣,人人生而平等,此刻原本的建構的防御機制和是非評判準則進化得更加理智和清醒,凱西認清了現實,但卻不會向現實妥協。她明白要在反抗的同時學會自我保護,此時的凱西已經逐漸形成自己的人格,對自我身份以及自我處境有了更全面的認知。
3.破土——直面風浪,勇敢前行
市集屈辱事件之后,凱西開始用自己的手段和智慧報復了莉蓮的侮辱,并且沒有拖累家人,讓欺負她的白人自食其果。但成人的世界相較于孩子兇險多了,凱西家的土地一直被白人覬覦,自食其力的洛根家族是當地的異類,成為格蘭杰家族的眼中釘肉中刺。
凱西的朋友提杰成為背叛者,向政府舉報凱西母親的行為,導致凱西的母親失去工作和收入來源,母親在面對政府官員的監視時,絲毫不退讓,堅守一個老師的本分,即使面對被辭退的威脅也沒有絲毫的退讓,她據理力爭:“我做不到……因為上面寫的都不真實。”[6]這一刻,母親已經知道不會有人站在自己的一邊,但依然沒有低頭。父親和大伯為了保護其他身為佃農的黑人同胞,決定冒險和格蘭杰家族對抗,為同胞進城購買物資,以擺脫格蘭杰家族的控制,即使同胞們都因為畏懼權勢而退出,父親和大伯依然不放棄,最終慘遭白人暗算,身受重傷。
凱西是這一切的見證者,父親和大伯是凱西心中崇拜的對象,父親勇敢勤勞,大伯離開家鄉,在外面的世界闖出了自己的事業,她看著崇拜的父親身受重傷,奄奄一息,大伯變賣家產,保全土地;看到家里的土地即將被格蘭杰家族強占,看見自己曾經的朋友提杰被白人毆打。雷聲滾滾的夜晚,火光蔓延,父親和大伯沖出去保衛土地和同胞。惡劣的自然環境和事態的突然變化,把最殘酷的現實呈現在這個十歲的小姑娘面前,父親和哥哥生死未卜,這讓凱西在一夜間長大。凱西明白那一夜帶走了很多東西,也留下了很多東西,她看清楚了白人對黑人同胞趕盡殺絕的惡,看到每一個努力生活的黑人同胞的苦,明白了家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和信念。凱西的一家人拼盡全力也很難守護住祖輩努力換來的土地,但凱西沒有被嚇退,她在疾風驟雨中看到了人性的丑惡,也看到人勇敢與命運抗爭的光輝,“孩子,我們沒法選擇自己的膚色,沒法選擇我們的出身。我們唯有選擇努力生活。我向上帝祈禱,希望你能做出最好的選擇”[6]。凱西無法選擇出生,但可以選擇未來,家人的話和那個雷聲滾滾的夜晚讓凱西真正明白了身份究竟為何物,身份是不被他人定義的,命運是靠自己書寫的。凱西的平靜是成長后的堅定,她明白了自己是誰,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三、結語
認知圖式建構的過程,是主體和外界磨合和相互作用的結果,人要和現實生存環境相適應,從而將圖式進化到最合理成熟的模式和狀態,在當時的美國南方,原有的話語權力因民權運動而有所松動,但黑人仍處于社會的底層,被白人群體視為他者,主體面對身份危機,身份的統一性和連續性遭到破壞。面對當時白人權力的壓迫,凱西沒有一味屈服,為了滿足主體對歸屬感和自身安全感的需求,構建認知圖式極為迫切。洛根一家敢于向白人購買土地、尋求公正公平的行為極大地挑戰了“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家人以及朋友等積極的社會紐帶的支持為凱西提供了反抗的勇氣,身后祖輩的土地是主體完善自我認知的理想空間。脆弱稚嫩的主體認知在理想空間和重要他人所提供的積極氛圍下不斷對抗社會話語的強壓與重創,主體在不斷的自我修復與和解中完成蛻變與成長,全新的身份認知圖式得以建構。
參考文獻
[1] 邵志芳,高旭辰.社會認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 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Inequality. London:Routledge,2018.
[3] 戚濤,朱妤雙.情感、認知與身份:懷舊的圖式化重構[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3).
[4] Freeman A.Cognitive therapy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General treatment considerations[M]//Cognitive psychotherapy:Theory and practice. Berlin,Heidelberg: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1988.
[5] D’Andrade R.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anthropolog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6] 泰勒.黑色棉花田[M].陳儀萱,譯.海口:南方出版社,2016.
(特約編輯 "劉夢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