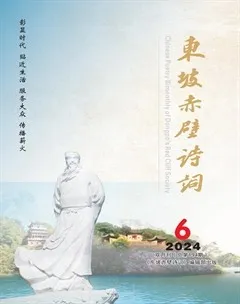詩詞創(chuàng)作中環(huán)境思維
環(huán)境思維,是我在創(chuàng)作西藏百首詩詞過程中的感悟。我第一次去西藏是2003年,回來后,有了想寫西藏百首詩詞的想法。可是,寫到二十幾首后,卻再也寫不出來了。想一想,是對西藏的感性認識不夠,走過的地方太少,缺少對西藏環(huán)境直接觀感的印象。這時如果硬寫,出來的詩,就不會符合西藏的環(huán)境,會讓人覺得不像是在寫西藏。原來,人的思維在不同的環(huán)境影響下,所產(chǎn)生的作品風格也會有所不同。正所謂“鐵馬秋風塞北,杏花春雨江南”。想到這些,我又第二次、第三次去西藏,然后,又讀了六七十本有關(guān)西藏的書,才寫成了西藏百首詩詞(2014年《詩刊》的《子曰》增刊第四期一次發(fā)表97首和一篇自序)這是我對環(huán)境思維的初步認識。
其實,古人說的“行萬里路”,就是環(huán)境思維的意思。古人把它同“讀萬卷書”等同起來,也說明它的重要性。
環(huán)境思維的獲得主要有兩條途徑,即直接獲得和間接獲得。
直接獲得的環(huán)境思維。即詩人到所想表達的環(huán)境中,抑或讓以往的生活經(jīng)歷再現(xiàn),并去體味、去感受環(huán)境氛圍而獲得的靈感。也許大家都有這樣的體會,有時想寫一首郊游題材的詩,在家蹩了幾天也寫不出來,可一旦走出家門,來到郊外鄉(xiāng)間或深山野林,詩便自然地產(chǎn)生了。2003年7月,我去九寨溝。一踏入九寨溝人間天堂般的境地,忽有恍如隔世、第一次來到地球的感覺:“水奏琴音下斷崖,野花倒掛澗邊開。我是地球村外客,山床一覺夢生苔。”(《游九寨溝》)因為全身心地進入了這里的環(huán)境,這首詩就像山谷中流出來的泉水一樣自然。這說明寫詩需要身臨其境,有了這個“境”,才會有“環(huán)境思維”。寫詩20多年,我有一個感覺,就是每當寫軍旅詩的時候,便會自然而然地出現(xiàn)境界。因為,軍旅的環(huán)境是我所熟悉的。如:“邊境穿行欲斷腸,當年歷史已微茫。界碑立處雜荒草,一朵花開兩國香。”(《故鄉(xiāng)邊境行之一》)
間接獲得的環(huán)境思維。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讀書。我最近寫西藏百首詩詞時就發(fā)現(xiàn),原來積攢下來的大約五百條零散詩句,一句也派不上用場,后來終于明白,原來的零散詩句,都是在西藏以外的環(huán)境下產(chǎn)生的,自然不符合反映西藏那個特殊的環(huán)境。于是,我決定重新到西藏的自然環(huán)境、生活環(huán)境和語言環(huán)境中去尋找西藏的詩。就這樣,我不但第二次去西藏感受那里的環(huán)境,而且用了八個月的業(yè)余時間,閱讀了大約1000萬字的關(guān)于西藏的紀實散文。這樣做確實產(chǎn)生了很好的效果,一首又一首詠西藏的詩,在特定的“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如:“遠處雪山攤碎光,高原六月野茫茫。一方花色頭巾里,三五牦牛啃夕陽。”(《高原牧場》)“啄食牧歌藉夢孤,長空展翅向平蕪。一鉤寒暮夕陽血,撕爛荒原殘雪圖。”(《雪域雄鷹》)可以說,這些詩只能在西藏的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連續(xù)數(shù)年耕讀,我在西藏廣袤蒼茫的氛圍里徜徉,像“冬蟲夏草”一樣,在經(jīng)幡下禪定。這充分證明,經(jīng)常地、反復(fù)地閱讀某一類書籍,也是產(chǎn)生環(huán)境思維的重要途徑。
為此,我們要充分認識環(huán)境對人思維的影響,并努力培養(yǎng)自己的環(huán)境思維能力,回到自己熟悉的環(huán)境中去,開拓自己向往的環(huán)境,打造獨特環(huán)境下的獨特詩詞。不難想象,環(huán)境還是一個詩人形成個人風格,一個地方形成詩歌流派的重要因素。同時,環(huán)境更有另一個深刻的寓意,那就是說,我們不能模唐仿宋,因為,我們的社會環(huán)境和自然環(huán)境,早已與和唐宋時期大相徑庭了。
(作者劉慶霖,系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中華詩詞》雜志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