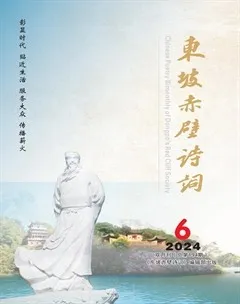謎比
謎比,是詩人在詩作中,把題中旨趣隱藏在若干與題旨挨近或相似的意象或意境背后,讓讀者像猜謎語一般,轉彎抹角去猜測它、發現它。用這種謎比手法寫成的詩,也就成了謎語詩。然而,詩與謎既有密切聯系,又有實質性的區別。就其密切聯系而言,二者都要求借助某些相似相關的物象,含蓄地表達某種旨趣;而就其實質性的區別而言,誠如詩論家丁國成先生所說的:“詩謎不同于詩歌,很難猜中——這只是它的外在形式。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內容:詩謎更講究科學,隨物賦形,可以貌合神離;詩歌則注重感情,詠物抒情,要求形神統一。因此,它們的社會效果也大不相同:詩謎作用于讀者的理智,猜謎可以鍛煉人的頭腦;詩歌作用于讀者的感情,讀詩能夠凈化人的心靈。”[1]當然,能做到首先是詩、同時也是謎的詩謎詩,也不是沒有,只不過是鳳毛麟角而已。
就詩謎詩的謎底分類,可分為物謎詩與情事謎詩,而以物謎詩居多。
(一)物謎詩。以形神兼備、托物寄情之作為佳勝。比如有這么一首詩作:“春風一夜到衡陽(衡陽有回雁峰,乃鴻雁越冬之所),楚水燕山萬里長。莫道春來又歸去,江南雖好是他鄉。”掩卷冥思,便不難看出:詩題應是《歸雁》。詩中不僅道出了作為候鳥的鴻雁的基本特征,而且賦予詩人以濃郁的歸思鄉愁;記得還有一首物謎詞,是我年輕時從一本散文集中讀到的,至今仍記憶猶新。詞云:“想當年,綠蔭婆娑。自歸郎手,青少黃多。受盡幾多折磨,歷盡幾多風波。莫提起,提起珠淚灑江河。”——打一水上用的工具。乍讀之,仿佛是一首代言體的抒情小詞。詞中體物寫人,形神兼備,好像在為舊社會那苦難深重的勞動婦女傾訴衷腸!若仔細體察詞中的比附,順藤摸瓜,從“當年”的“綠蔭婆娑”到“歸郎手”后“青少黃多”看,定是一件經常用的竹木器具;再從“受盡折磨”“歷盡風波”看,定是經常同水打交道,而且提不得,一“提起”就“珠淚灑江河”。至此,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指撐船用的竹篙子。體物賦形,神形畢肖。
(二)情事謎詩。謎比以寓情詠事,或借景寄興,措意曲深,頗耐尋繹。古代日本學者遍照金剛,曾以王昌齡詩為例論及此法。他說:“謎比勢者,言今詞人不悟有作者意,依古例有別。昌齡《送李邕之秦》詩云:‘別怨秦楚深,江中秋云起。’——言別怨與秦楚之深遠也。別怨起自楚地,既別之后,恐長不見,或偶然而會,以此不定,如云起上騰于青冥,從風飄蕩,不復可歸其處,或偶然可歸爾。‘天長夢無隔,月映在寒水。——雖天長,其夢不隔,夜中夢見,疑由相會。有如別,忽覺,乃各一方,互不相見,如月影在水,至曙,水月亦了不見矣。”[2]這段話,對于王昌齡運用謎比法,表達對摯友的深情厚誼,真可謂鞭辟入里。詩中托秋云以寄別恨,借水月以托夢境,以實寫虛,曲徑通幽,謎比妙趣,巧得天然。漢魏時期也有一首運用謎比法的民歌,即《古絕句》之一:“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這四句詩是兩問兩答,即一、三句是問,二、四句是答。第一句是問:夫在何處?第二句是答:言已外出。第三句再問:何日還歸?第四句再答:言在月半。首句中的“藁”即“稻草”;“砧”即砧板,是斫物時墊在刀下的木板。古代罪人被斬時,以藁為席,伏在砧上,行刑者用鐵(大斧)去砍他,所以藁、砧、鐵三者總是緊連在一起的。詩中舉其兩物,則其第三物就會被自然而然地聯想到。故首句以“藁”“砧”隱“鐵”,又因“鐵”與“夫”諧音雙關,便借這一隱語指“夫”。第二句“山上復有山”是“出”字,比較好猜。第三句中的“何當”是何時,“大刀頭”則暗指“環”(刀頭常有環),“環”的諧音是“還”,又拐了一道彎彎。末句以“鏡”喻月,“飛上天”的“破鏡”就是“月半”。全詩四句皆用謎比,借物象來比事象,幾番周折,方悟其意,一旦猜出,頗有興味。但如果脫離古代的生活知識,便茫然無所知了。還有一首妙趣橫生的《圈兒詞》,據說是清朝時候有位婦人想念在外的丈夫,打算捎個信去,可又不會寫字,就在信紙上畫了密密麻麻的圈兒,有大有小,有單有雙,有破有圓。一位秀才揣摩其意,破譯了其中的密碼,寫成這么一首《圈兒詞》:“相思欲寄無從寄,畫個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里。我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整圈兒是團圓,破圈兒是別離;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把一路圈兒圈到底。”[3]詞中提到的各式各樣的圈兒是謎面,這《圈兒詞》揭示的相思情便是謎底。這個謎面,一般人是很難猜中的,一經《圈兒詩》點破,便覺妙趣無窮。
綜上所述,謎比詩中的佳篇,也饒有別趣,可觀可賞,但不宜提倡,因近乎文字游戲,易流于形式主義詩風。
參考文獻
[1]丁國成《古今詩壇·詩謎》。
[2]日本·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地·十七勢》。
[3]清·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
(作者系黃岡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華詩詞學會教育培訓中心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