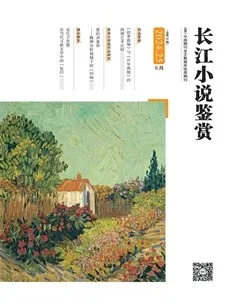兒童視角下的反戰小說《二十四只眼睛》
[摘要]兒童視角,指的是一種“小說借助于兒童的眼光和口吻來講述故事,故事的呈現過程具有鮮明的兒童思維特征,小說的敘述調子、姿態、結構及心理意識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選定的兒童的敘事角度”。本文圍繞兒童視角,對壺井榮的小說《二十四只眼睛》進行剖析,從三個方面入手:小說的創作背景、兒童視角下的戰爭呈現,以及兒童視角如何塑造了作品獨特的文學效果和表達的深層內涵。重點在于考察《二十四只眼睛》中,兒童視角下戰爭對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影響,以此進一步挖掘戰爭在小說中的具體表現,進而深入分析小說蘊含的深層意義——作者對故鄉的深切熱愛,以及通過兒童純真的視角,表達對和平與人性美好的向往。
[關鍵詞]《二十四只眼睛》" "反戰小說" "兒童視角" "壺井榮
[中圖分類號] I06"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25-0027-04
日本著名近現代作家壺井榮的代表作《二十
四只眼睛》在日本文壇備受推崇。該小說以日本瀨戶內海一個偏遠的小漁村為背景,敘述了女教師大石久子及其12名學生從1928年至1946年間的生活變遷與成長歷程。小說通過“戰前”“戰時”“戰后”三個階段,詳盡展現了普通日本民眾經歷的幸福和苦難,刻畫了戰爭給平民帶來的身心創傷,傳遞出反戰與和平的強烈呼聲。
一、《二十四只眼睛》中的“兒童視角”
在《現代小說研究的詩學視域》中,兒童視角被定義為:“小說借助于兒童的眼光和口吻來講述故事,故事的呈現過程具有鮮明的兒童思維特征,小說的敘述調子、姿態、結構及心理意識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選定的兒童的敘事角度。”[1]簡言之,這是一種以兒童的視角,但并不局限于兒童的認知水平,用兒童的眼睛、語氣、思維和感覺來觀察世界、講述故事的一種敘述策略。作家通過兒童視角,生動展現了戰爭如何改變了孩子們的生活與內心世界,揭示了他們在戰爭環境下不同于成年人的思維方式、認知框架和價值觀念。不可忽視的是,這種視角背后蘊藏了作者的真實意圖,通過兒童的視角,將戰爭以另一種新奇、另類的角度進行解讀,為讀者呈現出一種獨特的話語表達方式,從而形成了與眾不同的美學風格。
在整部小說中,兒童視角總是在與大石久子的互動中自然流露,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而顯現,無論是大石久子在瀨戶內海小漁村中教導的12名學生,還是后來她的3個親生子女。在戰爭的陰影下,壺井榮借用與成人視角截然不同的兒童視角,從不同角度展現了戰爭對孩子們在物質以及精神方面的影響,控訴了戰爭的殘酷,同時表達了對和平的渴望。
二、兒童視角下《二十四只眼睛》戰爭的表現
本文將從戰前、戰時與戰后三個時間點,從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剖析小說中戰爭的呈現。
1.物質生活的表現
《二十四只眼睛》是以1928年為起點,大石久子(昵稱“小石老師”)來到瀨戶內海一個偏遠的村莊執教展開的。戰前,這個村莊遠離塵囂,民風淳樸,村民們自給自足。12名學生來自各種家庭,有的經營豆腐店、米店、旅館和鈴鐺修配店,有的以捕魚為業,或是當木匠。每家既從事本行,又種田打魚,他們熱愛勞動,珍惜著這個能維持生計的地方。在這樣一個樸實淳厚的村莊中,孩子們也肩負著不小的責任。例如,當小石老師摔傷腿后,12名孩子們計劃步行到老師家看望,其中琴江內心的矛盾被細致地描繪——她露出不安的復雜神情,既擔心家中事務,又想外出探望老師。壺井榮通過心理刻畫,著重描寫了早苗、松江、琴江和小鶴這類多子家庭中孩子們的責任,如看護家里其他孩子——“然而,這兒的孩子即便玩耍,也不能真正自由地玩耍,他們總得領著弟妹,背著嬰兒”[2]。作者刻畫了勞動至上、每個家庭成員都“各司其職”的情況,描繪出貧窮的村民們自食其力,努力生活的樂觀情景。
隨后小說時間線推至1932年,日本國內政治動蕩加劇,對外侵略行動如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相繼發生。然而,這些重大歷史事件對孩子們來說,僅體現為經濟蕭條對其日常生活的間接影響。兒童視角下,戰爭的殘酷和復雜性被簡化為衣食住行的改變。作者巧借這點,從孩童們生活上的物件入手,描繪了因戰爭局勢而變得不景氣的形勢,由此深入到家家戶戶受此影響變得更加貧困的現狀。例如,加部小鶴家故意給她買能穿三年的大號帆布鞋,因經濟不景氣影響到工作的父親無法給松江買百合花飯盒,以及早苗母親因為沒錢購買水手服便給女兒縫制了紅色下擺裝飾的自制棉夾衣。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也給日本社會帶來了不可預估的傷害,但在孩子們的世界里,無法深層次地理解戰爭所帶來的危害,能令他們直接感受到的便是自己日常生活的變化。作者巧妙地通過這些細節,描繪了戰爭帶來的經濟壓力如何滲透進每一個家庭,讓讀者感受到戰爭對普通民眾的無形壓迫。
至戰后時期,小說中的12名學生已長大成人,此時出現了新的兒童視角,即主人公大石久子的孩子們。在這一代孩子的身上,因戰爭所造成的物質匱乏更為嚴重。在那個食物稀缺的時代,孩子們有時需要去山里撿橡子、吃苦味面包充饑,去當少年航空兵是因為“紅豆甜湯管個飽”,最小的孩子八津甚至因食用青柿子而不幸離世。作者沒有采用正面描寫的手法,而是通過兒童的視角,勾勒出一個資源枯竭、饑餓肆虐的社會圖景。
安德魯·戈登在其著作《現代日本史——從德川時代到21世紀》中指出,1928年至1946年,日本經濟經歷了劇烈波動。1929年一場經濟危機襲來,不僅大城市受到影響,鄉間小鎮也未能幸免。1931年至1934年,盡管日元貶值有助于日本產品開拓國際市場,且實行凱恩斯的經濟政策使日本從經濟危機中復蘇的速度比西方快,但西方國家對日本的貿易壁壘和日本侵華行動加劇了國際關系的緊張。戰爭期間,日本實施了全面的經濟控制,目的是動員“所有物資及人力資源”。1942年后,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的不利局勢,其經濟開始陷入混亂,戰爭陰影下的不安跡象也漸漸浮現,經濟失衡且因為物價與工資管制,日本民眾被迫依賴黑市獲取基本生活用品。
這些現實的一面,壺井榮在《二十四只眼睛》中并沒有直接提及,而是通過兒童的視角,以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變化,反映出戰爭對物質生活造成的破壞,實現了意想不到的文學效果。
2.精神生活的表現
戰爭不僅摧毀了日本的城市,也波及小村莊的物質生活,同時給普通居民造成了難以想象的精神創傷。在小說中,關于戰爭給精神生活帶來的創傷是無法回避的。戰前,小石老師剛來學校,遇到的12名學生是活潑的、天真的、純潔的、真摯的。當小石老師摔倒站不起來時,孩子們擔心得哭了起來。與男老師教的“愛國歌”《千引巖》相比,一年級的香川增之老成地對同行的山石早苗說:“我真不喜歡男老師教的歌,還是愛唱女老師教的歌曲。”潘雨榕提及,女老師教導的歌曲多出自1918年7月1日由鈴木三重吉創刊的兒童雜志《赤鳥》,與男老師教的那種由政府主導的歌曲不同,意在培養孩子們的純潔心靈。作者從孩子們的行動、言語和心理入手,試圖描繪出精神上還未遭受軍國主義侵蝕的天真無邪、純潔美好的兒童形象。然而,對男老師的刻畫意在表達軍國主義思想已初步滲透到學校的教育中。
到了戰時階段,報紙上以“腐蝕純真靈魂的赤色教師”為題報道了稻村老師的事件。小石老師試圖向學生解釋什么是赤色、無產者、資本家以及勞動者,但不出所料,孩子們尚不具備理解這些深奧詞匯的能力。作者在小說中特意安排了竹一和阿正未來想當軍官的爭論場景,一旁是流露出羨慕神色的吉次和磯吉。在這一幕中,筆者認為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有二:一是文中提及的受家中親人當兵以及社會氛圍的熏陶;二是孩子們之間不服氣、不示弱的爭強好勝心理的體現。從兒童視角看,孩子們對于戰爭的具體形態仍處于懵懂狀態,但戰爭的氣氛已經彌漫整個社會。
戰后,出生于戰爭時代的他們,其思想、感情以及價值觀完全被戰爭所影響,因為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便是如此。正如小說中寫道:“不知道和平生活為何物的大吉曾聽說自己出生的當夜因防空演習家中一片漆黑,他是在燈火管制的生活中長大的,聽慣了警報聲,盛夏也拿著棉頭巾去上學的大吉很難理解母親為何如此憎恨戰爭。家家戶戶都有人走向戰場,村莊里幾乎沒有青年人,這在他想來都是理所當然的。學生們受到動員,婦女們外出參加義務勞動,所有的神社里都被掃得一干二凈,大吉相信這便是國民的生活。” [2]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大吉的內心不免為“貪生怕死”的母親感到羞愧,他認為去參戰是件體面且值得驕傲的事。日本在戰時統制體制下,同時也加強了對思想文化的統制,希望通過后者來加強和鞏固前者。從兒童的視角來看,隨著戰爭的發展,兒童教育與軍國主義的聯系日益緊密,這直接導致了一代兒童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造成了一代人無法治愈的精神創傷。
三、小說中運用兒童視角的藝術效果及深層內涵
1.藝術效果
王黎君認為:“這種兒童視角的細節化表述,一方面觸摸到了生活的真實,還原了生活的本來面貌,同時孩子對世界的一知半解和感性的思維方式,又使他們無法真正把握世界的深層意蘊和內涵,只能真實地展現生活的表象。”[3]在運用兒童視角展開敘述的小說中,孩子們用自己特有的思維方式和細膩的眼光,觀察周圍的一切以及大人們的世界,由此產生了一種既富有童趣又獨具特色的藝術效果。
首先,尚未接受系統教育的孩子,他們的生活經驗和認知水平有限,對世間事物的看法與成人截然不同,將孩子們的奇思妙想融入文學,令人耳目一新。小說中就有一段十分典型的描寫:
在這樣激烈的動蕩之中,幼小的孩子們吃著麥片飯茁壯地成長著。他們不知道今后等著自己的是什么,只是為自己的成長感到高興。雖說到了五年級,可仍然買不起運動鞋,孩子們死了心,把這看成人力無法抗拒的不景氣造成的結果,依然滿足于很久以前就穿的草屐,上總校讀書這件新事使他們興奮不已。[2]
在這段描寫中,孩子們并不清楚造成經濟不景氣的深層原因是什么,他們只能察覺到經濟不景氣如何影響到了他們的日常生活,比如家里無力為他們購買運動鞋。這種視角為戰爭帶來的破壞蒙上了一層純真而又略帶諷刺的濾鏡。
其次,作者采用了這種巧妙的多重視角轉換的敘事策略,以“兒童”的方式與人交往、觀察世界,因此在文本中構建了一種兒童與成人之間的“對話”關系,使得小說的敘事視角能在成人和小孩間靈活切換。在兒童視角下,很多深層含義的事物僅停留于表面理解,因為孩子們的閱歷有限。此時,成人視角的轉換便能將深藏在背后的原因進行揭露,豐富了文本想要傳遞的信息。例如,當阿正和竹一爭論將來誰要去參軍時,作者立即將視角轉向小石老師,直接揭示了好戰氛圍下個人所失去的自由。通過這種方式,不僅彌補了孩子們視野上的局限,還深化了主題內涵,“成人視角”與“兒童視角”相輔相成,共同完善了作品的完整性。
2.深層內涵
2.1對故鄉故土的熱愛之情
在《兒童文學入門》(牧書店,1932年9月)的《我的童話是怎樣誕生的》中,壺井榮寫道:“我早期的作品之所以幾乎都是懷舊的,是因為這些作品是年近四十的我對過去的回憶的積累。我認為,所有這些都是我小時候經歷過的事情,也是我的祖先和兄弟姐妹們走過的路。正是這些過去的回憶激發了我的創作靈感。” [4]
作者在此強調了自己早期作品的懷舊性質,但在筆者看來,《二十四只眼睛》同樣包含著作者對自己童年回憶中故土的熱愛。這部小說是以壺井榮的故鄉小豆島為背景而創作的,據說小說中12個孩子的原型是作者家庭中的成員,但在與出版社協商后,最后呈現為分校里的12名學生。筆者認為,這些兒時的回憶深深植根于壺井榮的心靈深處,成為她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常能在她的作品中發現對家鄉風土人情的生動描述,能感受到作者對故鄉永恒不變的深情。比如在臺風來襲時,作家想象在村莊間的海面架設魔法橋梁,平息風浪,充滿了童話色彩,以及對當地居民質樸勤勞的刻畫,作者對這片故土的熱愛顯露無遺。
2.2戰爭受害者的多重鏡像
宮澤健太郎指出,壺井榮擅長描繪生活細節和人物心理,但在《二十四只眼睛》中并未充分展現這一點,他認為這是戰爭造成的后果。關于戰爭受害者身份這一敘述,朱穎指出,小說主要聚焦戰爭中的日本民眾的視角,并未觸及年輕士兵在戰場上的行為及心理變化,這樣的敘事選擇可能意在通過民眾的視角來強化戰爭給人類帶來的廣泛傷害。這樣的書寫策略無疑觸動了讀者對戰爭中無辜受害者的同情,但也可能引發關于戰爭全貌展現不足的討論。
在兒童視角下,作者塑造了戰前還未被軍國主義思想浸染的純真的日本兒童形象,比起男老師教導的“愛國歌”,他們更喜歡女老師教的符合孩子們趣味的兒歌。戰中,盡管孩子們仍保有幾分純真與真摯,他們會為了哪種螃蟹更好吃而爭辯,也會專門捉來給小石老師分享。但不可否認的是,當作者將筆觸轉向男孩們爭相表達想要參軍的愿望時,這一場景與戰前無憂無慮的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深刻凸顯了戰爭對兒童心靈的侵擾與改變。到了戰后,小石老師的兒子,一個出生在戰時、其價值觀完全被軍國主義所影響的兒童形象,成為作者筆下又一個引人深思的角色。通過這一角色,作者不僅揭示了戰爭對日本兒童及其家庭造成的深遠影響,也暗示了戰爭這一全球性災難對所有無辜孩童的普遍傷害。
四、結語
長篇小說《二十四只眼睛》以一位小學老師與12位學生在戰爭中的悲慘命運為線索,講述了人們在戰爭中遭受的苦難。小說主要運用了多視角的轉變,將兒童視角與成人視角相結合,從兒童純潔、淺顯的目光中看世界戰爭的變化發展,同時,也通過成人視角的穿插,揭示了戰爭對成人世界的深刻影響,以及戰爭如何摧毀了無數家庭的幸福與安寧,展現了戰爭對全人類的普遍傷害。
參考文獻
[1] 吳曉東,倪文尖,羅崗.現代小說研究的詩學視域[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1).
[2] 壺井榮.二十四只眼睛[M].譚晶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
[3] 王黎君.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兒童視角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7.
[4] 宮澤健太郎.壺井栄の肖像:児童文學をめぐって[J].白百合女子大學研究紀要,2009.
[5] 戈登.現代日本史——從德川時代到21世紀[M].李朝津,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6] 潘雨榕.反戰小說《二十四只眼睛》的生成[D].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2021.
[7] 朱穎.從《二十四只眼睛》看日本人戰爭記憶重建[D].杭州:浙江大學,2017.
[8] 王珊.勒克萊齊奧的兒童視角小說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2.
[9] 秦偉.日本戰時統制體制研究[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11.
(責任編輯" 余"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