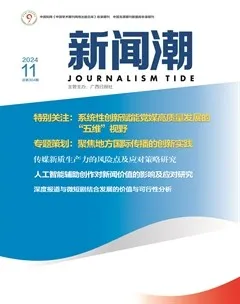從內容編創(chuàng)到共情傳播: 民生視角下政務新媒體融合服務研究
【摘 要】政務新媒體是移動互聯(lián)網時代黨和政府聯(lián)系群眾、服務群眾、凝聚群眾的重要渠道,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手段。但其發(fā)展過程中仍存在政務與媒介場域博弈問題凸顯、內容質量不佳、“流量”紅利下滑、受眾黏性低、編輯職業(yè)認同感偏低等問題。“政務+媒體+民生”融合以服務民生為目的,深耕優(yōu)質內容編創(chuàng)與共情傳播長遠生態(tài)基礎上的新型路徑。政務部門應明晰自身角色定位,以優(yōu)質內容激發(fā)受眾閱讀興趣,化解政務新媒體與群眾實際需求之間的矛盾,增強親近感與認同感,借助全媒體共情傳播與互動機制,引導受眾參與式互動,建構切實可行的服務體系,積極培養(yǎng)“政務+新媒體”運營的復合型人才,助益通民心、達民意、惠民生。
【關鍵詞】政務新媒體;內容編創(chuàng);共情傳播;民生;融合服務
根據《2022聯(lián)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中國電子政務排名在193個聯(lián)合國會員國中從2012年的第七十八位上升到了2022年的第四十三位,成為全球增幅較高的國家之一。而2024年“五一”前后一些政務新媒體驟然關停的現(xiàn)象,既是當前政務新媒體發(fā)展癥結的縮影,映射了政務新媒體發(fā)展進程中“外熱內冷”“角色定位不明”等問題,受眾參與度低、“指尖上的形式主義”、“不能真正辦成事”等也成為阻礙政務新媒體發(fā)展的暗礁。本文從民生視角出發(fā),圍繞當前政務新媒體的發(fā)展困境,探析“政務+媒體+民生”以服務民生為目的,將內容編創(chuàng)與共情傳播相結合,追求價值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新模式。
一、全媒體時代政務新媒體的功能價值與特征趨勢
(一)功能價值:政務信息的傳播者,內容編創(chuàng)的“把關人”
首先,政務部門在運營新媒體過程中,是政務信息的傳播者。“對于大多數(shù)人而言,印刷物、電影、廣播、音樂、電視和互聯(lián)網是我們生活的主要組成部分。”[1]政務新媒體在傳播政務信息、發(fā)揮宣傳功能、延伸便民利民服務、弘揚正能量等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政務新媒體的智能化升級本質上是要把媒介技術、政治和行政三個層面緊扣‘人民’這一中心,把贏得民心民意、匯集民智民力作為智能傳播時代發(fā)展的根本遵循。”[2]政務新媒體依托全媒體傳播矩陣,內容多元化,傳播大眾化,獲取信息快捷、便利。其次,扮演內容選題、質量的“把關人”角色。政府部門借由新媒體實現(xiàn)與受眾的線上互動,通過文章推送、新媒體運行功能服務等提供便民利民服務。根據自身政務特色或者服務功能指定主題品牌類型,如“浙江宣傳”微信公眾號的“出圈”與“爆火”不僅與其優(yōu)質的內容輸出有關,更離不開其文章選題、傳播方式與受眾之間的高契合度,“‘浙江宣傳’善于結合當下熱點、難點、爭議事件,發(fā)表具有針對性的評論,在堅守基本原則立場的情況下,大膽展開批評,這種批評話語是解決社會‘疑難雜癥’的良方”[3]。
(二)特征趨勢:政務閱讀社群化,提高受眾參與度
全媒體時代改變著文本的創(chuàng)作、生產與傳播,全民媒體、全景式呈現(xiàn)等傳媒技術發(fā)展為政務新媒體的出現(xiàn)提供了技術支持。一方面,有助于形成政務新媒體社群,凝聚社群力量,諸如微信、微博等社交網絡媒體更具親和力和主動性,具備聯(lián)系群眾的天然優(yōu)勢。人們在數(shù)字、電子化閱讀過程中可以保持與世界的聯(lián)系,在這里文字也成了一種聯(lián)結人與事物、人與人之間的媒介。另一方面,數(shù)字技術與互聯(lián)網技術的發(fā)展與變革為閱讀提供了新的契機,閱讀不再依靠傳統(tǒng)的紙質媒介,由傳統(tǒng)的平面閱讀向立體化、交互式的方向轉變,諸如網絡閱讀、手機閱讀等新型的數(shù)字閱讀方式,這些數(shù)字閱讀方式在目標讀者、文本推介、交流互動等方面各有其定位與側重,便于分享與交流,增強了互動性與參與性,也延展了交流與言說的空間。
二、政務新媒體的挑戰(zhàn)及困境
(一)政務場域與媒介場域的博弈
一些政務新媒體的結合并沒有“出圈”,反而出現(xiàn)“水土不服”問題,既表征其統(tǒng)籌工作與運營策略的得失,也牽涉政務新媒體發(fā)展過程中政務場域與媒介場域之間的博弈。“政務微信生產實踐宜理解為新聞場域與政務場域兩個文化邏輯之間的融合與沖突,理解為其間各行為主體之間的博弈。”[4]大多數(shù)的政務新媒體都在考慮應該賦予什么樣的人設,要端起來還是接地氣,怎樣做到既有流量又能有姿態(tài)。[5]
上述困境表現(xiàn)出在政務新媒體運營過程中的雙方場域的邏輯沖突:一方面,政務新媒體存在自身的特殊性,并不能完全比附其他新媒體與自媒體,倘若完全憑借媒介“流量”的高低來評估政務工作的成敗與得失,極容易走向另一種極端的形式主義與本末倒置;另一方面,倘若一味強調嚴肅性,又難以吸引關注和流量,由此出現(xiàn)政務新媒體定位模糊、文章內容質量不高、發(fā)布頻次極低等問題。
(二)運營模式單一,缺乏互動性
政務新媒體作為政務部門與受眾之間溝通交流的重要渠道,同時因其具備政府部門公信力、權威性與服務性,應積極發(fā)揮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作用,積極為公眾提供答疑解惑、信息咨詢等服務。而受眾對意義的建構方式與對文本的闡釋方式,都表征著受眾絕不是被動的接受者。“媒介制作者制作出復雜的媒介文本,通常表達出比較明確的媒介內涵,但這種內涵并不是被動地輸入到受眾思想中,而是由受眾來闡釋信息,賦予各個組成部分以不同的含義。”[6]一些政務新媒體存在運營模式單一,甚至名存實亡“僵尸號”等情況,群眾反饋渠道的評論區(qū)、留言區(qū)形同虛設,阻塞了公眾的反饋渠道,導致受眾黏性較低,不僅影響了政府部門的公信力,也將降低后續(xù)政務新媒體建設中受眾的參與度。
(三)編輯職業(yè)認同感低,工作內容定位模糊
媒介融合確實仰賴于新興技術的支持,但其一線的媒體運營者與編輯團隊的文化驅動也尤為重要。“個體與組織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個體的職業(yè)歸屬和認同都屬于組織文化的范疇。”[7]一些政務新媒體編輯人員職業(yè)認同感低,認為“錢少事多”“工作內容雜”等。例如,豆瓣平臺上的一篇《政務新媒體編輯工作日常分享》:“不知道大家對編輯這個工作感興趣嗎?說是編輯,但其實是內容運營+活動執(zhí)行+客戶執(zhí)行等崗位的promax版本(不是所有編輯崗位都這樣哈,可能只有我比較特殊)。”[8]
從上述政務新媒體編輯的一線工作體驗中不難窺探出,新媒體運營編輯工作的困境以及政務新媒體定位與實際運營之間的模糊界定。從編輯執(zhí)行者視角來看,“既要”“又要”難以做到,這些問題阻礙了政務新媒體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三、政務新媒體融合服務路徑及對策
亨利·詹金斯認為:“我們使用的融合概念,包括橫跨多種媒體平臺的內容流動、多種媒體產業(yè)之間的合作以及那些四處尋找各種娛樂體驗的媒體受眾變遷行為等。”[9]意即剝離掉種種媒介的想象之后,“融合”是指內容與媒體以流動的受眾為導向。政務新媒體面對發(fā)展過程中的困境,應從內容賦能、共情傳播、培養(yǎng)“政務+新媒體”運營復合型人才等角度制定對策。
(一)明晰政務新媒體品牌定位,打造“人格化”IP
政務新媒體融合業(yè)務辦理、信息咨詢等功能,應強化與新媒體的融合度、趣味性,凝聚受眾,踐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理念。第一,明晰自身定位,并確立自身政務新媒體的內容風格與職責功能。例如,政務新媒體“國資小新”明確自身平臺定位,形塑了政務新媒體的人格形象和務實形象,奠定了新媒體IP化的智力基礎[10]。第二,內容生產IP化。在受眾心中勾畫自身政務新媒體品牌“畫像”,對一些原本便是新聞傳播類的政務機構,進行“人格化”。第三,因地制宜,發(fā)揚當?shù)靥厣郾就潦鼙姡凉撛谟脩簟!罢憬麄鳌敝猿蔀槿珖彰襟w中的翹楚,離不開其優(yōu)質的內容生產與服務意識,同時融入了浙江的地域文化、風土人情等特色。
(二)以優(yōu)質內容激發(fā)受眾閱讀興趣,建構共情傳播模式
一方面,以優(yōu)質內容激發(fā)受眾閱讀興趣,搭建好政務新媒體內容與群眾實際需求之間的橋梁,增強親近感與認同感。提升服務意識,將信息服務、內容服務嵌合于知識服務與情感共振。例如,分類制定專業(yè)知識服務、政策服務,優(yōu)化閱讀體驗,將“專業(yè)領域知識服務”內容生產鏈接在政務機構上,成為衍生品。比如,“深圳衛(wèi)健委”微信公眾號在醫(yī)學科普“賽道”中,明確目標群體定位,將政務內容與醫(yī)療健康知識傳播融合,收獲了眾多受眾的青睞與支持。另一方面,建構共情傳播模式。“共情形成過程本身就是一個交流、溝通、傳播的過程,離開了交流、溝通、傳播就難以形成共情,而共情的表達更是一種傳播過程。”[11]應以受眾需求為導向,結合自身特色做好政務新媒體定位。地方政務新媒體應以服務當?shù)厝罕姙榧喝危瑒?chuàng)作并推送與受眾需求相契合的文章。
(三)建構社群互動機制,引導受眾參與式對話
一方面,建構政務閱讀社群,凝聚社群力量。“社群主要表現(xiàn)人的關系:一群人有共同而持久的關系時,社群隨之形成。”[12]應促進受眾參與互動,增強其積極性與情感認同。閱讀是讀者與閱讀客體之間構筑的一種在精神上的共鳴與情感紐帶,記錄著個人的情感記憶,也影響著個體的價值認同。“通過閱讀,可以幫助讀者達到精神上的認同感,無形中建構了自己從屬于某個群體的身份,從而確立了集體歸屬感。”[13]“受眾對公文傳播的參與,是社會進步的表現(xiàn),對建立服務型、高效性、民意型、責任型政府具有重要價值。”[14]例如,“中國政府網”微信公眾號設置了《政務問答》《便民服務》等欄目。另一方面,引導受眾參與式對話與交流,擴寬互動、溝通、反饋渠道。同時,可以設置獎賞機制密切聯(lián)系受眾,提升新媒體文章的閱讀量、點贊數(shù)、留言量等。如“浙江宣傳”微信公眾號就設置了類似的“點贊”福利——在下方評論留言,留言在本文發(fā)布的24小時以內得到點贊數(shù)最高者,將獲贈《話由心生》一套。
(四)培養(yǎng)復合型人才,加強實踐調研
優(yōu)質的人才隊伍是政務新媒體的智力保障。“政務新媒體不僅是信息發(fā)布的平臺,也是政府與公眾互動交流的橋梁,如果沒有專業(yè)的運營人員來回應公眾的問題和訴求,就無法有效發(fā)揮政務新媒體的作用。”[15]首先,重點培養(yǎng)兼具政治素養(yǎng)與新媒體采寫編能力的復合型人才。明晰政務新媒體運營的角色定位與人員配置,提升政務新媒體工作者的職業(yè)認同。其次,培養(yǎng)政務新媒體編輯樹立“為民”的寫作觀。注重內容表達的感染力,與實踐相結合,走出“書齋”,深入“田野”,汲取寫作知識養(yǎng)分,拓寬寫作者的思維視野與書寫格局。政務新媒體編輯應加強深入細致的實踐調研,否則僅僅依靠想象或是憑借網絡上獲取的信息,則難以創(chuàng)作出精品文章。
四、結語
政務新媒體發(fā)展任重道遠,其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內容質量不佳、“流量”紅利下滑、受眾黏性低等問題甚至關停現(xiàn)象,既是目標定位與現(xiàn)實的落差,折射出政務場域與媒介場域之間的博弈,也為政務新媒體的整體發(fā)展提供了冷靜反思與展望:僅以“數(shù)據流量”視為政務新媒體的評價指標時,所謂“流量為王”勢必會帶來新一輪的惡性競爭。流量不等于實際效能,切勿盲目追逐流量紅利而本末倒置。因此,政務新媒體應以民生為目的,不斷優(yōu)化內容,探索實現(xiàn)“政務+媒體+民生”融合的新路徑,更好地發(fā)揮政務服務的效能,在積極推進政務公開、優(yōu)化政務服務、凝聚社會共識、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等方面取得良好成效。潮
參考文獻
[1]克羅圖,霍伊尼斯.媒介·社會:產業(yè)、形象與受眾:第3版[M].邱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3.
[2]曾潤喜,張吳越.智能傳播時代政務新媒體的發(fā)展維度[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2022(6):146.
[3]李白,李雨瀟.政務微信公眾號“浙江宣傳”的內容特征與傳播策略[J].新媒體研究,2024(5):69.
[4]尹連根.博弈性融合:政務微信傳播實踐的場域視角[J].國際新聞界,2020(2):100.
[5][8]要發(fā)財.政務新媒體編輯工作日常分享[EB/0L].[2022-09-04].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74382330/?_i=17690046d151c06amp;dt_dapp=1.
[6]克羅圖,霍伊尼斯.媒介·社會:產業(yè)、形象與受眾:第3版[M].邱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311.
[7]馬麗丁娜.政務新媒體融合轉型中的“科層惰性”、創(chuàng)新困境與在地調適:基于A省消防全媒體中心的參與式觀察研究[J].新聞記者,2024(5):25.
[9]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體和舊媒體的沖突地帶[M].杜永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30.
[10]張燕,鞏湘紅.全媒體時代政務新媒體的IP化策略:以“國資小新”為例[J].傳媒,2024(1):47.
[11]趙建國.論共情傳播[J].現(xiàn)代傳播,2021(6):48.
[12]萊文森.新新媒介[M].何道寬,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17.
[13]蔡騏:文化·社會·傳播[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7:227.
[14]冒志祥.網絡語境下的公文傳播與受眾參與[J].當代傳播,2010(6):108.
[15]張鵬,閆炳樺,鄭楠.智慧社會建設背景下的政務新媒體傳播態(tài)勢研究[J].傳播與版權,2024(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