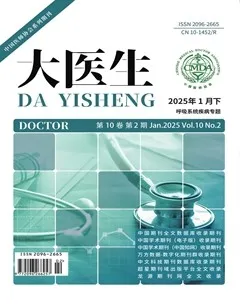探討Chinese way術式在關節鏡下治療巨大肩袖損傷的應用價值



【摘要】目的 探討Chinese way術式在關節鏡下治療巨大肩袖損傷的應用價值,為臨床治療提供參考。方法 選取2022年3月至2024年3月于揚州市江都中醫院接受治療的70例巨大肩袖損傷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根據治療方式不同分為雙排錨釘縫線橋組和Chinese way組,每組35例。雙排錨釘縫線橋組患者采用關節鏡下雙排錨釘縫線橋固定術治療,Chinese way組患者采用關節鏡下Chinese way術式治療。比較兩組患者肩關節活動度、并發癥發生情況、Fugl-Meyer評定量表(FMA-UE)評分。結果 術后3個月,兩組患者前屈、后伸、內旋、外旋的肩關節活動度均增加,且Chinese way組均大于雙排錨釘縫線橋組(均Plt;0.05)。Chinese way組患者并發癥總發生率低于雙排錨釘縫線橋組(均Plt;0.05)。術后3個月,兩組患者運動功能、感覺功能、平衡功能、關節活動度、疼痛的各項FMA-UE評分均升高,且Chinese way組均高于雙排錨釘縫線橋組(均Plt;0.05)。結論 Chinese way術式在關節鏡下治療巨大肩袖損傷的效果較好,可有效提升患者肩關節活動度和上肢運動功能,且安全性較高,值得臨床應用。
【關鍵詞】Chinese way術式;關節鏡;巨大肩袖損傷;雙排錨釘縫線橋固定術
【中圖分類號】R68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2665.2025.02.0139.03
DOI:10.3969/j.issn.2096-2665.2025.02.043
巨大肩袖損傷在肩關節疾病中較為常見,主要表現為肩袖肌腱大范圍撕裂,常引發肩關節疼痛、功能受限等問題,導致患者生活質量下降[1]。近年來,關節鏡技術不斷發展,關節鏡輔助手術治療已成為巨大肩袖損傷的主要治療手段之一,其中雙排錨釘縫線橋固定術因具備良好生物力學特性與臨床療效被廣泛應用[2]。但該術式術后再撕裂率較高,且易發生肩關節功能恢復不完全等情況。因此,探尋更有效且安全的手術方法極為重要。 Chinese way術式作為新型手術方法,近年來廣泛應用于關節鏡輔助治療巨大肩袖損傷領域,該術式采用獨特的縫合技術與錨釘布局,可有效修復肩袖肌腱,且術后并發癥發生率較低,有利于提升患者生活質量[3]。基于此,本研究探討Chinese way術式在關節鏡下治療巨大肩袖損傷的應用價值,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2年3月至2024年3月于揚州市江都中醫院接受治療的70例巨大肩袖損傷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根據治療方式不同分為雙排錨釘縫線橋組和Chinese way組,每組35例。雙排錨釘縫線橋組患者中男性21例,女性14例;年齡48~74歲,平均年齡(59.42±4.16)歲;損傷位置:左肩關節15例,右肩關節20例;撕裂長度3~7 cm,平均撕裂長度(5.37±0.21)cm。
Chinese way組患者中男性19例,女性16例;年齡47~73歲,平均年齡(59.39±4.21)歲;損傷位置:左肩關節17例,右肩關節18例;撕裂長度3~7 cm,平均撕裂長度(5.40±0.18)cm。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gt;0.05),組間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揚州市江都中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納入標準:⑴符合巨大肩袖損傷診斷標準[4],且經MRI檢查確診;⑵撕裂長度≥3 cm;⑶患側首次發病,且為單側損傷;⑷臨床資料完整。排除標準:⑴合并其他嚴重肩關節疾病者,如肩關節炎、肩袖鈣化等;⑵合并肩關節嚴重神經、血管損傷者;⑶合并精神疾病者;⑷合并血液系統疾病者;⑸合并免疫系統疾病者;⑹合并嚴重心、肺、肝、腎等重要器官功能障礙者。
1.2 手術方法 雙排錨釘縫線橋組患者采用關節鏡下雙排錨釘縫線橋固定術治療:患者取健側臥位,確保體位穩定后,行常規全身麻醉。手術區域行常規消毒,鋪設無菌手術單。通過肩關節后側入路,將關節鏡(杭州好克光電儀器有限公司,浙械注準20212060464,型號: GJ-Ⅳ)準確置入關節腔內。在肩關節前上方建立輔助通道,觀察肩關節內部結構,包括關節增生情況、肩峰形態及肩袖損傷程度。利用射頻氣化刀對肩峰下間隙進行精細清理,去除增生的滑膜組織及骨贅。存在肩峰撞擊綜合征的患者,實施肩峰成形術,通過磨除部分肩峰骨質,改善肩峰下空間,減少撞擊風險。使用探鉤測量受損肩袖的前后徑長度,評估肩袖殘端的回縮程度及修復難度。針對復位困難患者,進行肌腱松解及殘端清理。在關節軟骨邊緣位置,以90 °置入帶線錨釘,兩錨釘間距約15.0 mm。隨后,采用縫合器將縫線穿過肩袖肌腱,利用縫線橋結構固定。將肩袖斷端緊密貼合于肱骨大結節骨床,調整縫線張力,確保肌腱縫合后受力均勻,無過度牽拉或松弛現象。將外排錨釘固定于肱骨大結節外緣的10.0~15.0 mm處,鎖緊錨釘。確認肩袖修復效果滿意后,進行負壓引流,排出關節腔內的積血和滲液,逐層縫合手術切口,覆蓋無菌敷料,完成手術。
Chinese way組患者采用關節鏡下Chinese way術式治療:患者取健側臥位,背部適當后傾約30 °,患肢外展45 °、前屈20 °,行常規全身麻醉聯合臂叢神經阻滯麻醉。建立后側主入路,置入關節鏡,全面探查盂肱關節、肱二頭肌長頭腱、關節盂唇及肩袖損傷情況。建立外側輔助入路,利用射頻氣化刀對肩峰下間隙進行徹底清理,去除炎性組織及骨贅。鏡下觀察肩峰下空間及肩袖損傷情況,結合術前CT評估是否需要進行肩峰成形術。評估肩袖破口的張力及形態,對于張力較大的破口,進行充分的肌腱松解及粘連組織剝離。若岡上肌破口回拉張力較大,可考慮實施足印區內移技術,以改善肌腱的修復條件。在結節間溝后方約1 cm處的岡上肌腱止點處置入錨釘,利用錨釘上的縫線固定肱二頭肌長頭腱,實施長頭腱轉位術,以增強肩袖的穩定性。根據岡上肌、岡下肌腱的破口大小、形態及張力情況,選擇合適的錨釘(4.5 mm或5.5 mm)及縫線橋技術(單排或雙排)進行縫合固定,確保縫線分布均勻,張力適中。后縫合肩袖索、前方關節囊及肩袖間隙組織,進一步加固肩袖結構穩定性。在確認肩袖修復效果理想后,進行負壓引流,排出關節腔內的積液和積血,逐層縫合手術切口,覆蓋無菌敷料,完成手術。
1.3 觀察指標 ⑴肩關節活動度。于術后1周及術后3個月,采用量角尺測定兩組患者肩關節前屈、后伸、內旋、外旋的活動度。⑵并發癥發生情況。記錄兩組患者術后3個月內肌腱再撕裂、感染、神經損傷、血腫形成、關節僵硬的發生情況。并發癥總發生率=并發癥總發生例數/總例數×100%。⑶Fugl-Meyer評定量表(FMA-UE)[5]評分。于術后1周及術后3個月,應用FMA-UE評估兩組患者上肢運動功能,包括運動功能(滿分66分)、感覺功能(滿分24分)、平衡功能(滿分14分)、關節活動度(滿分44分)、疼痛(滿分44分)5個維度,分值越高提示患者上肢功能越好。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2.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統計與分析。計量資料用(x)描述,行t檢驗;計數資料用[例(%)]描述,行χ2檢驗。以Plt;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肩關節活動度比較 術后3個月,兩組患者前屈、后伸、內旋、外旋的肩關節活動度均增加,且Chinese way組均大于雙排錨釘縫線橋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lt;0.05),見表1。
2.2 兩組患者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 Chinese way組患者并發癥總發生率低于雙排錨釘縫線橋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lt;0.05),見表2。
2.3 兩組患者上肢運動功能比較 術后3個月,兩組患者運動功能、感覺功能、平衡功能、關節活動度、疼痛的各項FMA-UE評分均升高,且Chinese way組均高于雙排錨釘縫線橋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lt;0.05),見表3。
3 討論
肩袖是由岡上肌、岡下肌、小圓肌、肩胛下肌的肌腱組成,對肩關節的穩定性和正常活動至關重要[6]。巨大肩袖損傷是指肩袖肌腱撕裂范圍較大(撕裂口長度gt;3~5 cm或涉及2個及以上的肩袖肌腱)的一種損傷情況[7]。
本研究結果顯示,術后3個月,兩組患者前屈、后伸、內旋、外旋的肩關節活動度均增加,且Chinese way組均大于雙排錨釘縫線橋組;Chinese way組患者并發癥總發生率低于雙排錨釘縫線橋組;兩組患者運動功能、感覺功能、平衡功能、關節活動度、疼痛的各項Fugl-Meyer評定量表(FMA-UE)評分均升高,且Chinese way組均高于雙排錨釘縫線橋組。分析原因為,Chinese way術式采用特殊的錨釘布局和縫合路徑,在修復肩袖肌腱時,該布局方式能更好地模擬肩袖的生理結構與力學傳導特性,使肌腱在愈合過程中受到的應力分布更均勻,可減少局部應力集中對肌腱修復的不良影響,使肩關節能更順暢地完成前屈、后伸、內旋和外旋等動作,從而最大程度恢復關節活動度[8-9]。穩定的肩袖結構有助于恢復正常的肌肉收縮力傳遞,進而促進運動功能的提升。Chinese way術式在操作過程中能保護肩關節周圍的神經血管結構,減少手術操作對神經的損傷,使感覺功能更快、更完整地恢復;同時,由于其手術操作精細度較高,且具備良好的組織相容性,術后肩關節的炎癥反應、疼痛程度均較輕,患者進行更多功能鍛煉,促進關節活動度、平衡功能等的改善[10-11]。此外,Chinese way術式手術切口較小,術中組織的暴露時間較短,可防止細菌侵入,從而有效預防感染的發生;同時,該術式使用的錨釘與縫合線結構精細,在植入錨釘、縫合創口的過程中對骨組織的損傷較小,可降低組織粘連的可能性,減少術后骨質愈合不良的發生風險,進而降低并發癥的發生概率[12]。
綜上所述,Chinese way術式在關節鏡下治療巨大肩袖損傷的效果較好,可有效提升肩關節活動度和上肢運動功能,且安全性較高,值得臨床應用。
參考文獻
李瑛,王強,占鵬,等.關節鏡下肱二頭肌長頭腱改道轉位用于巨大肩袖損傷治療中的效果研究[J].中外醫療, 2024, 43(24): 1-4, 9.
裴杰,王青.肩袖撕裂雙排縫合技術與縫線橋技術的療效對比分析[J].中國運動醫學雜志, 2017, 36(1): 9-13, 20.
明文義,吳旭東,戴海東,等.應用改良Chinese-way技術治療巨大肩袖撕裂[J].中國骨傷, 2024, 37(9): 921-924.
張一翀,陳建海.肩袖疾病的治療: ISAKOS上肢專業委員會專家共識[J/CD].中華肩肘外科電子雜志, 2014(2): 128-135.
Singer B, Garcia-Vega J. The Fugl-Meyer upper extremity scale[J]. J Physiother, 2017, 63(1): 53.
黃東輝,梅正峰,葉辛,等.肱二頭肌長頭腱與岡上肌腱聯合固定術治療巨大肩袖損傷的療效[J].溫州醫科大學學報, 2020, 50(3): 217-220, 226.
段敏俊.關節鏡下雙排錨釘縫線橋固定術治療巨大肩袖損傷合并骨質疏松的療效觀察[J].大醫生, 2024, 9(8): 118-120.
張博,林源,任世祥,等. “Chinese way”在關節鏡下處理巨大肩袖損傷中的作用及臨床療效[J].首都醫科大學學報, 2022, 43(5): 792-798.
孫晟軒,謝曄,沈光思,等.關節鏡下“Chinese way”治療老年肩關節脫位合并巨大肩袖撕裂的臨床療效[J].中國臨床解剖學雜志, 2024, 42(3): 316-321.
尚西亮,呂婧儀,陳疾忤,等.關節鏡下肱二頭肌長頭腱轉位固定輔助替代上關節囊重建(Chinese Way)修補巨大及不可修復肩袖撕裂的臨床療效[J].中國運動醫學雜志, 2019, 38(8): 652-657.
余電柏,韋積華,藍常貢,等.關節鏡下“Chinese Way”兩種術式修補巨大及不可修復肩袖撕裂的臨床研究[J].微創醫學, 2021, 16(5): 624-629.
尚西亮,呂婧儀,陳疾忤,等.關節鏡下肱二頭肌長頭腱轉位固定輔助替代上關節囊重建(Chinese Way)修補巨大及不可修復肩袖撕裂的臨床療效[J].中國運動醫學雜志, 2019, 38(8): 652-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