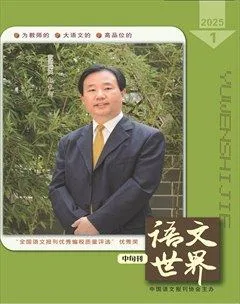講解(節選)
國文課里讀到文言,就得作一番講解的功夫。或者由同學試講,由教師和其他同學給他訂正(講得全對,當然無須訂正);或者徑由教師講解,同學們只須坐在那兒聽。兩種方法比較起來,自然前一種來得好。因為讓同學們試講和訂正,同學們先作一番揣摩的功夫,可以增進閱讀的能力。坐在那兒聽固然很省事,不大費什么心思,可是平時自己閱讀沒有教師在旁邊,就不免要感到無可依傍了。不妨想一想,為什么要講解?回答是:因為文言與咱們的口語不一樣。
像有一派心理學者所說,思想的根據是語言,脫離語言就無從思想。就咱們的經驗來考察,這種說法大概是不錯的。咱們坐在那兒悶聲不響,心里在想心思,轉念頭,的確是在說一串不出聲的語言——朦朧的思想是不清不楚的語言,清澈的思想是有條有理的語言。咱們心里也有不思不想的時候,那就是心里不說話的時候。現在咱們想心思,轉念頭,都是在說一串不出聲的口語。這也是作文該寫口語的一個理由。心里怎樣想就怎樣寫出來,當然最為親切,不但達意,而且傳神傳情。
依此推想,古來人思想所根據的是他們當時的口語,寫下來就是現在咱們所謂文言。咱們說古來人,包括不同時代的人。還有須知道的,古來人雖然根據他們當時的口語來思想,待寫下來的時候,為了書寫的方便,把他們的口語簡縮了,這是很尋常的事情;因而文言與他們的口語多少有些出入。還有,后一時代的人也可以學習前一時代的語言,用前一時代的語言來寫文章,或者參用一些前一時代的語言來寫文章(其實就是根據前一時代的語言來思想),而且不限于前一時代,盡可以伸展到以前若干時代;因而某一時代的文言大都不純粹是某一時代的語言,往往是若干時代的語言的混合體。還有,文言中間也有并非任何時代的口語,而是一種人工的語言,例如駢體文。用駢體文來寫作的人,他平時的思想當然也根據他當時的口語,但是他要作駢體文的時候,就得把他的思想加一道轉化的功夫,轉化為根據那種人工的語言來思想,這才寫得成他的駢體文;或者他對于那種人工的語言非常熟習了,像對于他當時的口語一樣,因而也不需要什么轉化的功夫,他要寫駢體文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根據那種人工的語言來思想。(這種經驗咱們也有的。咱們寫現代文,自然是根據咱們的口語來思想。但是咱們也可以寫文言;在初學的時候,是加一道轉化的功夫,轉化為根據文言來思想;到了熟習的時候,要寫文言就徑自根據文言來思想了。)
寫作的方面且不多說,這一回單說理解的方面——理解文言的方面。咱們是根據現代的語言來思想的,而文言是根據以前若干時代的混合語言來思想的,這其間就有了距離。咱們要徹底地理解文言,須做到與那些文言的作者一樣,能夠根據文言來思想。凡是能夠通暢地閱讀文言的人都已達到了這個境界。他們在閱讀文言的時候,拋開了從小學會的最熟習的口語,仿佛那文言就是他們從小學會的最熟習的語言,他們根據這個來領受作者所表達的一切。但是,初學文言的人就辦不到這一層。他們還沒有習慣根據文言來思想,對著根據文言來思想的文言,只覺得到處都是別扭似的。消除那些別扭須作一道轉化的功夫。根據咱們的口語是怎么說的,根據文言就該怎么說,要一點一滴地問個清楚,搞個明白;反過來,自然也知道根據文言是怎么說的,根據咱們的口語就該怎么說。這就是轉化的功夫。轉化的功夫做到了家,口語與文言的距離消失了。遇見文言就可以根據文言來思想來理解,與平時根據口語來思想一樣。其實這時候已經多熟習了一種語言了(文言),正同熟習了一種外國語相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