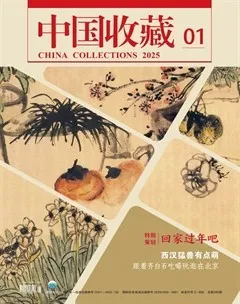“財用恒足”實則不足
本人收藏了一枚“寶鞏金城背財用恒足”開爐錢,該開爐錢是清朝前期寶鞏局所鑄的一枚具有明確地理標識的錢幣。此幣為黃銅質,圓穿,錢徑36.9毫米,邊厚2.6毫米,重量17.39克;正面四字“寶鞏金城”對讀,背面四字“財用恒足”對讀。
“金城”是甘肅省會蘭州的古稱。“寶鞏”,寶,珍也;鞏為地名,在今天甘肅省隴西縣鞏昌鎮。清康熙六年(1667年),戶部準令各省開爐鑄錢,陜西右布政使司奏準在鞏昌府設寶鞏鑄錢局,所鑄錢幣正面為漢文“康熙通寶”,背面滿漢文“鞏”,存世極少。康熙七年(1668年),改鞏昌布政使司為甘肅布政使司,將治所遷至蘭州,保留鞏昌府鑄錢局稱號。康熙九年(1670年)鑄錢局移至蘭州,蘭州鑄造的錢幣仍使用寶鞏局稱謂。
“財用恒足”出自《大學》:“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這枚開爐錢把“財恒足”變成“財用恒足”,多了一個“用”字,內涵發生了變化:“財恒足”強調財富的累積和保持,而“財用恒足”除了強調財富的累積和保持外,還要在財富的使用過程中有充足和持續的保證。
這枚“寶鞏金城背財用恒足”開爐錢是康熙九年(1670年)寶鞏局遷至蘭州后所鑄造的開爐錢幣,作為具有明確地理標識和財富期許的錢幣實物,其見證了甘肅布政使司的成立,見證了寶鞏局易址金城蘭州的事實,也反映了甘肅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
隨著甘肅戰略位置的重要性日益顯著,甘肅布政使司設立,清政府對甘肅的經略和財政政策發生了變化,但甘肅財政困難的局面并未得到改善。金城蘭州鑄造這枚“財用恒足”開爐錢的背后,隱藏著如下歷史背景:

一是清政府對甘肅的軍事經略。甘肅地處中國西北部,是中原與西域的必經之路,具有“控大漠、遏西藏、連西域”的戰略地位。清政府把甘肅作為西北的戰略核心來經略,在甘肅省境內駐扎了大量的軍隊,包括八旗軍和綠營軍等,以維護西北的安定。如康熙、雍正時期駐軍2.8萬余人,乾嘉時期為15730人,道光時期為9479人,光緒末減為2600余人。長期大量的駐軍,導致甘肅軍餉需求加劇。
為解決軍餉問題,清政府在甘肅實施“協餉”制度,通過從其他富裕省份協撥銀兩,減少中央政府對甘肅的直接財政壓力,但甘肅一直存在著協餉調撥不及的困境,迫使甘肅自己解決這一難題。
二是清政府前期對甘肅的經濟開發。作為一個具有潛在價值的大經濟區,清政府對西北的經濟開發十分重視。康熙年間,在新疆屯田之前,清政府已對陜西、甘肅實施鼓勵移民的政策,康熙議準甘肅“安插失業窮民六款”。甘肅移民是一般移民和遣屯、民屯、兵屯的結合,移民屯耕格局從水利和自然經濟條件較好的河西走廊由東向西點線結合,移民的優惠政策是建立房屋、給予路費、口糧、籽種、牛具、牛羊以及相應的銀兩,承認土地所有權,頒給關防印信等,導致甘肅地區的人口相應增長。
清前期,銀兩和銅錢并行。銅錢主要用作經濟生活所需,隨著人口增長、經濟發展,民眾對銅錢的需求加大。寶鞏局只有通過鑄造錢幣,增加市場的貨幣供應量,才能促進甘肅經濟的繁榮。雍正四年(1726年),甘肅巡撫石文焯奏請開爐鑄錢,在鞏昌府鑄錢局停鑄59年后,寶鞏局于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在蘭州鑄錢。
三是開源節流的財政政策。甘肅地處西北干旱地區,自然條件惡劣、災害頻發、戰亂不斷,手工業和商業落后,財政收入困難。同時,甘肅缺乏銅料,鑄幣時間短,錢幣鑄量很小,康熙、雍正、咸豐、同治四個時期,鑄造錢幣時間總共才十三四年。因此,甘肅主要依靠外省調入的“協餉”維持開支。據《蘭州古今注》記載,嘉慶、道光年間,江蘇等11省調撥甘肅餉銀470萬兩。
針對財政拮據、“協餉”不濟的難題,陜甘總督左宗棠采取加強水利管理、鼓勵農業生產等措施,增加稅收來源,減少對外依賴。嚴格官員俸祿和公務用度,制定和執行嚴格的財務審計和監督制度,確保財政資金合理使用,實現財政的節約和開支的減少。
總之,這枚開爐錢上的“財用恒足”折射了當時甘肅“財用不恒足”的困局,反映了甘肅布政使司想改變這種現狀的強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