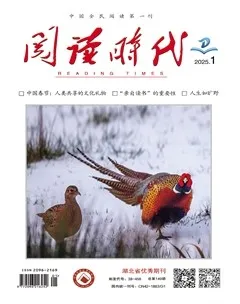笑中窺史,品味中國式幽默

已故著名學者王學泰的《中國笑話史》,作為首部以中國笑話發生、發展為研究對象的學術專著,以海量史料為參照,從“笑話”這一解讀中國歷史與文明形態的視角出發,為讀者展示了品味中國式幽默的別樣體驗。書中,無論是剖析“笑與笑論”,探討“笑話作為一種文體”,還是解讀“引人發笑的幾個要素”“幽默感是笑話創作的心理基礎”,都展現出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
在對笑話歷史演進的梳理上,王學泰彰顯出深厚的史學功底。由西周至魏晉,笑話經歷了萌芽、附庸和自覺三個階段。在萌芽時期,通過對西周到春秋時代社會狀態的描繪,挖掘出最早的笑話與笑事,并于《易經》《詩經》《左傳》等文獻中尋找笑的蹤跡。在附庸時期,從諸子百家著作中的笑話,到《史記》《漢書》等正史中含著眼淚的微笑和嚴肅背后的詼諧,都展現出笑話與當時社會、思想的緊密聯系。而進入魏晉這個“文學的自覺時代”,笑話迎來了獨立的契機。從寫人物與品評人物的風氣,到人與人之間相互嘲謔的風氣,都推動了笑話的發展,《笑林》的誕生更是標志著笑話作為一種獨立文體的重要里程碑。
當時的笑話是為說理服務的,與個人性格關系不大。《莊子》之“朝三暮四”“邯鄲學步”“井底之蛙”,《韓非子》之“守株待兔”“鄭人買履”“濫竽充數”,以及《孟子》之“揠苗助長”,《列子》之“杞人憂天”,《尹文子》之“狐假虎威”……諸子典籍里的笑話,精警短小,寓意深刻,生動呈現出人生哲理和社會現象。
如果說《笑林》所錄笑話大都源自市井小民,那么《世說新語》的誕生則更多地反映了當時文人士大夫的趣味,以及其側重語言的機智與雋永。譬如《世說新語·排調》中的一節:“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寥寥數語就勾勒出了郝隆生性狂傲、豁達爽朗的名士形象。該書從“贊頌類笑話”“笑話中的溫情”“揭示人性丑陋的笑話”等方面,通過一個個或令人捧腹,或發人深思的笑話,勾勒出當時獨特的文化氛圍,展現了魏晉時期文人階層豐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和復雜多面的人性特點。
笑中窺史,余味無窮。中國式幽默,是溢出來的智慧,是沉淀在歷史中的風趣,是鐫刻在文化里的詼諧。透過《中國笑話史》這扇獨特的窗口,我們得以窺見中國歷史與文明形態的另一種風姿:有民間智慧的蓬勃力量,也有社會萬象的鮮活縮影。這種見微知著的解讀方式,讓我們在輕松一笑間,亦能領略歷史的厚重和文化的深沉韻味。
(源自《濟南時報·新黃河》,有刪節)
責編: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