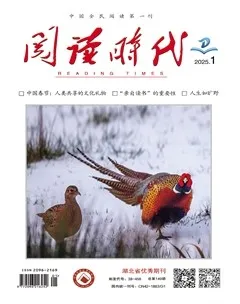陳春成:讓我躲在書的后面,忘掉張大千的胡子
想象力的消失
我讓所有的想象力都集中到腦部。它們是一些淡藍(lán)色的光點(diǎn),散布在周身,像螢火蟲的尾焰,這時(shí)都往我頭頂涌去。過了好久,它們匯聚成一大團(tuán)淡藍(lán)色的光芒,往我頭上飄升起來,漸漸脫離了我,像一團(tuán)鬼火,在房間里游蕩。這就是我的對(duì)策:我想象我的想象力脫離了我,于是它真的就脫離了我。那團(tuán)藍(lán)光向窗外飄去。我坐在書桌前,有說不出的輕松和虛弱,看著它漸漸飛遠(yuǎn)。最后它像彗星一樣,沖天而去。
——《夜晚的潛水艇》
問:如果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和游刃有余、信手拈來的筆力只能二選一,你會(huì)選擇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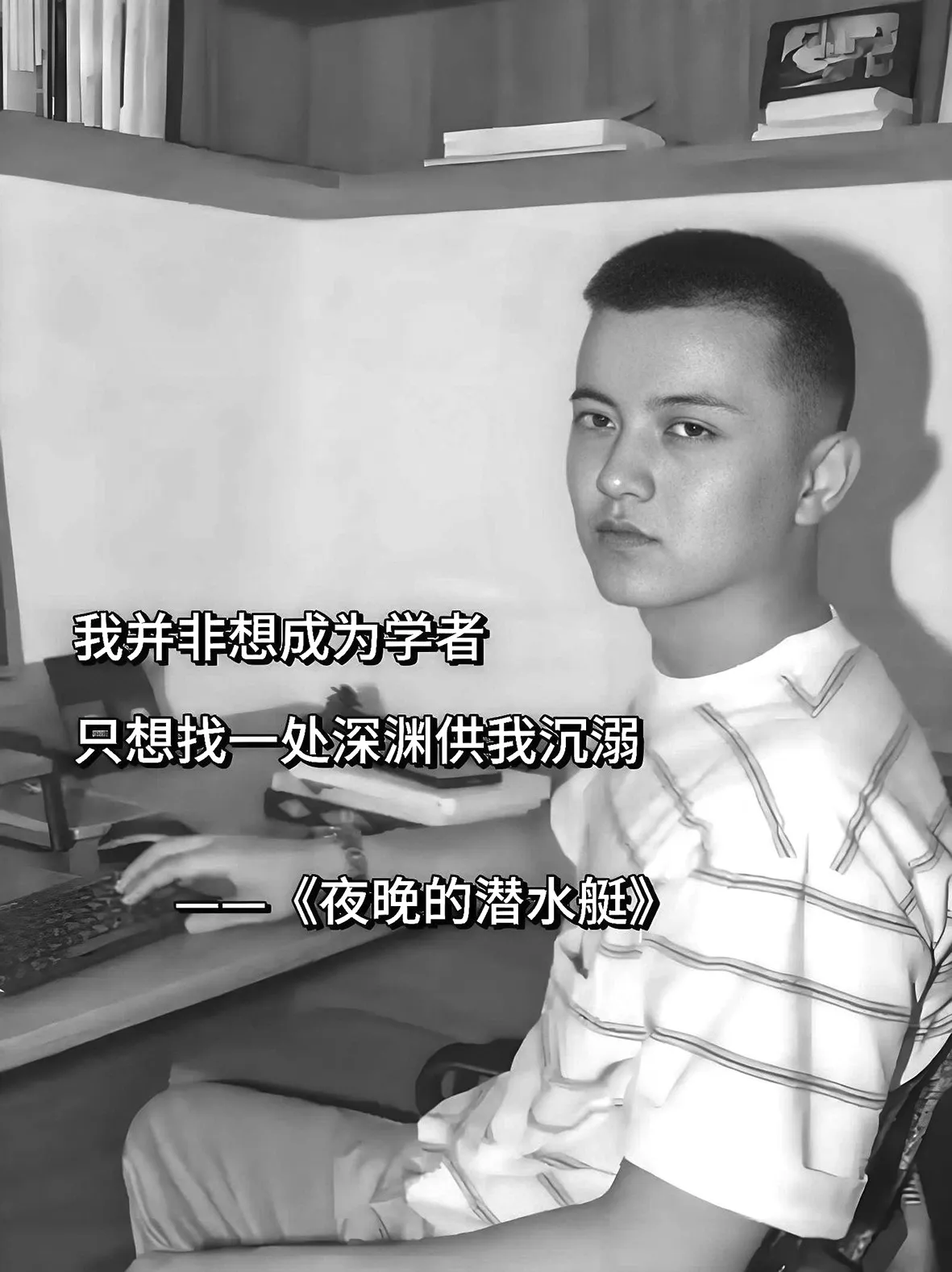
陳春成:我會(huì)選擇想象力。因?yàn)槲矣X得,有前者、沒有后者的狀態(tài)就是我小時(shí)候的狀態(tài)。如果沒有筆力,你就是不能成為一個(gè)作家而已,但是你可以享受想象的樂趣,但我好像沒辦法想象沒有想象力的感覺是怎樣的。我也的確被想象力困擾過,比如說在學(xué)習(xí)或工作上成了一個(gè)容易走神的人。
我沒想過想象力的消失,也不會(huì)擔(dān)心。我們小時(shí)候有很多胡編亂造的故事,比如20世紀(jì)80至90年代的那些世界未解之謎,有一些完全是杜撰的,胡亂編一些外國人名,就展開一個(gè)外星文明或史前文明的故事,我很喜歡這種氣質(zhì)。但對(duì)于我來說,這種寫法好像是一個(gè)“只能一不能二”的東西。
最后的作品
再精致的散文,也總有一些字可以增減。想要那種不可動(dòng)搖的圓滿,只有求諸詩歌。我要寫這樣的詩歌:它的語言應(yīng)是最優(yōu)美的現(xiàn)代漢語,不應(yīng)求助于古詩的格律,但音韻與結(jié)構(gòu)要如古詩般完美。文筆要節(jié)制而輝煌,吟詠的對(duì)象包括但不限于整個(gè)世界。
——《傳彩筆》
問:如果現(xiàn)在你的人生只能寫最后一篇文章,你會(huì)選擇什么體裁?是古體詩、現(xiàn)代詩還是小說或者其他?
陳春成:如果是最后一篇的話,我希望寫古體詩,希望獲得一種不可動(dòng)搖的、圓滿的感覺。我覺得古體詩是高于小說的。我不是很想寫很像小說的那種小說,我希望更偏向詩的感覺——當(dāng)然這也可能只是我現(xiàn)在這幾年的審美。詩首先是高于小說的,但我總覺得現(xiàn)代詩好像沒有形成一個(gè)特別定型的東西,似乎每一句都是可斟酌的,而古詩會(huì)讓人覺得非常完美,像行星或山體一樣不可動(dòng)搖。
如果有值得沉迷的東西,愿意過每天一樣的生活
問:如果你有再選擇一次的機(jī)會(huì),你會(huì)希望做出意大利“隱身”作家費(fèi)蘭特那樣的選擇嗎?沒有人知道她到底是誰,她拒絕露面接受采訪,躲避媒體的盤問和大眾的審視。
陳春成:我覺得是挺好的選擇。但是我現(xiàn)在也都接受了,就回不去了。反正我現(xiàn)在就提起精神來,想著等這一波過去了就好了。
問:失去興趣,是說這個(gè)東西對(duì)你來說不再有吸引力了,你就沒有動(dòng)力把它寫出來是嗎?
陳春成:會(huì)這樣,我覺得大部分作家都會(huì)經(jīng)歷這個(gè)過程。我沒辦法寫一個(gè)自己不想再看第二遍的東西,畢竟寫作對(duì)我來說是一個(gè)挺愉快的過程。我很難做那種特別艱苦的事情,可能正因如此我也寫不出一些特別偉大的作品吧,因?yàn)槲姨⒅刈约涸趯懽鲿r(shí)候的愉悅感,或者說寫得太舒服了,很多東西不會(huì)去強(qiáng)攻,我缺少那個(gè)東西。但另一方面,寫短篇可能也是一個(gè)比較舒展從容的辦法吧。
流行詞是語言退化,極不準(zhǔn)確且磨損漢語
問:“內(nèi)卷”。我不知道在你生活的環(huán)境里面,是否也會(huì)感受到比較世俗意義上的焦慮或壓力。
陳春成:肯定有,但是說實(shí)話,我(就算)想卷也不是一個(gè)特別能卷的人,所以我看得比較淡。我覺得人不用去比,從小我父親也是這樣教育我的,我覺得這種東西不是特別有意思,我工作的氛圍也不太需要我去內(nèi)卷。一些年齡方面的焦慮我肯定還是會(huì)有,比如說我現(xiàn)在三十歲剛過,三十一歲了,在家庭生活等方面肯定會(huì)慢慢有一些變化。
其實(shí)我不是特別喜歡“內(nèi)卷”這種流行詞。好像每隔一陣子就會(huì)出現(xiàn)一兩個(gè)流行詞,所有人就一直用這個(gè)詞,我覺得這是一種語言的退化,把這個(gè)詞磨損過度之后就完全地拋開了它,比如“永遠(yuǎn)的神”這種詞。我不喜歡這種語言環(huán)境,這會(huì)磨損我們的漢語,這些詞不足以概括那么多東西,很多都是牽強(qiáng)附會(huì),將這個(gè)詞磨損之后再完全拋開,以后沒有人再去說。我不太喜歡這些流行語,它們不是精準(zhǔn)的、可以在討論時(shí)使用的語言。
(源自“理想國”)
責(zé)編(見習(xí)):徐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