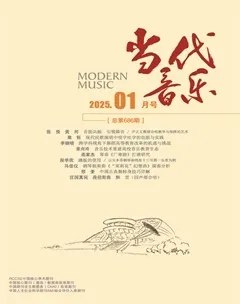淺析《大江東去》音樂性與文學性的交融
[摘 要] 《大江東去》是我國音樂家青主創作的一首藝術歌曲,被認為是“中國藝術歌曲創作的開山之作”。這首作品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代表作,它既借鑒了西方作曲技法,又表現出了蘇軾詞作《念奴嬌·赤壁懷古》的情感。不僅如此,這部作品也是音樂與文學成功交融的典范,對后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本文依據音樂要素綜合分析藝術歌曲《大江東去》的音樂性,再根據歌詞和詞作《念奴嬌·赤壁懷古》分析作品中存在的文學性,最終探索這部作品中音樂與文學相結合的方式。
[關鍵詞] 《大江東去》;音樂性;文學性;交融
[中圖分類號] J605" "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2233(2025)01-0136-03
一、作品簡介
《大江東去》是我國現代音樂家青主根據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創作的一首藝術歌曲。詞作《念奴嬌·赤壁懷古》是蘇軾被貶至黃州游覽赤壁時有感而發,借赤壁之戰時周瑜雄姿英發名傳千古卻依然隨著歷史長河消散,感慨人生短暫以及人的生命在歷史面前的渺小。這部作品是青主于1920年在德國創作的。[1]此時國內派系林立,軍閥混戰,青主也想為國內的民主事業盡一份力,他將自己比喻為當年的蘇軾,同蘇軾一樣有著濃烈的愛國情懷,卻不料命途多舛,無法實現報國之志。
二、作品的音樂性與文學性
(一)音樂分析
這首藝術歌曲的曲式結構為帶尾聲的單二部曲式,根據蘇軾詞作上下闋的結構而來,上闋旋律采用了宣敘調的形式,莊重嚴肅,大氣豪放;下闋則是以詠嘆調的形式抒發情感,形成鮮明對比。曲式結構如下(以調式d-D-d為例)。
首先歌曲A段為非方整形樂段,調式以d小調為主。開頭a樂句的音樂材料直接以屬音到主音向上的跳進開始,然后整體級進向下進行到小字一組的la,隔半拍休止后級進上行又急轉直下到小字一組的mi,旋律線條上下波動呈波浪形。樂句前后強弱對比鮮明,伴奏以柱式和弦為主,一個字對一個和弦,鏗鏘有力,氣勢磅礴。3、4小節的材料是對前兩小節的陳述做進一步補充,材料級進下行到小字一組的降mi上;鋼琴伴奏右手同旋律一樣共同進行,左手為柱式和弦;調式進入降A大調,和聲停留在降A大調的Ⅰ級上。a樂句短短四個小節就能夠使聽眾身臨其境,仿佛站立在長江邊,望著波濤滾滾的江水一路向東,為全曲的氛圍奠定了基調。
隨后b樂句以級進向上的均八分音符為主,中間各穿插一拍的休止,不斷由弱到強。伴奏織體右手是隨著旋律向上的柱式和弦,左手為向下跳音進行的四分音符,形成右手與人聲同步進行,左手與人聲一呼一應的效果,調式在第6小節轉入f和聲小調,和聲停留在Ⅰ級和弦上。b樂句7、8小節旋律材料和鋼琴伴奏都是根據a樂句后半部分的材料發展而來,和聲停留在Ⅰ級上。B樂句結合歌詞欣賞能感覺到剛剛被拉到長江邊上的聽眾似乎還不清楚身處何地,然后蒙眬地看見赤壁場景,逐漸會想起三國時期火燒赤壁的歷史故事。
間奏部分9—12小節的伴奏旋律材料由十六分音符、八分音符、四分音符按照特定的排列方式進行,旋律線條呈波浪形,全程由弱到強反復進行,而且每個音符都有重音記號,情緒極為激烈,好像長江水流翻涌不斷,調式在第12小節轉入d小調。13、14小節的材料為間奏前半部分材料的簡化,只有一條旋律線進行,而且都為弱奏,仿佛是洶涌江水的回聲,也為歌曲后面的內容進行過渡。
c樂句的材料為b樂句材料的變化發展,伴奏織體為間奏13、14小節伴奏織體的延續,都是固定的和聲在Ⅰ級上的和聲音程,給人意猶未盡之感。17—20小節的旋律材料和伴奏織體依然是b樂句的變化發展,19、20小節是17、18小節的變化重復,二者相差五度,一強一弱,銜接緊湊,形成鮮明的對比,進一步增強情感。
20—22小節d樂句的旋律材料在a、b樂句都能找到類似的材料。分析到此不難發現,八分休止加八分音符連著兩個平八,再以四分或二分音符結束(例如“江山如畫”這四個字的節奏型),這個特定的節奏型是這個作品最具有特征的符號。上闋的ab兩個樂句的“尾巴”、間奏、尾聲,都是以這個節奏型進行發展創作,運用這個節奏型時,鋼琴伴奏也會演奏同樣的旋律,進一步強調這個節奏特征,因此不難窺探出青主在進行創作時的構思。
B樂段音樂風格發生了變化,無論是旋律、節奏,還是伴奏織體、調式調性等都與A段形成對比。調式由d小調轉入同名大調D大調,旋律從宣敘調的風格轉為詠嘆調的風格。旋律以主和弦的三音開始,上下起伏,節奏大多以一個二分音符帶兩個四分音符進行發展,鋼琴伴奏右手部分是主旋律,左手部分是連續的反復上下波動的三連音節奏型,和聲以Ⅰ、Ⅵ為主,28、29小節短暫的轉入降G大調后又回到D大調,在41小節樂段臨結束時調性轉回了主調d小調,最終和聲結束在Ⅰ級。
43—53小節是作品的尾聲部分。旋律整體是休止的,只有“人生““如夢”二詞以單音出現,風格回到宣敘調的形式。伴奏是以Ⅰ級分解和弦用大附點的節奏形式進行排列,與主旋律部分形成巧妙的搭配。這部分以鋼琴伴奏作為情緒的渲染,給人以思考沉靜人生的空間氛圍。
最后,第51—53小節再次出現A段的特征性節奏型,旋律和伴奏都以主和弦的根音一路向上,音樂由弱漸強,以表達作品從對人生的思考到豁然開朗,從音樂性上形成與《念奴嬌·赤壁懷古》的完美配合。
(二)文學分析
《大江東去》的歌詞直接借鑒蘇軾的詞《念奴嬌·赤壁懷古》,[2]詞中描繪的赤壁景觀,以山、浪等客觀存在暗喻現實世界與歷史浪潮,既描繪出了事物的客觀形象,又寫出了事物的精神。開篇“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描繪出長江流水磅礴的氣勢,展現出龐大的意境美。短短一句話直接表現詞作行文豪放的特點。“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則是借赤壁江水的場景聯想到赤壁之戰的史實,從而具體展開對“千古風流人物”的感慨。“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對赤壁寬闊兇險的場景進行更加細致夸張的描寫,充分展現蘇軾豪放不羈的創作風格。同時,這一句也是歌詞改動的主要部分,“亂石穿空”改為“亂石崩云”“驚濤拍岸”改為“驚濤裂岸”“卷起千堆雪”做了一次重復。“穿空”改為“崩云”,“拍岸”改為“裂岸”,從文學的角度上看,他們之間所表達出的效果是接近的,都能夠表現出惡劣兇險的環境,后者表現得更為夸張。從音樂的角度分析,我們分別將蘇軾原版的歌詞和青主改過后的歌詞代入旋律試唱能夠明顯發現,青主改版過后的歌詞更加適合代入音樂旋律。“亂石穿空”這四個字在誦讀時是連貫的,而在歌曲中這四個字中間穿插了一個四分的休止,它并不是連貫的。“穿空”改為“崩云”運用被動句式將四個字分開,完美契合了音樂的旋律。從歌唱咬字的角度來考量,“崩”的聲母“b”和韻母“enɡ”咬字相比“穿”的聲母“ch”、韻母“uɑn”更加適合歌唱的咬字,而且“崩”字具有力量感,能夠更加夸張地表現出環境的兇險。“驚濤拍岸”改為“驚濤裂岸”也是同樣的道理。“卷起千堆雪”重復一次從文學的角度看是有著些許加強語氣的作用,從音樂的角度看,重復的兩者之間旋律節奏相同,但在音區和強弱上形成對比,著重表達了環境的險惡。這一句歌詞的改編能夠使人感受到青主在進行創作時對歌曲整體表現的考究。“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這一句是上闋的結尾句,“江山如畫”是對上文赤壁場景的總結,“一時多少豪杰”是為下文回憶周瑜火燒赤壁鋪墊,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這兩句是對火燒赤壁史實的細致描寫,但是其中存在部分歧義。[3]赤壁之戰是孫劉聯軍與曹軍對抗,吳軍的主帥是孫權,孫權“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周瑜并不是赤壁之戰的主要貢獻者。火燒赤壁無論是看出曹軍不善水還是草船借箭,大多是諸葛亮所提的計策,文中“羽扇綸巾”的形象也明顯是指諸葛亮。但是根據蘇軾描繪的內容,仿佛周瑜是赤壁之戰中料事如神的謀士,很容易讓人誤解。不過,中國自古以來無論是藝術還是文學都崇尚寫意而非寫形的美學態度,蘇軾對詞的考量應當是更偏向于意境和感受,是抽象的而非具體的,他并沒有刻意地描繪赤壁之戰誰是勝利者,誰為赤壁之戰的勝利做出最多的貢獻,蘇軾對這段史實的描繪只是做了簡寫,這首詞的中心內容在于風流人物都隨著歷史消散,無論是周瑜還是諸葛亮。因此對這一句的深入解讀能夠進一步感悟到蘇軾豪放不羈的人格魅力。
“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是對蘇軾內心的直觀描寫,蘇軾被貶至黃州,空有一身報國志,內心的憤懣無處可泄,他羨慕那個英雄輩出的時代,然而時光易逝,未壯志報國就已年邁,詞句中充滿了對自己的嘲諷和遺憾。“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這一句簡短有力,充分展現了蘇軾灑脫的人生態度。[4]人生就像一場夢,不要對人生中所遇到的事物過于執著,不如享受當下,舉杯與江水明月共飲。這一句既是全詞的結尾也是中心主旨,一句話就拉高了蘇軾的人生的境界與格局拉高。即使蘇軾的身體隨著歷史的長河消散,但他的人格會依然屹立在歷史的長河中。
三、作品音樂性與文學性的結合
(一)音樂進行與音調的結合
蘇軾的詞《念奴嬌·赤壁懷古》通過對赤壁之戰的緬懷,表達出作者在歷經人生世事無常后依然展現出了對人生豁達樂觀的態度。[5]青主的曲其旋律貼合歌詞的聲調格律,如“大江東去”四個字,其平仄規律為“仄平平仄”,這一句的音樂旋律整體呈現出一個拱形,基本符合了詞的平仄規律。“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其平仄規律為“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其旋律在“平平”的字上進行時以級進為主,在“平仄”的字上則是為跳進。
(二)詩詞結構與音樂結構結合
詞的結構分為上下闋,上闋繪景并引出下闋,下闋回憶抒情,而歌曲的結構同詞一樣分為兩段,A段宣敘調,B段詠嘆調,尾聲是對B段抒情感慨人生無常后的自我解脫。從結構上看,歌曲的上下兩段形成鮮明的對比,而蘇軾的詞上下闋之間沒有明顯的對比,但仔細品味詞的內容不難發現上下闋的風格是存在一定對比的。上闋以赤壁的險惡環境引出周瑜火燒赤壁的故事,以敘述為主;下闋借周瑜火燒赤壁大敗曹軍雄姿英發,然而這一切都隨著歷史的長河消散而去,借此抒發自己命途多舛、胸懷壯志卻不能實現的感慨,以抒發情感為主。所以,詞作的上下闋具有一定的對比特征,青主用音樂的形式將詞作上下闋的對比放大,使聽眾能夠更加清晰明了地體會作品中的情感。
(三)音樂動機的創作與詩詞的聯系
慢慢誦讀蘇軾的詞作,細細體會詩詞中蘊含的抑揚頓挫,不難發現,我們在誦讀“千古風流人物”時通常會把“千古”二字連讀,“千古”與“風流人物”斷開,將“風流人物”四個字一字一頓。不僅如此,“三國周郎赤壁”中“三國”是連讀,“三國”與“周郎赤壁”斷開,“周郎赤壁”是一字一頓;“一時多少豪杰”中“一時”是連讀,“一時”與“多少豪杰”斷開,“多少豪杰”也是一字一頓。在誦讀詞作的過程中能明顯感受到這種獨有的抑揚頓挫的規律,如果用音樂節奏的形式來展現這種規律,可以表示為兩個八分音符帶三個四分音符(■)。這種特點與前文所說的A段中常出現的特征性節奏型具有一定的關聯。只要在這個節奏型的前面加上一個八分休止符和一個八分音符,就變成A段中出現的特征性節奏型。所以,在進行歌曲旋律創作的過程中,青主必然也曾無數次地誦讀蘇軾的詞,然后以詞的抑揚頓挫的規律進行音樂的創作。
總" "結
通過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探究《大江東去》這首作品,我們不難感受到青主在創作這首音樂作品時的考究程度。青主嫻熟的西方作曲技術與蘇軾流傳千古的詩詞相得益彰,為中國音樂發展的歷史畫卷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青主創作出的音樂作品及其風格和形式成為中國近代里程碑式的創新,開辟了現代音樂與中國古詩詞相結合的創作形式,為現代的古詩詞藝術歌曲創作風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于洋.歌曲《大江東去》音樂分析與歌唱演繹[D].南京師范大學,2017.
[2] 楊生善.淺談蘇軾詞作及《念奴嬌·赤壁懷古》[J].文學教育(上),2020(11):62-63.
[3] 錢玉趾,陳思同.對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的正解[J].文史雜志,2018(03):37-44.
[4] 尹飛揚.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意境分析[J].散文百家(新語文活頁),2018(11):11.
[5] 周茂文.青主《大江東去》鋼琴伴奏的藝術特點[D].青島大學,2022.
(責任編輯:韓瑩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