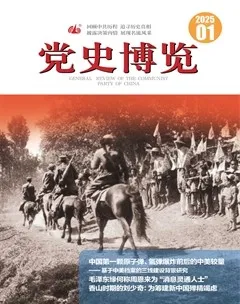《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形成過程中的國際因素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下稱《歷史決議》)原則性通過于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但其開始形成可追溯到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及毛澤東所寫的《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無論是《結論草案》還是《歷史決議》,都很明顯地受到了蘇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下稱《聯共(布)黨史》)的影響,而《歷史決議》在形成及完善時的有些表述也與共產國際或蘇聯的態度密切相關。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領導下的革命運動也是國際共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就決定了在考察中共編撰《歷史決議》時蘇聯與共產國際的因素是不可忽略的。
《聯共(布)黨史》對《歷史決議》形成的影響
《聯共(布)黨史》出版于1938年,是斯大林為鞏固自己在聯共(布)黨內的地位而主持寫就的。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共自然也被要求學習傳播這部著作。1939年7月15日,任弼時在莫斯科致電中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四個問題:“(一)是否收到了中文版《聯共(布)黨史》1萬冊以及該書紙型?(二)此書發行如何,賣出了多少本?(三)為學習該書你們采取了哪些措施?(四)對此書有什么評論?”他還說,“發行和學習此書是提高黨的思想水平的一個轉折點和強大杠桿,是保證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深入最廣大群眾的一個最有力的手段。在兄弟黨那里此書的發行進行得很成功”。此文件上有季米特洛夫的簽字,充分體現了共產國際對傳播這本書的重視。中共中央于1939年8月18日給任弼時回電說明了《聯共(布)黨史》的發行傳播情況,稱:“這部書對于提高我們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會起重大作用。現在我們在采取更多的措施來擴大該書的學習范圍。”這說明中共對《聯共(布)黨史》有著足夠的重視,這使得《聯共(布)黨史》在中共黨內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中共對《聯共(布)黨史》的重視不僅源自共產國際的指示,還因為該書高度契合了中共的現實需要。這從毛澤東對《聯共(布)黨史》的高度評價中便可以看出。1939年5月20日,毛澤東在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上講話時提出,要把《聯共(布)黨史》長期地學下去。1941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指出:“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又應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為中心的材料。《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
1941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關于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中再次提出,“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以《聯共(布)黨史》為學習的中心”。1942年,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多次提到《聯共(布)黨史》,并將從中摘取的部分內容列入會議散發的《宣傳指南》四篇文章中,號召黨員依照列寧的精神去做宣傳工作。1942年3月10日,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再次提及《聯共(布)黨史》。他說:“我們讀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它告訴我們,布爾什維主義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和方法,創造了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要按照同樣的精神去做。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將《聯共(布)黨史》列為5本要讀的馬列主義的書。他說:“還有斯大林主持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比較厚一點。這本書是歷史的,又是理論的,又有歷史,又有理論,它是一個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成功的歷史。”毛澤東上述的一系列講話,充分說明了他對《聯共(布)黨史》一書的重視,這種重視更多源自中國革命實踐中的現實需要——以官方文件的形式鞏固延安整風的勝利成果、團結全黨為中國革命事業奮斗。

《聯共(布)黨史》對《歷史決議》的最主要影響體現在其敘述模式上。《聯共(布)黨史》將斯大林樹立為蘇聯正確路線的代表,將聯共(布)黨史簡化敘述為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斗爭史,以樹立斯大林的光輝領袖形象。《聯共(布)黨史》在導言中便指出了其著重于路線斗爭的特點。導言寫道:“聯共(布)在工人運動內部是同小資產階級的黨派,即同社會革命黨(更早是同他們的前輩——民粹派)、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和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作原則斗爭中,在黨內則是同孟什維主義的、機會主義的派別,即同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民族主義傾向分子和其他反列寧主義集團作原則斗爭中成長壯大起來的。”正如曾任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的沃爾科戈諾夫所說:“在1937年《布爾什維克》雜志第9期上斯大林發表了《給聯共(布)歷史教科書編者們的信》。斯大林寫道,《黨史》要把重點放在黨同各種派別和集團、同各種反布爾什維主義傾向的斗爭上。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這樣一來,黨史的中心必然是斯大林,因為正是他——斯大林‘擊敗’了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他們領導的集團和‘傾向’。用這種簡單的方法,即首先通過同‘反對派’的斗爭來描寫黨的歷史,當然占首要地位的就是斗爭的勝利者——斯大林。”這種突出領袖的黨史敘述模式恰好適應了當時中共的政治需要。在毛澤東指導和親自修改下,任弼時、胡喬木等人以《聯共(布)黨史》《結論草案》等文件為藍本,編寫出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歷史決議》的敘述模式也是以黨內路線斗爭為主線,突出毛澤東及其代表的正確路線。《歷史決議》在開篇便指出:“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隨后在決議所述的每個歷史時期內,毛澤東的名字都作為正確路線的代表被提及,并在最后的結論中寫道:“二十四年來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了,并且還在證明著,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我們黨和全國廣大人民的奮斗方向是完全正確的。……而且黨正是在克服這些錯誤的斗爭過程中而更加堅強起來,到了今天,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結果,必將給黨和中國革命帶來偉大的進步和不可戰勝的力量。”此外,決議中還多次引用了毛澤東的個人著述,這也與《聯共(布)黨史》頻繁引用斯大林的著述異曲同工。
歷史和實踐證明,這種歷史敘述模式雖然存在著一定的弊端,但在特殊時期是有其必要性的。正如胡喬木所說:“《決議》在黨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這個《決議》也不是沒有缺陷的。一是對毛主席過分突出,雖然以他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處提到劉少奇,稱贊他在白區的工作。在《決議》中,其他根據地、其他部分的紅軍也很少提到。”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決議把許多好事掛在我的賬上,我不反對,但這并不否認我有缺點錯誤,只是因為考慮到黨的利益才沒有寫在上面,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這說明,《歷史決議》按照這樣的敘事模式書寫是有其現實原因的,在革命戰爭年代有著其必要性和獨特的優勢。從事實上看,《歷史決議》對樹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不僅有助于戰爭年代中共內部的團結,也有助于中共取得全國革命的勝利。
《聯共(布)黨史》還在撰寫黨史的目的上深深影響著《歷史決議》。《聯共(布)黨史》在導言中就點明了撰寫黨史的目的,研究聯共(布)歷史,“就是用我國工農為社會主義斗爭的經驗豐富自己”,“有助于掌握布爾什維主義,能提高政治警惕性”,“就是用社會發展和政治斗爭規律的知識武裝自己,用革命動力的知識武裝自己”,“就能增強信心,確信列寧斯大林黨的偉大事業必將最后勝利,確信共產主義必將在全世界勝利”。由此可見,斯大林組織編撰《聯共(布)黨史》有著豐富黨員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知識,了解斗爭的經驗以推動黨的偉大事業和共產主義的勝利的目的。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講話時,明確提出了中共進行黨史研究的目的:“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們要用這樣的研究來使我們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進步。”這表明了毛澤東推進中共進行黨史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弄清歷史問題以促進當時工作的發展。這個目的也體現在《歷史決議》的編撰過程中,毛澤東將《歷史決議》的討論從黨的七大改為六屆七中全會,便是出于這個目的。胡喬木回憶:“1945年3月31日六屆七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將《歷史決議》交七中全會作結論,毛主席在這次全會上講了產生這個想法的緣由。他說:要使大會代表們有這種自覺,就是歷史問題應由七中全會作結論,以便大會只集中注意力于當前全國的政治問題。精神是弄清歷史,團結全黨抗日建國。不采用大會的武器來算舊賬,才能集中注意力于當前問題。”這也說明了中共編撰《歷史決議》的目的就是解決歷史問題,以團結一致向前看。

共產國際因素對《歷史決議》個別內容定性的影響
《歷史決議》的編撰過程,從1941年毛澤東寫《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算起,到1945年已有近4年時間。在此過程中,毛澤東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及定性發生了變化,這與此期間共產國際因素的影響不無關系。
毛澤東在《結論草案》中將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的歷史分為三個時期,并為這三個時期作了路線結論,即“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詳細材料經過詳細討論之后,一致認為四中全會及其以后一個時期,中央領導路線雖有缺點、錯誤,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九一八事變至遵義會議這一時期內,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遵義會議及其以后,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在這個草案中,毛澤東將六屆四中全會與隨后的錯誤路線分開,并沒有否認這次全會,并指出:“四中全會的成功方面在于,指出立三時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打擊了羅章龍為首的反黨右派,恢復了共產國際在中國黨內的信任,克服了‘立三路線’反國際的性質。”在講述四中全會的錯誤時,毛澤東認為:“四中全會全靠共產國際,只克服了當作政治形態(其主要部分)的‘立三路線’,不能克服當作思想形態的‘立三路線’,這是后來形成新的‘立三路線’的最主要原因。他們強迫推行共產國際東方部制定的極左的土地政策,大反其所謂‘富農路線’,造成了在經濟上消滅富農,在肉體上消滅地主,影響中農利益的嚴重局面。”《結論草案》認為四中全會恢復了共產國際在中共黨內的信任,而在指出六屆四中全會中共產國際的錯誤時,也僅僅將矛頭指向共產國際東方部。而此時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早已被處決,這樣措辭可以避開對共產國際的直接指責。這說明在《結論草案》出臺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還很大,中共無法對其錯誤進行指責,在給歷史問題定性時仍受外部因素影響。而在《歷史決議》中,中共明確指出六屆四中全會的路線是錯誤的。其中說:“這次會議的召開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其結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使它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勝利,而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路線對黨的第三次統治。”毛澤東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路線從基本肯定到否定,其中有著多重因素,而共產國際解散后對中共束縛的減弱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在對《歷史決議》草案進行說明時說:“內容上的其他問題:四中全會是否根本錯了?現在弄清楚了,四中全會在根本上是錯誤的。共產國際的問題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產國際現在不存在了,我們也不把責任推給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總的來說是功大過小,猶如玉皇大帝經常下雨,偶爾不下雨還是功大過小。沒有共產國際的成立和幫助,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不能有今天的。他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他們。”在這段話中,毛澤東不僅明確指出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根本上是錯誤的,也提及了改變這個問題定性中的共產國際因素。從中可以看出,即便共產國際已經解散,其對中國革命仍有著一定的影響力,這從對王明問題的定性中也可以看出。
在對王明錯誤定性時,季米特洛夫所代表的共產國際意見也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6月25日,毛澤東就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的錯誤路線給季米特洛夫發電報稱:“在將來的七大上,我們考慮不選舉王明為中共中央委員,因為他依然堅持老的錯誤,至今未放棄分裂主義活動。此外,有理由認為,他將同國民黨進行交易。”毛澤東在此電文中認為王明將與國民黨進行交易,這將王明問題定性為黨外問題。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給毛澤東發電報,稱:“關于政治性問題。不言而喻,共產國際解散之后,其原有領導人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是我個人不能不友好地說出中國共產黨內的情況使我感到的不安。……我認為,開展反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指責他們推行共產國際建議的民族戰線政策,似乎他們正在把黨推向分裂,這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不應當使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孤立于黨,而應當維護他們并盡一切辦法為黨的事業而使用他們。使我感到擔憂的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在黨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對蘇聯懷有不健康的情緒。”季米特洛夫在這封回電中,表達了自己對王明問題的看法,認為應該保持團結,同時向毛澤東表達了對中共黨內反共產國際情緒的不滿。1944年1月2日,毛澤東給季米特洛夫回電,稱:“王明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反黨活動。這一切都已通報給黨的全體干部。……我請您相信并能保證,斯大林同志和蘇聯在中國共產黨內是受到愛戴和高度尊敬的……我的看法是,王明是個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幾個人說他在獄中承認了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之后被釋放。還有人說他同米夫有可疑的聯系。王明進行了大量的反黨活動。”1月7日,毛澤東再次回電季米特洛夫:“除我1月2日電報所陳觀點之外,現擬再就這些問題陳述如下:我衷心地謝謝您給我的指示。我一定深入研究這些指示,注意它們,并根據指示采取措施。……關于黨內問題,這方面的政策是致力于聯合一致,鞏固團結。在同王明的關系上正是執行這樣的政策。由于1943年下半年所作工作的結果,黨內的形勢、黨的團結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請您放心。就您的想法,您的內心感受而言,我們是心心相通的,因為我的想法和感受和您基本是一致的。”從上述電文內容可以看出,毛澤東在首次回電中就中共黨內不存在反蘇情緒作了說明,但仍然認為王明進行了反黨活動,其問題是黨外問題,對這一問題并未妥協。而短短幾天后的第二封回電不僅措辭溫和了許多,也沒有再提及王明的反黨問題,并強調自己與季米特洛夫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從毛澤東立場的變化可以看出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對中共仍然有著一定的約束力,季米特洛夫在回電中也特別強調了毛澤東第二封回電使他感到高興。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毛澤東立場變化的原因。
194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黨的歷史問題,認為:王明、博古的問題應視為黨內問題;臨時中央與五中全會因有共產國際承認,應承認是合法的,但必須指出合法手續不完備。3月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了書記處會議精神,確定王明、博古是黨內問題,并且指出五中全會經過共產國際批準,根據這一點,是合法的。但應指出,其法律手續不完備。至于四中全會,經過共產國際與中央的承認,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路線內容是不好的。1944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召開,全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于黨內歷史問題的6項意見,主要內容便是上述會議的成果,但在表述上沒有點出王明、博古的名字。其大意是:1.中央某些個別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懷疑為有黨外問題,根據所有材料研究,認為他們不是黨外問題,而是黨內錯誤問題。2.四中全會后1931年的上海臨時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會是合法的,因為當時得到共產國際的批準,但選舉手續不完備,應作歷史的教訓……4.自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黨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但尚有其正確的部分,應該進行適當的分析,不要否認一切。
這說明在季米特洛夫來電后,毛澤東將王明問題定性為黨內問題,同時在指出六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的路線完全錯誤時,也強調其有共產國際的批準所以是合法的。這表明共產國際雖然已經解散,但其背后的蘇聯仍對中共事務有著較大的影響力。考慮到對蘇關系與中國革命事業,中共在書寫《歷史決議》時無法將其意見置之不理。
新中國成立后中蘇關系因素對《歷史決議》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所作修改的影響
經歷多次修改,《歷史決議》于1945年8月9日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一致通過。早在4月20日,《歷史決議》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原則性通過時,毛澤東便說:“決議現在還有缺點,還需要修改,故今天只要求基本通過。我想它的基本思想是不錯的。至于整個歷史敘述是否完全正確,那是不一定的。如果二三十年后看來,還是功大過小,就很好了。”這表明毛澤東深知《歷史決議》仍需要繼續完善。
新中國成立后,《歷史決議》在編入《毛澤東選集》的過程中又進行了一定的修改,而修改的原因中,蘇聯因素占據很大比重。
此次修改中,最顯著的地方是刪去“毛澤東思想”這一表述。胡喬木回憶:“凡有‘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體系’用語的地方一律刪去,有些就是毛主席在審定過程中親筆刪改的。如在第一節講黨在奮斗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之后,刪去了原有的‘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毛澤東思想體系’一語;也有將‘毛澤東思想’刪后改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的。這樣,發表稿通篇就沒有‘毛澤東思想’的字樣。”如《歷史決議》的第七部分,有四處“毛澤東思想”,第一處改為“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第二處直接刪除“思想”二字,第三處改為“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第四處則直接刪除,將“在毛澤東思想與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改為“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正確領導下”。
首先,產生上述修改的原因與蘇聯密切相關。胡喬木回憶:“這與蘇聯共產黨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不感興趣有關。《歷史決議》提毛澤東思想就有對著蘇共的意思。……因為共產國際盡管解散了,它的影子還存在,它對中國黨的影響始終沒有斷。但是,在我們黨提出毛澤東思想后,蘇聯黨始終拒絕承認這個提法。在蘇聯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這成了一個禁區。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發表時都給刪掉。既然蘇共是如此態度,而中國革命又離不開蘇聯的幫助,從大局出發還必須搞好與蘇共的團結,出于這樣的考慮,不僅《歷史決議》將毛澤東思想提法刪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
其次,《歷史決議》在修改中著重突出了中國革命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之下的,有意淡化中國革命指導思想的特殊性。“《決議》在指導思想的闡述方面,修改時有些地方直接將‘毛澤東思想’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些地方則插入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表述。比如在第二部分的結尾,將‘在思想一致的基礎上’,改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同時,這次修改中還突出了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和其論著的引用。胡喬木回憶:“原來一些地方沒有提斯大林名字的,都添上了‘斯大林同志’,有幾處還增加了他的引語。這個修改是陳伯達提議的,毛主席贊同了。”對于上述修改的原因,從毛澤東的一段話中可以看出:“為什么當時我請斯大林派一個學者來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樣沒有信心,連文章都要請你們來看?沒有事情干嗎?不是的,是請你們來中國看看,中國是真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這說明中共修改《歷史決議》的目的之一是向蘇聯證明自己所遵循的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二戰后蘇聯的外交政策以維護雅爾塔體系為核心,蘇南沖突時,蘇聯便指責南斯拉夫忽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忽視蘇聯作為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決定性力量。這體現了蘇聯非常在意自身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和對馬列主義的解釋權。而此時的中國百廢待興,在許多方面都離不開蘇聯的援助,所以維護好中蘇關系是非常必要的。在斯大林并不完全信任中共的前提下,中共對《歷史決議》作出上述修改也是在意料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