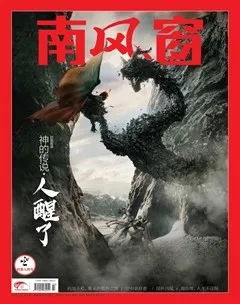愛情難以承受救命之恩
我們似乎很久沒有聽過這樣的故事了:男友失蹤后,女友想盡辦法擴散信息,最終竟成功打通了一條求生之路。演員王星成功獲救后,其女友嘉嘉在采訪里坦言自己當時的想法:“我和星星在一起3年了。對我來說,救他出來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我在事發后從未在這件事上猶豫過。……在需要彼此的時刻,我們兩人幾乎也都未缺席過。”而成功獲救的王星,也在字里行間充滿了對女友的感激、尊重與欣賞。
即便是懷著最熟練的警惕,也無法不被二人之間這份樸素直接的愛意所打動。繼而想到今天常見的一種調侃——你這么愛TA,TA是救過你的命嗎?言下之意,愛情應寄托在一些真正為我所利的東西上,比如救命之恩、經濟利益。對嘉嘉和王星來說,救命之恩也許的確成立了。可他們二人應該都不愿這么去定義它,更不愿將它用于兩人感情發展的衡量標準。
愛情是承受不了救命之恩這般隆重的。它理應只承擔一些輕巧的、不足撼動人生的感動,比如愿意為彼此改變一項細微的生活習慣、記住彼此的口味和愛好、悉心照料對方的寵物。愛是在自我完整的基礎上去延展生命,救贖從來不是它的任務。
過去十年來,愛情在時代價值排序里的地位大大下降。社交媒體上,勸人分手的“逆耳忠言”比比皆是。不肯為自己花錢,分;送禮不對等,分;父母不同意,分。分手就像換掉一件衣服一樣簡單,一顆紐扣掉了、一小塊污漬出現,或僅僅是不適合今天的天氣,都應當毫不猶豫換掉它。
聊天記錄里,說更多字的一方輸了。琢磨對方話語含義的一方輸了。愛情成了一場博弈,主導它的關鍵因素,是“等價性”。因此,在年輕人扎堆的社交媒體,依然有不少因彩禮談不攏而分手的泣訴。
那種愁苦的感慨,仿佛這并不是自主的選擇,而是被外界一雙不可抵擋的大手干擾和命令。愛情回到了封建模式,開始的動因啟自內心,結束的理由卻可歸結于千萬外部的條條框框。
“重利輕別離”重新成為常見場景,而我們很容易歸咎于某些大環境。就業、買房、育兒,幾乎所有人生大事的難度都比父輩更上一層樓。自顧不暇的年輕人缺乏安全感,在感情里也應當重防御大于付出。
本尼迪克特飾演的現代版福爾摩斯,在電視劇里有這樣一句臺詞:“我一直認為愛是危險的不利因素”。他識破了愛慕他的女人感情用事的伎倆,這是一種智識上的勝利,但并不是作為人的勝利。
文藝作品多把天才塑造成殘缺的人,他們的頭腦是數字和邏輯搭建的完密結構,難有孔隙滲透感情。藝術的魅力,很多時候就在于打破這種完密性。愛情的魅力,與之相似。
可荒誕的是,如果“救命之恩”的分量愛情里不該存在,卻是在現實中的確發生了,人們又短暫地再次相信了愛情。
一切都是為了更安全、更體面。有感而發是危險的,有話直說是愚蠢的。就像進入社會三五年后,你會自動在微信聊天里剔除表情包、感嘆號和波浪號。明面上,是怕顯得自己學生氣、不專業,但內心深處都知道,袒露感情和情緒似乎會讓自己顯得低位,就像對一個人暴露內心,則容易被TA所傷。
為避免陷入險境,為避免顯得愚蠢,我們將自己獨一無二的真實感受關進圍欄,看著欄桿外人潮涌動,仿佛自己正搭著時代的快車前進。前方的路通往哪里,無人知曉,但被遺落在身后的是什么,只有我們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