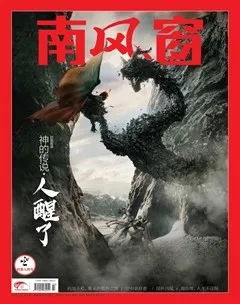蘇州,越來越強

“我覺得我們來錯地方了……不太確定蘇州是不是真的(新)一線城市。”
去年10月,一對來自愛爾蘭的旅行博主“瘋狂探險家”(TwoMadExplorers)發布了一條名為“我們第一次來到蘇州”的視頻,引發廣泛熱議。
視頻中,這對夫婦從杭州乘坐高鐵抵達蘇州。他們期待看到一座高樓林立、車水馬龍的現代化都市,但蘇州旅店外古樸的建筑群卻讓博主有些困惑。“這里沒有超級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實際上在很多方面看起來很舊……這真的是(新)一線城市嗎?”
或許他們的疑問正是許多人對蘇州的第一印象——典雅的園林,幽靜的街巷,處處透著江南水鄉的韻味與歷史積淀。這里似乎更多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而非經濟繁榮的現代都市。但這種初印象既真實又片面。
倘若將視線從古城移開,走向金雞湖畔,畫風則截然不同。這里,矗立著酷似“巨型褲衩”的東方之門,總高278米,它是蘇州現代化的象征之一。與“東方之門”僅一湖之隔,是有“鯉魚尾”之稱的蘇州國際金融中心。一東一西、一“魚”一“門”,當地人戲稱這是“鯉魚躍龍門”。
事實的確如此,過去30年里,在蘇州工業園區這片土地上,發生了太多“鯉魚躍龍門”的故事。周邊的高科技園區、國際化社區和繁忙的商務中心共同勾勒出這座城市的另一面——工業奇跡的代名詞。
目前,蘇州已有經營主體280萬戶。2024年新增206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10家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同時,還有多家企業入圍2024年《財富》世界500強。全市營收超百億元工業企業(集團)達47家,占全省23.5%,數量位居全省第一。
但神奇的是,這座引領制造業前沿的城市,既不是省會,也不是計劃單列市,更不是直轄市,只是普通地級市,卻創造了一次次的經濟奇跡。
“中國最強地級市”——蘇州,到底是如何養成的?憑什么能成為中國制造業的標桿?
制造之都
蘇州的工業實力獨樹一幟。
作為第一梯隊的領跑者,2022年,深圳、上海、蘇州率先躋身萬億工業GDP俱樂部。2023年,蘇州GDP接近2.5萬億元,穩居全國第六;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超4.4萬億元,僅次于深圳,位列全國第二。
2024年,蘇州依然追趕深圳。1月至11月,深圳規上工業總產值為4.75萬億元,而蘇州同期為4.26萬億元,全年預計逼近4.7萬億元。
作為下轄4個縣級市、6個區的小城市群,蘇州以全國0.09%的國土面積和1%的人口,創造了2%的經濟總量、3%的工業增加值、4%的實際使用外資和6%的進出口總額。
2023年,蘇州一二三產業增加值結構分別為0.8∶46.8∶52.4,二三產業占比平分秋色,放在全國都極為罕見。
這從側面說明,蘇州第二產業在保持較高占比的同時,已經跳脫了傳統模式,向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邁進,使工業經濟地位保持穩固,并能與服務業一同促進經濟增長。
然而,如何進一步破局?蘇州工業化的下一步,打造全球領先的“智造之城”。
今年1月3日,蘇州召開“新年第一會”,將“新型工業化”作為主題。這是蘇州連續第二年將這一主題作為開年最重要的議題。
蘇州以全國0.09%的國土面積和1%的人口,創造了2%的經濟總量、3%的工業增加值、4%的實際使用外資和6%的進出口總額。
會上發布的《蘇州市推進新型工業化2025年行動方案》明確提出,到2026年,蘇州將打造4個萬億級產業、培育15個超千億級產業,規上工業總產值突破5萬億元的目標;到2025年,規上工業產值將達到4.8萬億元,工業投資總額增速保持在10%以上,繼續鞏固工業強市的優勢地位。
為實現這一藍圖,蘇州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包括《關于支持制造業企業擴大有效投入的若干政策》《關于加快推動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10項政策文件及清單。
“擴投十條”設定了清晰的目標:計劃短期內每年推動1000家企業設備更新、實施1000個投資超1000萬元的增資擴產項目;到2027年,完成設備投資1100億元,技改投資1300億元,并改造3萬畝低效工業用地,以高效整合資源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一批重大產業項目也在會上簽約、投產,其中簽約億元以上項目220個,總投資998億元;投產(啟用)億元以上產業項目166個,總投資796億元。
制造業作為實體經濟的基礎,對于城市和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和互聯網這種不斷掀起造富神話的行業比起來,制造業留給大眾的印象總是有些笨拙甚至乏味,但國際經貿環境復雜多變的背景下,制造業不僅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還保證了產業鏈的穩定和安全,推進制造業的可持續發展顯得尤為重要。
“企業有困難的時候,政府總是無處不在的。現在不少產業都遇到了寒冬期,蘇州這些政策就是在給企業雪中送炭。”一位參會人員告訴南風窗。
一批批企業在蘇州的幫助下成長壯大,也讓“制造業之都”的金字招牌更加閃亮。
“招商引資要看長遠”
蘇州工業園區,位于蘇州城東,總面積278平方公里,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構建了成熟的產業發展格局。協鑫集團作為較晚入駐園區的民營企業之一,2016年陸續在此設立了總部和旗下4家上市公司,資產規模近2000億元。
協鑫選擇蘇州并非偶然。最初,公司總部設在上海,但由于辦公成本高企和發展空間受限,集團決定將目光轉向蘇州。“蘇州是長三角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綜合考慮經濟指數、招商指數和創業指數等因素后,最終決定把總部搬到這里。”協鑫控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員王營表示。
協鑫入駐后,立刻感受到蘇州效率帶來的驚喜。不到半年,總部就在園區順利建成。甚至在辦公樓還未完工的時候,園區就早早做好了道路規劃,在公司各個方向設立指示牌,連地鐵都已經通到了門口。
入駐后,協鑫不僅為園區企業和居民提供穩定、清潔的熱力和電力,還投資建設了多座新型儲能電站,“園區每用10度電,有7度都是協鑫貢獻的”。然而,協鑫的主要光伏產業鏈布局在全國其他地區,大部分經濟和稅收收益并未完全體現在蘇州。
“最初我們就像一只不下蛋的老母雞。”王營坦言,但園區不僅給協鑫提供了優質的公共資源,還為近千名員工提供了價格極低的人才公寓。
因為對政府而言,他們并不計較眼前的經濟收入,而是更看重企業的長遠發展。
事實證明,這份包容和耐心很快得到了回報。
2024年,協鑫在蘇州國際科創大會上宣布,與蘇州市、昆山市和吳江區政府共同發起設立總規模100億元的鈣鈦礦產業基金及30億元的裝備產業基金,并簽署了多個重大項目協議,包括昆山20GW鈣鈦礦光伏組件生產項目和吳江鈣鈦礦裝備產業園的建設。預計到2027年,這些項目將帶來千億級產值。
鈣鈦礦被譽為光伏行業的未來,其技術的顛覆性在于更高的轉換效率和更低的度電成本。協鑫通過自主創新,將鈣鈦礦與晶硅疊層組合,不僅大幅提升了光電轉換效率至34.6%,還將組件成本降至晶硅產品的70%,這是光伏領域的革命性突破。
協鑫計劃在年初正式投產全球首條GW級鈣鈦礦生產線,生產規格為2.4米×1.2米的組件,這將是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功率最高的鈣鈦礦產品。項目建成后,企業能為蘇州帶來稅收、就業和綠色發展的動力。更重要的是,這一系列布局還將助力蘇州打造國內領先、國際一流的新能源產業集群。
蘇州的做法也給其他城市傳遞了一個信號:招商引資不能只盯眼前數字,更要看長遠。給企業空間,給產業動能,是投向未來的智慧,也是城市繁榮的底氣。這樣的耐心和格局,讓蘇州在總部經濟中脫穎而出。
細節決定成敗
總部經濟,是蘇州近年來大力推動經濟轉型的重點之一,也是各地爭相爭奪的“香餑餑”。
蘇州的做法也給其他城市傳遞了一個信號:招商引資不能只盯眼前數字,更要看長遠。
原因很簡單,總部企業通常是大型公司,即使主營業務不在本地,它們的落戶依然能帶來豐厚的稅收、穩定的就業機會,以及上下游產業鏈的全面帶動。同時,吸引高端人才,也能讓城市的產業生態和競爭力顯著提升。可以說,總部經濟的價值遠超單純的經濟數據。
正因如此,各地對總部企業的爭奪格外激烈,各種獎勵和扶持政策層出不窮。協鑫集團就曾接到四川、深圳等地的邀請,條件一個比一個優厚。
但對于總部企業來說,他們更看重一個城市的產業配套、人才儲備、綜合成本和營商環境等因素。在這些方面,蘇州具有強大的綜合優勢。作為一個非省會、非計劃單列市,蘇州在資源和政策上的先天條件并不突出,但這也讓優化營商環境成為蘇州的“生命線”。
昆山流傳一個段子,“市長要敢于給外商端洗腳水”。早在1994年中國與新加坡合作開發蘇州工業園區時,這種開放、包容的基因就已深埋其中。當時,蘇州借鑒新加坡經驗,與其合作打造的工業園區,成為了全國開放的典范。
蘇州也憑借這些積累和沉淀,在對外開放中引了進一批高質量制造業外企,主要集中在裝備制造、電子信息等行業,如三星、松下、西門子等。如今,全市外企已經超過兩萬家。
同時,全市還擁有607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省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超3500家,數量全國領先。到2025年,蘇州計劃再新增200家國家級“小巨人”企業。這樣的成績背后,是政府精準、高效、細致的服務。
衡量一個地方的營商環境,不能只看它怎么說,更要看行動,細節騙不了人。
舉個例子,在招商引資白熱化的今天,許多城市出臺的涉企政策繁瑣復雜,企業看了猶如“天書”。而在蘇州,今年的“新年第一會”發給企業家的不是厚重文件,而是一張“政策明白卡”,掃碼即可查閱最新政策清單和申報入口,幾步操作便能完成申請,省去了繁瑣流程。
同日,蘇州還揭牌了企業綜合服務中心,通過“線下一中心、線上一平臺”的閉環服務體系,為企業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支持。
“以前是政府給什么,企業接什么;現在是企業需要什么,政府主動提供服務。”蘇州數據局副局長周旭東介紹,政府正通過“線下一中心、線上一平臺”的模式和閉環管理機制,構建覆蓋全市的“1+10+N”綜合服務體系,為企業提供貼心、優質的“蘇式服務”。
具體到日常辦事體驗,蘇州干部的作風也讓人印象深刻。
“每次政府這邊有什么優惠政策,或者能給企業申報的項目,都會直接派人通知,手把手教我們怎么申請、怎么填表格。”會后一位蘇州企業家告訴記者,在蘇州開公司,是件很省心的事。
挑戰與未來
在協鑫總部的展館里,排列著光伏技術的迭代產品,從傳統的棒狀硅到突破性的顆粒硅,再到前沿的鈣鈦礦材料,展現了協鑫在光伏領域的技術革新。尤其是鈣鈦礦,生產成本更低,能耗僅為晶硅電池的1/10,這項技術也成為協鑫未來在光伏行業中的核心競爭力。
即便如此,協鑫也不敢“躺平”。近年來,隨著光伏市場的迅速擴張,行業內的同質化競爭日益加劇,供需逆轉,產能過剩、低價競爭、停產裁員等問題成為常態。在新玩家不斷涌入的背景下,企業若想不被擠下牌桌,必須掌握核心競爭力,“上桌”的資本尤為重要。
“卷”,成了協鑫的關鍵詞。
“其他企業1公斤棒狀硅大約需要耗電65度,制造成本55元;而我們的顆粒硅耗電僅13度,成本不到30元。他們想打價格戰,也拼不過我們。”王營介紹,協鑫算是整個光伏行業里的“卷王”,這種“卷”不是簡單的價格內卷,而是靠科技創新、人才提升、工藝優化以及綠色減排贏得市場主動權。

這種“卷”的精神,融入了蘇州的每一處細節,也成為江蘇崛起的縮影。江蘇在中國綜合競爭力百強縣市排名中實現“全員上榜”,所有地級市GDP均突破4000億元。蘇州的昆山、張家港、常熟、太倉集體位列全國百強縣市前十,昆山更是連續20年穩居榜首。
這種內部競爭轉化為全市的協同發展。“蘇州的農村富裕程度甚至超過很多城市,這里幾乎沒有窮地方。”一位在蘇州生活多年的市民感慨道。
一位蘇州企業家告訴記者,在蘇州開公司,是件很省心的事。
然而,作為地級市,蘇州也需要克服很多難關。機場和大學,一直是蘇州發展的痛點。
作為江蘇省的經濟龍頭,人口超千萬的大城市,蘇州至今沒有自己的機場。盡管有上海、無錫、揚州、常州等周邊城市機場的環繞,但“環蘇州機場城市群”的尷尬讓蘇州更渴望擁有一座自己的運輸機場。
此外,蘇州在高端人才吸引力和教育資源上也存在劣勢。全市雖有25所高校,卻僅有一所211大學——蘇州大學,以及幾所985大學的分校。蘇州的高校資源和經濟總量相比,顯然并不匹配。
蘇州在某些專精特新領域的確有優勢,但與上海這樣的國際大都市相比,綜合吸引力仍顯不足。王營透露,許多企業員工寧愿每天通勤,也要在上海定居。從中足以看出,蘇州的聚才能力還有較大提升空間。
盡管如此,這座城市并未停下腳步。從制造業到智能化,從傳統模式到全球創新,這座城市始終在尋找新的突破口。
當夜幕降臨,路燈與星光交相輝映,遠方工廠的燈光閃爍,照亮前行的路。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營為化名)
責任編輯趙靖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