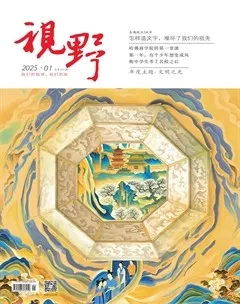漢字信息化的百年突圍史

中文打字機:大文豪的小發明
讓我們回到19世紀中后期,彼時的西方正大規模地生產著新式打字機,將他們僅有的二十多個字母塞進方塊大小的鍵盤里。
沒有人會想到,這一看似“不起眼”的小發明將會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一場文字信息化的革命。
當這項偉大的技術傳入中國后,卻在20世紀初引發了一場關于漢字的激烈爭論。
漢字的復雜性使得我們無法用有限的符號將其標示在鍵盤里,因此,漢字將面臨無法被信息化、數字化的窘境。
于是,新文化運動中一批致力于救亡圖存的激進知識分子便站出來高呼“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彼時任教于清華大學的林語堂正思考著如何在保留漢字的情況下,發明一臺中文打字機,這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創造中文打字機的嘗試始于1899年,美國傳教士謝衛樓發明了首臺中文打字機。然而,繁重的機器和流程,有限的字庫與字數大大制約了打字的效率。
1919年,商務印書館的工程師舒振東發明了舒氏打字機,把字模分成了常用字和生僻字兩部分。一般情況下用常用字模來打字,有需要時再補充生僻字模。盡管這種方式大大提高了打字的效率,但還是存在著較高的學習門檻。
兩次不太成功的嘗試并沒有嚇退林語堂,他一邊學習著機械制造原理,一邊親自動手繪制設計草圖。
林語堂終于在1931年完成了中文打字機的設計草稿。然而,此刻擺在他面前的是另一道難題。
金錢成了他最大的障礙,為了制造這臺打字機,他一邊變賣家產,四處借錢,一邊靠作品賺取稿費,期間還寫出了代表作《吾國與吾民》《京華煙云》。
1947年,由林語堂親手設計的“明快打字機”終于問世,這款打字機的尺寸接近于當時流行的打字機,并且采用了一套“上下形檢字法”系統,大大降低了操作門檻。
只可惜,這臺耗費林語堂三十多年心血的打字機最終還是失敗了。當時正值中國內戰時期,沒有廠商愿意大批量地生產這款打字機,第一臺原型機也在不久后丟失了。
盡管如此,林語堂的設計理念卻傳承了下來。1983年,王永明發明了五筆輸入法,在某些方面與明快打字機所采用的上下形檢字法是一脈相承的。
作為現代文學的大家,林語堂因其創作的優秀文學作品和兩次被諾獎提名的經歷而著稱。但我們不能忘記的是,正是這臺在當時人們眼中微不足道的明快打字機,為漢字開辟了信息化和國際化的道路。
漢語拼音方案:“語同音”的時代
用拼音識讀文字、查閱字典、輸入文字……如今漢語拼音方案已經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我們常常會忽視它并非古已有之,是建國后漢語現代化的產物。
漢字是世界上少有的意音文字,這曾是我們引以為傲的一個特點,但也帶來了一個問題:很多時候我們無法直接從一個字的字形看出它的讀音,因此正確地識讀漢字需要注音方法的輔助。
在漢語拼音方案被發明以前,我們曾經用過的注音方法就有直音法、反切法、注音符號法等。但直音法要求學習者本身就掌握大量漢字的讀音,而反切法則易受各地方言的影響而出現注音不準的情況,注音符號又顯然無法適應時代的潮流。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央為了提高識字率,把制訂一套比較合理的注音方案作為重大工作,并在1955年設立了拼音方案委員會。
委員會提出了民族化與拉丁化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案,并由甲組擬訂漢字筆畫式方案,乙組擬訂國際通用字母拼音方案。
盡管內部仍然存在著分歧,但是委員會中的部分專家隱約意識到拉丁化的字母拼音方案很有可能是漢字與世界接軌的重要契機。
在周有光等人的努力下,委員會最終達成共識,敲定了以拉丁字母為語音形式的漢語拼音方案。方案一經公布,群眾提出的意見便如雪片一般飛來,反應熱烈,但多數人不同意使用新字母。
隨著計算機時代的到來,西方表音文字因為形式簡單能直接轉化為計算機信息,而漢字卻因復雜的字形結構而陷入難以信息化的窘境。
對于這樣的形勢,語言學家蘇培成曾說:“我們失去了一個打字機的時代,不能再失去一個電子計算機的時代。”
于是在眾多的輸入法中,一種以漢語拼音方案為基礎的輸入法——漢語拼音輸入法脫穎而出,解決了漢字無法被直接信息化的難題。
現在看來,我們應當要感激當年采用了拉丁字母的注音形式,使不表音的漢字能夠進入鍵盤,從而便捷地跨上信息化和國際化的快車道。
拼音方案委員會的委員有:吳玉章、胡愈之、韋愨、丁西林、林漢達、羅常培、陸志韋、黎錦熙、王力、倪海曙、葉籟士、周有光、胡喬木、呂叔湘、魏建功。
我們應該記住他們的名字,今天我們每一次拼寫漢字,每一次用漢語拼音輸入法敲擊鍵盤,都是他們智慧光芒的閃現。
漢字激光照排系統:告別鉛與火,邁入光與電
漢字激光照排系統就是把漢字以編碼形式儲存到計算機中,輸出時再用激光掃描成字。
60年代以后,西方已經開始研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統了,但國內仍處于鉛印的時代。
?1974年8月,原?四機部等五家機構聯合發起設立了?748工程,分為三個子項目:漢字通信、漢字情報檢索和漢字精密照排,旨在改變我國印刷行業的落后面貌,解決漢字的計算機信息處理問題。
當時任職于北京大學的助教王選正病休在家,對于這三個子項目,他唯獨鐘情于漢字精密照排。根據自己的大膽設想,王選直接提出了要研制西方尚未成功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技術。
然而,這樣一個石破天驚的方案得到的不是眾人的鼓勵和支持,而是一連串的懷疑與謾罵,甚至有人說他“玩弄騙人的數學游戲”,“夢想一步登天”。身邊人的不理解并沒有讓王選氣餒,真正難住他的是漢字的信息化儲存問題:西方文字僅二十幾個字母,而漢字不僅數量龐大,結構復雜,還有字號和字體的變化,想讓當時尚處于起步階段的計算機直接儲存漢字的海量信息無異于癡人說夢。
王選仔細琢磨漢字的結構規律,結合數學與計算機方面的知識,他想到了信息壓縮的方式,即用輪廓和參數相結合的方法描述字形。
這一辦法將每個漢字數字化后的信息量減少了幾千倍,極大地降低了計算機處理漢字信息的壓力。
1979年7月27日,中國科研人員首次用激光照排機輸出中文報紙版面,報頭是“漢字信息處理”六個字,標志著四代激光照排系統取得重大成果。
王選帶頭研發的漢字激光照排系統讓中國印刷行業僅用幾年便走完了西方幾十年的路,徹底改造了我國沿用上百年的鉛字印刷技術,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印刷時代。
這一成果與漢語拼音輸入法相輔相成,使計算機處理漢字信息,中國人在計算機上輸入漢字、處理漢字、調節字體字號成為可能,讓我們在手機上互發短信和郵件成為現實,也讓歷經幾千年歲月的漢字在信息時代煥發出新的生機。
(摘自微信公眾號“默讀Rea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