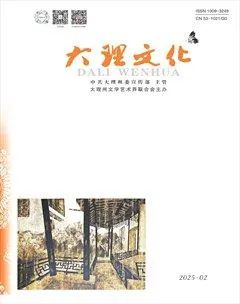白鷺(外八首)
那彈琴之人,當他被認出
音樂泄了一地
急促的事物一旦成立
勸誡是不明智的,你只能直面白鷺提交
你波光粼粼的傷口
像才耕作的水田:平整,慎重,嚴絲合縫
白鷺就在那里,一個象征性的比喻
瓷一樣容易打碎。但白鷺有自我的主張
獨立于你的聽力
像生根的果木,開白花,枝丫潔凈
茂盛。羽毛頭發一樣白,軟
無視你的挽留單獨老去
藤椅里,父親以此為漣漪的中心緩慢擴散
他曾長期困囿于此
此刻。再沒有聲響和形體,甚至
遠遠矮于你的幻覺
——記憶再也不能復原
天亮之前
蟬聲是暗紫的,河水
緩慢流過你的手指,需要擠出夜色的膽汁
而我的父母在深睡
隔壁房間安靜地遠離我,沉船一樣
一年中最溽熱
的時間,必須熬過去——
一種腐木的苦味,在發散
軋路機是突然響的,堅硬的地面
被撬動
翻卷帶著痛苦的回聲——可是幻聽?
又如此黑白分明
真切的流逝無法阻擋,死亡并非總默默無聲
有時,會蓋過其他聲音
鳥叫突然響起。天亮之前
只有它們
可以制造一種清涼的,島嶼般的愛情
南梆子
有沒有更明確的炫技?
那白鶴并非消失。如果它一直游弋

時間的歃血為盟就一直存在
聽戲的母親,就不會一直老下去
她會停在聲線的最高處
像枚黃金的柿子
也會一直抱穩收音匣子
一遍遍倒敘——
比如,在柿子樹上蕩秋千
或是陪她的伯伯喝杯苞谷酒。滾石
按拍,板鼓和琵琶
領受一種
敬仰般的使命,替一個姑娘
完成她夢里理想的一生
仿佛真的可以是穆桂英或花木蘭
事實上。母親極速衰老——
在生活里
在各種討生活的腔調里
唯有明月
恒久地,歡暢地唱著流水板
懸崖
窗口羈押了一枝黃花
而它的搖曳
又替自己羈押了一座懸崖
靠著香味這根繩子,它把自己
從虛擬中搭上來
而你也將它與別物區分
仿佛,它之所以蟄伏在黑暗的底部
只是為了被你尋出
也可能。它代表了一種草木的輕
類似,你站在窗口向深淵凝神——
那里有什么?
它異乎常態的香
像壓迫,像一種不可鉗制的阻擋使你心驚
但你已無法轉身
……黑暗中,它把自己托付給你
它喘著粗氣的香
仿佛走過很長的路。又仿佛只是時間的一瞬
而你也只是在懸崖站了一會兒
就耗盡了一生
魯冰花
她在緩慢地恢復香氣
所以我不敢很快地靠近
只在護欄外看她
她也平視我
河一樣,滾動的寂寞
有種集體性的穩固審美使我確信
她更適合隱藏在多數中間
——整齊劃一的布局
和冰涼的氣息。花田迷途一樣
我不得不讓視線拐彎
以適應她的曲折和幽深
尤其,當她屏住呼吸
用不在場驗算著我的分辨力
我實在沒辦法將她和他者區分
她們那么多
正午在她臉的正中央
當移到角落,我已經完全找不到她
只覺得她混沌一片
艷麗的顏色一點點剝落
筆直的腰身也卷曲
我只能跪下去
向叢林般的墓園深深拜別
并習慣性地喊:“媽媽”
蜻蜓
烏溪河邊。他的翅膀往下壓了壓
河水更深了像幻鏡
以回溯照徹他的中年。跌進老邁之前
他終于又回到這里
張力輕薄得隨時可以帶他飛
麥地寂靜,一種無法被轉述的愉悅
在他跑動時放大成童年的景象
無法區分現實和夢境
他用探針計數烏溪河的深淺和流速
也計數蘋果花的白銀庫存
甚至,他的復眼極速地復原著當年的場景
露水使他晶亮。空中
植物戀愛般的花粉具備綿長的捕捉之力
他的快活那么易得
就是用自制的捕捉神器
去捕捉一個個欲飛的久違的紅衣少年
夏枯草
沉入淵藪的人
也曾困于這草木的九重塔
淤青暗沉
枯萎的花序必須和半夏雜糅
或可逼出你內心的盜匪
夏枯草,當它被砍掉頭顱
置換于一次命運的轉折。你需要
穩固的血壓。或者
摘掉多余肝火
才能夠重獲復生的域名
但耽于她心有所屬
夏至后,也會極快地老去
空余一座悲傷的城池。因此
最好是把它連根拔起
杜絕她在更深的命里
理解一株多年生草本植物的宿命
立秋后
一種芬芳的危險緩慢靠近
江漢平原更加立體,果實們分出層次
長江可以被預約
這些甜蜜的儲藏罐——
進入“寫作才有的迷人錯覺”
菊花枝葉瘋長,賦形
她們取出體內音箱。有些,開始了譜曲
當我演奏,最早的音符露出端倪
立秋后。松弛逐層取代緊繃
老虎溫柔,石頭
加大了美妙的回聲。我聽見一陣“轟隆隆”的滾雷暗中傳來,緊跟著
閃電扯爛黑布匹
久違的雨點穿過裂縫,撲了過來
蟬蛻
它只是回到了開始
像當初,擠在黑暗的泥土里一樣
用一種不和解就丟棄的方式

空出自己
每次。當她奮力從硬殼里擠出去
都留一個被孤獨掏空的
脆殼給我。這本是她的原身子
但此刻空泛,透明
沒有細節和溫度。卻保留最后一刻
她奮力一蛻的姿勢
能看出,力在脫離她之后仍繼續困在了那里
類似琥珀。只是角度不對——
一個向內,另一個向外。因無法預判這力
能維持多久,在以慘烈著稱的重生面前
這小小的棺槨只能暫時寄宿于空茫
崩塌之前,像她一樣
牢牢地扎進樹干上,用想象的吸吮虛構著生
而活著的她,或許早被人捕捉了去
或許,只是個單純的影子
從醫學上說,它比她更滿足人類的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