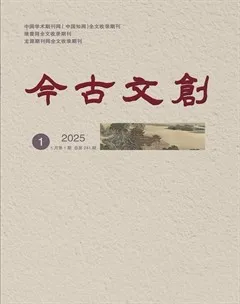《登記》中夫妻沖突被淡化的敘事策略及其效果
【摘要】趙樹理的小說《登記》中存在著被淡化的人物對立關系。在婚姻生活中,小飛蛾與張木匠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沖突,而趙樹理的小說敘事策略,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這種關系的進一步書寫。趙樹理的“問題小說”繼承了傳統清官文學的創作模式。在《登記》中,“清官”所斷的“冤案”,案由是婚姻是否自主的問題,而不是婚姻生活觀念的現代性轉變。同時,小飛蛾在文本中既是母親,亦是妻子,其妻子身份的被淡化,亦關聯了她與張木匠的對立關系被淡化。
【關鍵詞】趙樹理;《登記》;小飛蛾
在趙樹理的《登記》中,讀者可能對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以及老一輩人在婚姻中飽受封建思想觀念的壓抑和新一代人追求自主婚姻的艱難印象深刻。然而,通過文本細讀,《登記》的文本存在一個少有研究者聚焦的現象:作為舊社會婚姻觀念的受害者和自覺反思封建意識的覺醒者,小飛蛾與依舊受制于封建思想觀念的張木匠之間存在著對立關系。這在小說故事的發展中被淡化了。趙樹理對小飛蛾與張木匠之間矛盾沖突的淡化處理,使得小說留有一個闡釋空間:是什么在影響著趙樹理淡化處理了小飛蛾與張木匠的對立關系呢?
本文將圍繞《登記》中存在的人物間沖突關系被淡化的現象,試圖從趙樹理小說的敘事策略、“清官斷案”故事的案由選擇和前現代社會意識形態的回歸三個角度,探究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
一、權益保障優先的線性敘事
趙樹理的小說創作深受傳統白話小說的影響。中國白話小說源于民間的“說話”藝術,是為大眾歡迎的藝術形式。白話小說在文本中維持著一個“擬書場”格局,保留了一位客觀化的、富有情態的“說書人”,并以線性敘述作為小說主要的敘事策略。這種敘事模式預設了講故事的人與故事的接收人,使“說書人”既把握著敘事的主導權,又需依照說書場格局,時常照顧讀者對故事的接收,在敘事上講究故事的連貫順暢,使故事有頭有尾,讓讀者對故事的前因后果明白清晰。
通讀《登記》以后,可以發現小說延續了趙樹理順敘的敘事策略,雖然文中出現了展現小飛蛾過去婚姻生活的倒敘,但這種倒敘的進行總是以不破壞故事線性敘述的完整性為前提的,是為了保障“現在”的故事繼續推進下去而敘述的事件。本文提出趙樹理在《登記》中更加重視“現在”,并非認為其對小飛蛾與張木匠之間對立關系的淡化是對“過去”問題的不關注,而是試圖指出,趙樹理于文本中采取的敘事策略直接影響了兩者對立關系的繼續展開。
在《登記》中,“說書人”不斷發出聲音,提醒著讀者“過去”的事是為了確保故事的完整、清晰而必須交代的,對主線時空中發生事件的敘述與評價更為要緊。在敘述者發出的聲音里,“過去”中最成問題的不是婚姻生活內的問題——張木匠對小飛蛾的欺凌和對婚姻的背叛,而是傳達、聚焦婦女作為舊式婚姻受害者,長期受封建家長制壓迫的尊嚴受辱與身心創傷,以及個人權利的受侵害現象——自主婚姻的權益被破壞。正是趙樹理對主時空中婦女權益的重視,使得小飛蛾的故事沒有成為故事矛盾的集中點,她與張木匠的對立關系不是《登記》所想解決的問題,也便成為線性敘事中淡化乃至省略的一部分。
如果將《登記》中對倒敘故事的處理與“五四”新小說中的倒敘進行比較,也可以發現《登記》中倒敘故事所發揮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小飛蛾與張木匠之間的矛盾。相比起“五四”作家自覺學習西方作家將倒敘中的故事作為結構作品的一種藝術方式,趙樹理對倒敘手法的借鑒更多來自傳統白話小說,倒敘是對線性敘述的補充說明。對于“五四”作家而言,倒敘的故事可以成為具備獨特美學價值的整體。誠如陳平原所說:“‘五四’作家的真正貢獻在于,倒裝敘述不再著眼于故事,而是著眼于情緒。過去的故事之所以進入現在的故事,不在于故事自身的因果聯系,而在于人物的情緒與作家所要創造的氛圍——借助過去的故事與現在的故事之間的張力獲得某種特殊的美學效果。”在魯迅的《祝福》中,“現在”的事件相對單薄,而被倒敘的祥林嫂悲劇性人生遭遇成了“有頭有尾”的整體,正是“過去”的苦難與心靈困境為人物“現在”的悲劇性結局奠定了基礎。“過去”的時空起到了揭示封建禮教、舊道德對人的迫害的作用。在《登記》中,小飛蛾的故事更多的是為講好新一代人故事所必須敘述的一個部分,從屬于一個線性敘事,在響亮地揭示出新一代人面臨的核心問題——婚姻自主權問題之后,敘述者為避免打亂線性敘事,仍需回歸主線,小飛蛾與張木匠的矛盾便在這種敘事策略下淡化為艾艾偷聽兩人交談時的模糊的對話。
二、“清官”案由選擇影響下的問題聚焦點
趙樹理的“問題小說”中蘊含著“清官意識”。我們能夠較容易地體會到趙樹理作品與清官文學的互文性:趙樹理小說往往“重事輕人”,凸顯出為問題而寫作,為問題開藥方的創作意識。在內含“清官斷案”模式的《登記》中,“清官”所斷的案由,并不是小飛蛾與張木匠之間的“冤情”。由于隱含作者強烈的介入姿態——宣傳新婚姻法“婚姻自主”的思想觀念,《登記》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民的婚姻問題,呈現出其對關注側重點的選擇:“冤案”案由是婚姻是否自主的問題。
趙樹理的“問題小說”具有與傳統清官文學相似的內部結構框架。《登記》的故事結構可以被簡化為:艾艾和小晚等有情人追求婚姻自由——小飛蛾自我覺醒后不再阻礙有情人——守舊勢力阻撓——政策公布、區委書記幫助有情人——有情人登記結婚。在這一結構內,艾艾等年輕人是沖擊外部阻礙、渴望“請官”出面和尋求婚姻自主權的“鳴冤人”。可以發現,被敘述者引到堂前的是新一代渴望婚姻自主的年輕人,而不是小飛蛾與張木匠。小飛蛾在他們的斗爭中是重要的“證人”,她的經歷使讀者知道張家莊的婦女的冤情。
趙樹理的“問題小說”對婚姻是否應該以愛情為基礎的議題缺乏思考。黃修己曾在趙樹理與當代作家張弦的比較中指出過這一點:“如果不提倡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而單有婚姻自主,還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在婚姻中得到幸福。對于這一點,趙樹理似乎注意得不夠……他卻沒有認識到這是一個應該揭示的問題,沒有進一步挖下去。”
其次,作為趙樹理為響應政策宣傳的號召而創作的作品,《登記》始終側重維護青年婚姻自主權,使婚姻法的出臺成為促成故事大團圓的主因,將婚姻法作為破除新舊社會婚姻悲劇的出路。然而,趙樹理僅僅表現新“清官”的威嚴、描述出受新法的出臺而得到保障的新社會新人的婚姻生活的美好前景,仍可能造成一種遮蔽——婚姻生活的美滿幸福并不單單來自權益的保障,更與現代婚姻生活觀念的建構有關,而正是案由選擇的側重點不同,客觀上,使得小說的故事敘述沒有聚焦到兩人的對立關系上。亦使得小說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沒有繼續進行下去。這種觀念建構的缺失問題是客觀存在于文本之中的,具體來說,則表現為婚內個體間的人格平等與相互尊重。
夫妻在生活中相互關愛與尊重、共擔責任是婚姻和睦的重要支柱,而小飛蛾的人格尊嚴沒有得到過來自家人起碼的尊重,張木匠也沒有承擔起維持家庭的責任,突破婚姻的底線。張木匠在婚姻中是單方面地向小飛蛾索要關愛的人,在單向地索求小飛蛾的情感。對于他而言,丈夫向妻子尋求體貼的關愛是理所應得的。在熱暴力以外,張木匠也長期對她施予冷暴力:張木匠“一年半載不回家,路過家門口也不愿進去,聽說在外面找了好幾個相好的”。張木匠的這種行為很大程度上緣于其婚姻責任意識的缺失,他不會意識到,與人結為夫妻便意味著責任的肩負。夫妻間缺乏互愛互重,個體喪失責任意識,這些正是舊社會婚姻生活中長期存在的思想癥候。事實上,婚姻是否應以情感為基礎、婚姻生活觀念是否應變革,是與保障婚姻自主權這一現代性追求并軌的,后者不能單純地將前兩者包含于內,而前兩種問題已然客觀地顯現在《登記》的文本中,只是由于趙樹理為婚姻法這一新“清官”所確定的案由側重點不同,一定程度上致使小飛蛾與張木匠對立關系的淡化,使對這些關乎現代人婚姻生活方式的癥結的思考沒有進行下去。
三、響應前現代社會道德觀念呼喚的“母親”
趙樹理對農民立場的堅守,意味著趙樹理在創作中尊重農民對真善美的價值判斷,并以此為標準,展開敘事。這其中攜帶著前現代的意識形態,便使趙樹理的“問題小說”秉持另一種道德視角。正是在《登記》中隱含的這種傳統道德觀念的復歸,影響到了小飛蛾與張木匠對立關系的被淡化,以及對小飛蛾這一人物形象的完整塑造——母親與妻子兩重身份的整合。
小飛蛾一方面是具有樸素母性的母親。她真心愛護艾艾,唯恐她重蹈自己的悲劇。小飛蛾又是未被封建舊思想改造、能夠自我覺醒的母親。她真正意識到張家莊的婦女在舊婚姻禮俗下,始終重復著“人是苦蟲”的不幸,從而改變了包辦女兒婚姻的想法,支持她追尋真正的幸福。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小飛蛾也是一個尊嚴被踐踏、婚姻遭背叛,卻從未向暴力與歧視屈服的妻子。作為妻子,小飛蛾從未感受過家庭的溫暖。她忍受著丈夫毫不留情的家庭暴力,還要忍受丈夫每次在她回娘家時的緊緊跟隨、監視。正是在這種“愛護”下,張木匠延續著丈夫對妻子生活的掌控,捍衛著夫權權威。
然而,在《登記》中,真正等來大團圓結局的,不是作為長期對抗家庭暴力與封建意識的、作為妻子的小飛蛾,而是那個作為覺醒群體代表的、作為母親的小飛蛾。不妨借用托多羅夫的敘事平衡理論來探討《登記》的故事是如何達到一種平衡狀態的。宏觀地觀察《登記》之后,可以發現,小說中存在著兩個平衡結構,一是艾艾羅漢錢的失而復得這一平衡的達成;二是艾艾等年輕人在遭遇種種阻礙后,終于取得捍衛婚姻自主權的勝利,完成了新時代下的平衡。敘述者要完成的,是艾艾等人如何由“不準登記”的失衡狀態達到成功登記的平衡狀態。小飛蛾曾作為封建家長,是艾艾等人為尋求新平衡而要克服的封建障礙。覺悟后的小飛蛾將羅漢錢還給艾艾,既意味著年輕人跨越了一個阻礙,同時也意味著將作為封建婚姻受害者的母親納入沖破封建意識藩籬的集體中。在《登記》所達成的平衡狀態中,小飛蛾僅以母親身份被納入大團圓中,仍令小說言有未盡,對其妻子身份的淡化,則有另一道德視角的介入。
小飛蛾的母親身份的凸顯,以及其妻子身份的受忽視,與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露西·伊利格瑞的相關論斷相呼應。“成為母親”從屬于父系社會主流話語的預設。結婚后,小飛蛾作為妻子,成為張木匠隨意把持的“物”,既寄托著他對青春活力的欲念投射,又是能在舊式婚姻禮俗下,不斷被棍棒“馴化”的封建家長權威的附屬物。
小飛蛾對年輕人婚姻自主的支持,一方面體現著農民翻身、婦女解放等現代意識形態的萌芽,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塑造新人、改變舊社會的主題的呼應,同時也響應了現代社會的意識形態,使小飛蛾成了啟蒙話語預設下的開明母親。她與張木匠的矛盾和解,建立在歲月對記憶的淡化和呵護艾艾婚姻自主的意愿上,張木匠突然不再堅持舊習俗,他們一夜間冰釋前嫌,一同默默支持艾艾。這樣的矛盾和解,實際上回應著隱含讀者對有著慈母和仁父的、仁愛和諧家庭的共同記憶,這一人倫重歸和睦的小家庭恰似傳統農耕社會價值觀念的理想形態,隱約顯示著屬于舊社會農民的傳統道德觀念于《登記》的在場證明。以現代讀者的眼光來看,這樣的矛盾和解是相當模糊且不可信的,因為小飛蛾這一人物之所以仍具有典型意義,充滿獨特魅力,不僅僅在于其順應了主流政治話語,作為問題揭示的“話頭”,還在于除母親身份以外,小飛蛾也是飽受身心創傷卻從未被征服的妻子。
四、結語
趙樹理的作品之所以到今天仍然能作為現代文學的經典,就在于他的故事本身有更為豐富而寬廣的向度,存在著眾多可供后世人闡釋的空間與可供探討的時代癥候,依然在與當代研究者、讀者發生互動,進行著溝通。很多年后,《婚姻法》已經不必經“宣傳”便深入人心,但“登記”的故事卻一直在被閱讀,后世讀者已能越過《婚姻法》,發現在逐漸寬松的土壤里小飛蛾的自覺,以及她身上所內蘊的生命能量。對于小飛蛾與故事中其他人物的關系的探究,能夠使研究者注意到趙樹理小說中未被關注的性別問題與身份問題。
參考文獻:
[1]趙樹理.趙樹理選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2]白春香.趙樹理小說的民間化敘事[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6.
[3]黃修己.趙樹理研究資料[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
[4]黃修己.黃修己集[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8.
[5]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6](法)露西·伊利格瑞.他者女人的窺鏡[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
[7]趙樹理.趙樹理文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8]白春香.想像對現實的征服——趙樹理“問題小說”內在結構探微[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04).
[9]朱慶華.論趙樹理小說“清官”斷案模式的貢獻與局限[J].甘肅社會科學,2002,(04).
[10]孫先科.作家的“主體間性”與小說創作中的“間性形象” ——以趙樹理、孫犁的小說創作為例[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01).
[11](俄)弗拉基米爾·雅可夫列維奇·普羅普.故事形態學[M].北京:中華書局,2006.
[12]周彥彥.“清官意識”的無意識流露——趙樹理小說的結構主義解讀[J].名作欣賞,2013,(08).
[13]張莉.重讀趙樹理《登記》:舊故事如何長出新枝椏[J].小說評論,20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