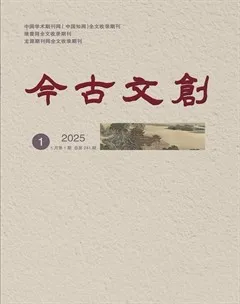《金鎖記》中“月亮”意象的隱喻分析及其英譯研究
【摘要】本文從概念隱喻理論視角,考察了張愛玲《金鎖記》中月亮意象的具體隱喻含義。《金鎖記》中的月亮意象不僅彰顯了時間流逝、場景轉換,也預示著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命運走向。在三個主要女性人物身上,月亮意象均作為女性命運的見證者存在,但在刻畫曹七巧時,月亮是人性欲望的象征;而體現(xiàn)在長安和芝壽身上,月亮意象則更多是人生蒼涼的寫照,在這悲慘蒼涼的一生中,長安是命運抗爭的失敗者,芝壽卻是命運壓迫的接受者。其英譯版本主要采取直譯的翻譯策略,對原文中月亮的具體形態(tài)及隱喻含義進行了再現(xiàn),反映了張愛玲對女性人物悲劇命運細致入微的刻畫和展示,在時代背景的大環(huán)境下,女性命運的悲劇性是注定的,但悲劇卻是不重樣的、永恒的。
【關鍵詞】概念隱喻;《金鎖記》;月亮;意象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月亮作為文學作品中的一個重要意象,是諸多作者筆下寫景傳情的重要文化符號。有時,它是抒發(fā)愁緒的窗口,是漂泊異鄉(xiāng)的游子思鄉(xiāng)懷人、凄苦心境的寄托;有時,它是慰藉心靈的寓所,是抑郁不得志之時遠離煩惱、撫慰心靈的天地;有時,它是美好愛情的見證,是追求純潔永恒愛情、尋覓美好佳人的期盼與向往[1]101。
張愛玲作為熟練、精確運用月亮意象的代表作家,她筆下的月亮掙脫了傳統(tǒng)月亮意象表意的束縛,一方面起到轉換場景、營造氛圍、提示時間的作用,另一方面卻在作者成長教育經歷、外來文化沖突、時局變幻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成為作者刻畫女性角色命運的獨特方式[2]22。這一文學效果突出展現(xiàn)在其中篇小說《金鎖記》中,在該作品中,張愛玲反復運用月亮這一意象,描繪了不同月亮的不同形態(tài)和特征,通過具體分析發(fā)現(xiàn),反復運用的月亮意象實則隱喻了處于不同人生階段、不同生活狀態(tài)的三位主要女性角色(曹七巧、長安、芝壽)的悲劇性命運。
本文基于概念隱喻理論對《金鎖記》中反復出現(xiàn)的月亮意象進行了較為系統(tǒng)地分析,在張愛玲筆下,月亮意象是對不同人物命運的隱喻和預示,這一方面為我們體會張愛玲對意象爐火純青、鮮明獨特的運用提供了參考和實例,也為其筆下其他意象運用的探討提供了借鑒。另一方面,這體現(xiàn)了張愛玲對女性悲劇性命運的關注和獨特表達,對讀者深入領會張愛玲創(chuàng)作心理、寫作主題、寫作風格,把握張愛玲小說的藝術特征提供了途徑和可能性。
一、月亮意象
月亮自古以來就是中西方文學作品中經久不衰的重要意象,是作者筆下傳情達意的重要文化符號。《詩經》中《陳風·月出》以“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憂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表達借月懷人的憂思愁緒;曹操《短歌行》借“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抒發(fā)賢才難覓的愁緒;張若虛于《春江花月夜》借“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引發(fā)出對人生的思考、對生命的感悟。
莎士比亞在《羅密歐與朱麗葉》兩人的對白中借月亮表達了變化的無常:羅密歐想要憑著皎潔的月光起誓時,朱麗葉說月亮每月都有盈虧圓缺,憑著月亮起誓,也許愛情也會像月亮一樣無常。
月亮意象在毛姆《月亮與六便士》中象征著理想、真愛與逃避現(xiàn)實的“烏托邦”,“月亮”與“六便士”正代表了理想與現(xiàn)實的對立,當主人公的繪畫夢想在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無法立足時,塔西提島便成了他心中像月亮一樣神圣浪漫的“烏托邦”。
月亮在中西方文學作品中都是廣為運用的重要意象,其內涵既相似又不同。劉琳對兩種文化中的月亮意象進行了對比分析,認為月亮雖然都作為一種寄托情感的意象符號存在,但它們所傳達的豐富含義卻截然不同。在中國文學中,月亮是思念故鄉(xiāng)和家人的獨特意象,可以排解寂寞、失意和迷茫情緒,可以營造溫柔、快樂和慈祥的氛圍,可以表達時空和人生的永恒。在西方文學中,月亮意象傳達了對永恒的幸福與愛的追求,對人的占有,是與人分離時的常用意象,在西方人眼中,月亮是多變的、運動的,而非永恒的、一成不變的[3]16。
劉鋒杰也簡要提到了中西方文化中月亮意象的異同,但他將目光聚焦在張愛玲身上,關注了張愛玲在月亮意象運用上的獨創(chuàng)性,這一獨創(chuàng)性基于張愛玲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中月亮內涵的繼承和對西方文化中月亮意象內涵的吸收[4]59。張愛玲創(chuàng)造了心理月亮這一意象形態(tài)并借助于蝕月意象的創(chuàng)造取得了成功。她筆下的蝕月除了是自然現(xiàn)象外,更是一種心理現(xiàn)象,張愛玲借助這一意象傳達濃烈的情感,抑或是使字里行間都充斥著痛苦憂郁、詭譎癲狂乃至死亡的氣息。
劉三平將目光聚焦于張愛玲的中篇小說《金鎖記》,從三個角度對文中反復出現(xiàn)的意象進行了分析:同一意象反復出現(xiàn),分別從不同角度加以描述;同一意象反復出現(xiàn),從同一角度多次加以描述;同一意象的反復出現(xiàn),意象之間有潛在的發(fā)展關系[5]38。他將月亮意象歸為第一類,但并沒有對文中的具體實例做細致、具體的分析和解讀。
在此基礎上,后續(xù)研究擴大了聚焦范圍,對除《金鎖記》外,《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傾城之戀》等多部作品中的月亮意象進行了分析和解讀。
郎學初認為張愛玲筆下的月亮意象既是家族沒落和時代變遷的見證者,也是女性世界失意的見證者[6]54。張愛玲賦予經典的月亮意象以現(xiàn)代含義,從而表現(xiàn)出了蒼涼循環(huán)卻無能為力的悲觀主義人生哲學,使其作品呈現(xiàn)出獨特的文學和美學價值。田美麗和盧長春則更多關注了月亮意象與文本中女性角色及其命運的聯(lián)系[7][8]。田美麗認為張愛玲對月亮的隱形屬性有充分的體驗和了解,在繼承傳統(tǒng)文學中月亮意象含義的同時進行了發(fā)展和豐富,使月亮意象展現(xiàn)出了鮮明的性別意識,成了表現(xiàn)人物心理、性格、女性群體地位和命運的重要手段。與田美麗相同的是,盧長春認為張愛玲筆下的月亮意象被賦予了鮮明的性別色彩,并結合例子對上述不同小說文本中的月亮的具體內涵進行了詳細的分類:月亮是女性命運的見證和形象的代言人,是人性欲望的象征,也是人生蒼涼的寫照。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最終將目光聚焦在《金鎖記》中的月亮意象上,依據(jù)盧長春對月亮具體內涵的分類,從概念隱喻理論的視角分析文中反復出現(xiàn)的月亮意象對文中三位主要女性人物命運的隱喻。
二、《金鎖記》中月亮意象的隱喻分析
月亮在張愛玲《金鎖記》中是一個著墨眾多的意象,全文以月亮為行文線索將曹七巧、長安、芝壽三個女性人物的命運串聯(lián)起來,環(huán)環(huán)相扣,發(fā)人深省。
文章開篇張愛玲就以間隔三十年維度的月亮引發(fā)對時間流逝、命運輪回的感慨。張愛玲在此處對比了年輕人和老年人眼中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人眼中是“銅錢大的紅黃濕暈”,是“陳舊迷糊的淚珠”,是迷蒙的,像眼淚一樣又咸又苦的,帶著淡淡的悲傷和蒼涼之感。老年人眼中的隔了三十年的月亮是“歡愉的,更大更圓更白的”,卻又不免是“凄涼”的。月亮永恒存在、循環(huán)往復,月光下的一代代人的命運也在不斷地繼續(xù)著[9]21。形態(tài)各異又相似的月亮形態(tài)見證著一代代人迥然不同又不斷重演的人生經歷和命運走向。
小說的女主人公曹七巧是一個終身為金錢所困,并不惜以自身及身邊人幸福為代價的女子。這里將月亮描繪為“銅錢大的紅黃的濕暈”,一方面生動形象地描繪了月亮的形狀、顏色、大小等具體形態(tài),呈現(xiàn)出強烈的畫面感,讓讀者身臨其境,另一方面緊密契合了文章主題,月亮預示和見證了即將出場的主人公曹七巧在金錢和欲望的折磨下悲慘的命運走向,既有傷感,又有嘆息[10]120。
文中第二段提到“月光照到姜公館新娶的三奶奶的陪嫁丫鬟鳳簫的枕邊”[11]71,這里以月亮意象為線索,將上文中對月亮的關注轉換到人物身上。
在月光下,三奶奶鳳仙的陪嫁丫鬟鳳簫借七巧的丫鬟小雙之口,引出了文中的主要人物曹七巧,對其卑微的身世、潑辣的性格和錯位的婚姻進行了簡單的交代[2]22。劉鋒杰在分析張愛玲作品中的月亮意象時曾說,張愛玲擅用蝕月形態(tài)來營造冷酷、陰郁、死亡的氛圍[4]59。文中寫道:“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點,低一點,大一點,像赤金的臉盆,沉了下去”[11]74,這里運用“下弦月”這一殘缺的蝕月形態(tài),借其逐漸減少的形態(tài)和其下沉的過程,預示了七巧接下來的命運,隱喻了其生命逐漸衰落消逝的過程,為她接下來的掙扎、沉淪和人性的扭曲變態(tài)埋下了伏筆。
楊有娥將缺月稱為張愛玲在長安的世界里安置的意象[9]21。張愛玲在刻畫長安時運用月亮進行了環(huán)境描寫,刻畫了被遮擋著的“模糊的缺月”,缺月這一意象為長安決定退學前一晚眼中的月亮形態(tài),彼時的長安受盡了母親的逼迫,在老師同學面前丟盡了臉面。她眼中的月亮是不完美的、殘缺的,被灰墨的天和白云遮擋著,呈現(xiàn)出一副朦朧模糊的畫面。這里以殘缺的月亮意象隱喻了長安不完美、殘缺的人生,灰墨的天和白云對月亮的遮擋正如曹七巧對長安無處不在又密不透風的禁錮和控制,隱喻了長安人生中的被強加的痛苦和悲哀,是長安蒼涼人生的寫照。被瘋狂控制之下的長安雖有不安和反抗,最后卻無可奈何。
畫面一轉,筆墨又回到七巧身上,然而這一次她的身份卻發(fā)生了極大的轉變,她從在金錢、婚姻、封建家庭迫害下的受害者變?yōu)榱颂幪幈破取O盡刁難兒媳的婆婆。
兒子長白娶親后,七巧對兒媳芝壽十分不滿,她變本加厲地在深更半夜要求長白去她房里為她燒煙,阻止長白與芝壽同房,不斷打談并當眾取笑長白與芝壽的夫妻隱秘,而夜里高懸的月亮成了靜謐無聲卻全知全能的旁觀者[9]22。隔著玻璃窗看見的影影綽綽的月亮,“一搭黑,一搭白,戲劇化的猙獰的臉譜”,這里描繪被云層遮擋模糊迷蒙、陰森可怖的月亮,渲染出陰森恐怖又瘋狂的氛圍,象征著七巧深受折磨又不斷折磨他人的瘋狂病態(tài)狀態(tài),烏云消散后,緩緩冒出的月亮就像“面具底下的眼睛”,而這雙眼睛正是來自被金錢和情欲雙重折磨的七巧,是她探聽兒媳芝壽隱私的陰險又惡毒的眼睛。她對身邊人的監(jiān)視和控制,就像高懸的月亮一樣安靜無形,但又無處不在、極盡癲狂病態(tài)。
丈夫不管不問、婆婆瘋狂扭曲,芝壽眼中的世界是瘋狂又荒誕的,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不像婆婆,將她這個外來人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以至于她看到天上高懸的滿月時,竟神經質地覺得它像是“漆黑的天上一個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陽”,那反常的太陽無處不在般地監(jiān)視著她,讓她恐懼害怕、汗毛凜凜。在描繪芝壽死前的狀態(tài)時,文中這樣寫道:“月光里,她的腳沒有一點血色——青、綠、紫,冷去的尸身的顏色。她想死,她想死。她怕這月亮光, 又不敢開燈”[11]99。月亮與太陽各自代表著黑夜與白晝,張愛玲將月亮比作漆黑的天上的白太陽,混淆了黑夜與白晝,是詭譎而陰冷的。以黑白兩色形成鮮明對比,并輔以“汗毛凜凜”“反常”“灼灼”等形容詞,營造出恐怖異常的氛圍,將七巧的變態(tài)人格和猙獰心態(tài)得到了擴放和彰顯,同時也將芝壽的恐懼心理得到了外化[6]57。
文章最后,張愛玲切換視角,回到開篇提到的跨度三十年的月亮,此時故事接近尾聲,三十年前的月亮已經沉了下去,七巧的生命也走向了盡頭,用月亮的下沉隱喻了人生命的消逝和結束。但三十年前的故事并沒有完,月亮還會升起,人的生命也將繼續(xù),長安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七巧,七巧的悲劇仍在繼續(xù)著。月亮這一意象貫穿全文,或是環(huán)境描寫,或是隱喻人物命運,在不知不覺中月亮已經成了窺視著七巧一家的、全知全能的見證者。在月亮的描寫里,讀者走進故事又走出故事,月亮的恐怖可怕揭示了人事的可怕病態(tài),月亮的升起沉淪也象征著世間人事的起伏沉淪[5]38。永恒的、循環(huán)往復的月亮見證著一代代人的命運和悲劇的重演與再現(xiàn)。
文章開篇和結尾以間隔三十年形態(tài)各異又相似、循環(huán)反復的月亮隱喻了一代又一代人生命的起始和衰落,在時光流逝中既相似又不同的命運往復輪回著。其后又以“銅錢大的紅黃濕暈”般的月亮預示曹七巧被金錢禁錮和折磨的一生,接著以下弦月這一缺月形態(tài)隱喻七巧逐漸衰落的命運走向,以缺月形態(tài)象征長安被七巧嚴密控制和禁錮的殘酷不堪的人生,以臉譜、面具般的月亮形態(tài)揭示了在七巧控制下芝壽注定屈服的命運,強調了七巧對身邊人病態(tài)癲狂的控制和禁錮。最后月亮呈現(xiàn)出完滿的形態(tài),將月亮與太陽、黑夜與白晝的界限模糊,將其進行混淆,形成強烈的反差,營造出恐怖異常的氛圍,強調了七巧控制的瘋狂程度和芝壽的極度恐懼與不安狀態(tài)。
三、《金鎖記》中月亮意象隱喻英譯分析
觀察發(fā)現(xiàn),作者在文本英譯過程中主要采用了直譯的翻譯策略,注重選詞和表達的精確性,對原文中月亮意象的具體形態(tài)和特征進行了生動地再現(xiàn),精準直觀地傳達了原文潛藏的深厚內涵,此處選擇了幾處較為典型的例子進行分析和解讀。
文章開篇將目光從月亮轉到主人公曹七巧身上時,提到“那扁扁的下弦月像赤金的臉盆一樣一點點沉了下去”[11]74,張愛玲在英譯時將“扁扁的下弦月”譯為“the flat waning moon”[12]142。“waning”一詞意為“as the moon then goes from full to new again,we see a diminishing portion of its illuminated half,and this is called waning,which means decreasing in strength or intensity”,在這里準確地傳達了下弦月逐漸減少的形態(tài)及下沉的過程,預示了七巧生命逐漸衰落消逝的過程。作者在英譯時用詞考究精準,注重還原原文中月亮的具體形態(tài),從而精妙傳達其表達的具體內涵。
在以月亮意象刻畫長安的悲慘命運時,張愛玲用到被烏云遮擋著的“模糊的缺月”這一形象,在英譯時她將其翻譯為“a blurred chip of a moon”[12]171。“chip”一詞意為“broken pieces from a complete one”,精準地描繪了原文中月亮的殘缺形態(tài),對理解原文中長安自己不完美的、殘缺的人生提供了可能。
在突出刻畫七巧對家里人嚴密窒息的控制時,張愛玲寫到烏云里影影綽綽的月亮,它像“猙獰的臉譜”,又像“面具下的眼睛”。在譯文中張愛玲譯為“the moon was barely visible behind dark clouds”[12]174,通過直譯的方法還原了原文中月亮的形態(tài)和特點,便于讀者理解月亮影影綽綽、迷糊不清的形態(tài),從而理解七巧對身邊人的無處不在、密不透風、令人窒息的監(jiān)視和控制。
文章結尾,張愛玲再次將視角聚焦在間隔三十年的月亮上時,她直譯為“the moon of thirsty years ago”[12]191,譯文直白明了地用傳達了原文中作者的意圖:用月亮的下沉隱喻了人生命的消逝和結束。
四、研究結果
分析發(fā)現(xiàn)文中多處“月亮”意象共同實現(xiàn)了“人生是一輪月亮”這一結構性隱喻,其中“月亮”為始源域,“人生”為目標域。“月亮的升起”隱喻“人生的開始,即人的出生”,“月亮的下沉”隱喻“人生的結束,即人的死亡”,“月亮的各種形態(tài),如滿月、缺月等”隱喻“人生的各種狀態(tài),如悲傷、空洞等”。
在文中各處的“月亮”這一意象具體內容不盡相同,在三個主要女性人物身上,月亮意象均是女性命運的見證者,預示和見證人物命運的起伏興衰,但在刻畫曹七巧時,月亮是人性欲望的象征;而體現(xiàn)在長安和芝壽身上,月亮意象則更多是人生蒼涼的寫照,在這悲慘蒼涼的一生中,長安是命運抗爭的失敗者,芝壽卻是命運壓迫的接受者。
對比原文及其英文譯本發(fā)現(xiàn),作者在文本英譯過程中主要采用了直譯的翻譯策略,選詞精準、用詞考究,在保留中國傳統(tǒng)月亮意象的基本內涵的同時,基于自身主體性因素,綜合漢英兩種語言隱喻表達的異同,保留了原文中對月亮及其特征的描述,再現(xiàn)了原文的生動隱喻和寫作風格、主旨。
五、結語
張愛玲選取月亮這一自然意象,以鮮明強烈的色彩形成對照,以華美的“象”寫凄涼的“意”,創(chuàng)新了月亮意象的運用和解讀。《金鎖記》中月亮意象不僅是時間流逝、場景轉換的提示器,更是刻畫和預示女性人物的命運走向的獨特符號和方式。張愛玲借月亮意象的各異形態(tài)展現(xiàn)了女性命運的多樣性。文章生動再現(xiàn)了月亮意象的具體形態(tài)和特征,反映了張愛玲對生命、社會的思索和獨特表達,在時代背景的大環(huán)境下,女性命運的悲劇性是永恒的、注定的,但悲劇卻是不重樣的。
《金鎖記》中反復出現(xiàn)的月亮意象以其不同的形態(tài)隱喻和預示著不同人物命運的走向和發(fā)展,這一方面為我們體會張愛玲對意象爐火純青、鮮明獨特的運用提供了參考和實例,也為今后從不同視角探討其他意象的系統(tǒng)性研究提供了借鑒和參考。另一方面,這體現(xiàn)了張愛玲對女性悲劇性命運的關注和獨特表達,揭示了張愛玲悲涼的人生觀與價值取向,是其藝術個性和審美風格的體現(xiàn)與凝聚,為讀者深入領會張愛玲創(chuàng)作心理、寫作主題、寫作風格,把握張愛玲小說的藝術特征提供了途徑和可能性。
參考文獻:
[1]葛金平.古典詩詞中月亮意象的起承與功用[J].江西社會科學,2012,32(10):99-102.
[2]王靜,王玉琴,劉桐彤.解讀張愛玲——論《金鎖記》的敘事藝術[J].名作欣賞,2005,(8):21-25.
[3]劉琳.中西方文學作品中月亮意象差異比較[J].語文建設,2015,(14):16-17.
[4]劉鋒杰.月光下的憂郁與癲狂——張愛玲作品中的月亮意象分析[J].中國文學研究,2006,(01):56-63.
[5]劉三平.《金鎖記》中的“意象反復”[J].修辭學習,2001,(6):38-39.
[6]郎學初.月亮的夢魘——試論張愛玲作品中的月亮意象[J].名作欣賞,2008,(20):54-57.
[7]田美麗.張愛玲小說中的月亮意象[J].中州學刊,2002,(6):79-81.
[8]盧長春.張愛玲小說中的月亮意象[J].齊魯學刊,2009,(1):150-152.
[9]楊有娥.月色式蒼涼 宿命式荒涼——談張愛玲《金鎖記》月亮意象與女性命運的關系[J].名作欣賞,2006,
(24):20-23.
[10]謝泳.張愛玲小說中的“月亮” ——讀張愛玲小說札記[J].名作欣賞,1994,(2):117-122.
[11]張愛玲.金鎖記[A]//張愛玲全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71-111.
[12]Eileen Chang.The Golden Cangue[A]//Eileen Chang.Love in A Fallen City and Other Stories[M].Penguin Books,2007:142-191.
作者簡介:
舒雪倩,女,重慶開州人,西安外國語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理論語言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