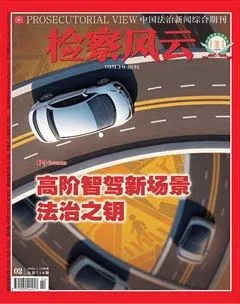自動駕駛汽車視野下的責任劃分

自動駕駛以將人從駕駛中真正解放出來為初衷,不僅可以顯著提升交通效率,也有助于降低事故概率,客觀上還催生出全新的產業鏈、商業模式和經濟增長點,其發展牽動著智能操作系統、物聯網、城市基礎設施、車輛檢測與認證等相關產業的聯動升級。
近年來,自動駕駛的全球應用與商業化進程加速。2024年8月,美國加州政府披露,Waymo無人駕駛出租車在舊金山總共完成了27.35萬次訂單。在中國,截至2024年7月,百度在武漢投入1000輛蘿卜快跑無人出租車,已經累計拿下500余萬次訂單。在自動駕駛的普及率不斷提高的同時,其所帶來的數據利用、安全管理與致害責任問題也引起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盡管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交通運輸部等印發的《智能網聯汽車道路測試與示范應用管理規范(試行)》與各地地方性法規形成了道路測試、示范應用、示范運營與商業化運營的智能網聯汽車測試“四步走”的治理框架,但隨著自動駕駛應用的加速落地,自動駕駛致害責任救濟問題日漸凸顯,亟須結合技術特征與商業模式進行探討。
自動駕駛汽車的歸責困境
數據顯示,目前特斯拉的FSD完全自動駕駛能力介于L4到L5級別之間,屬于全球領先水平。國內層面,百度的第六代蘿卜快跑無人駕駛汽車裝配了支持L4級別無人駕駛應用的自動駕駛大模型。而華為最新發布的尊界S800,也使L3級別的自動駕駛功能正式上線。以上現狀表明,我們已經進入自動駕駛時代,傳統汽車原有的單一工具屬性與客體角色發生深刻變革,人與車之間從機械時代簡單的“駕馭與被駕馭”之單向關系,逐漸演變為共享操控權限的互動格局。在這一互動格局下,“駕駛員”和“乘客”的身份界限變得模糊,智能駕駛對現行以人為核心的交通法律體系造成了巨大沖擊。
2024年10月4日,江西交警通告了一車主在高速開啟自動駕駛后,低頭擦汗片刻車輛便失控撞向路障的交通事故。基于我國現行道交法規則,事故責任認定書明確表明由機動車一方承擔全部責任。在無人或人干預缺失的自動駕駛模式下,若不能明確事故發生時的責任歸屬,或讓機動車一方背負全部事故責任,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自動駕駛系統開發的初衷,無疑將阻礙自動駕駛技術的商業化落地。要破解這一僵局,亟須針對我國法律體系與自動駕駛技術、產業發展現狀就歸責路徑進行系統梳理。
盡管各地地方性法規對自動駕駛責任劃分已有所涉及,如《上海市浦東新區促進無駕駛人智能網聯汽車創新應用規定》第二十九條第二款明確規定了高級別自動駕駛的責任劃分規則:交通事故依法應由智能網聯汽車一方承擔責任的,由該無駕駛人智能網聯汽車所屬的企業先行賠償,并可以依法向負有責任的自動駕駛系統開發者、汽車制造者、設備提供者等進行追償;但目前尚未有國家層面的統一規則。這就使得自動駕駛致害責任的歸責路徑、責任構成和賠償范圍等方面仍存在不確定因素。
對自動駕駛汽車產業而言,重要的不是哪一種歸責理論更為科學或者更為精妙,而是哪一種歸責理論更為契合自動駕駛的技術因素與商業模式,從而供給清晰可行的責任規則。
與此同時,作為創新產物,自動駕駛汽車往往伴隨新型商業模式的出現。根據我國《智能創新發展戰略》和各地普遍開始采用出租車形式開展自動駕駛測試的現狀,高級別自動駕駛汽車的發展方向應以商業化應用為主,個人私有化使用相對較少。因此,關于自動駕駛致害責任的討論,應以商業模式對責任劃分的影響為重點。同時,也需要考慮個人私有自動駕駛汽車可能引發的責任問題,以確保責任體系的全面性和適用性。
如何構建歸責路徑
當自動駕駛車輛發生交通事故時,主要涉及民法典、道路交通安全法、產品質量法等法律,受害人在侵權救濟路徑的選擇上,一般存在產品責任和保有人無過錯責任兩種路徑。
路徑一:生產者、系統開發者應承擔的產品責任。具體來說,當自動駕駛汽車因“產品缺陷”導致事故發生,生產者和開發者應承擔相應的產品責任。我國產品質量法第41條和《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對此均有所規定。將自動駕駛汽車認定為“產品”并沒有法律上的障礙。不過,在“軟件定義汽車(以軟件為核心的汽車架構)”成為趨勢的情況下,系統開發者作為軟件提供者,可能并非具有造車資質的生產者,對其責任的追究即成為問題,亟須設計從生產者到軟件研發者的追溯機制。如果具有造車資質的生產者與系統研發者身份重合,問題則相對簡單。
適用產品責任的另一個問題是自動駕駛汽車產品責任的抗辯事由。我國產品質量法規定了“產品投入流通時,缺陷尚不存在”的抗辯事由。在自動駕駛場合下,因自動駕駛系統可能升級更新,“流通時間”隨之調整,其判斷時點已不能僅以車輛出廠銷售時間為準。至于發展風險抗辯,生產者和開發者能否適用也存在爭議:一方面,如果允許適用,受害者可能在保險賠付不足時無處尋求救濟;另一方面,若不適用,則抗辯事由僅限于“未投入流通”和“缺陷不存在”,對生產者和開發者過于嚴苛,不利于科技創新。這一問題反映了安全與創新的兩難抉擇。兩難抉擇的核心在于受害者損失能否得到合理賠償,設置合理的自動駕駛保險制度或救助基金之后,即成為可能的選擇。
路徑二:以保有人無過錯為核心的機動車肇事責任。自動駕駛車輛的保有人需在損害發生時承擔賠償責任,不論事故是否因其過錯所致。這一責任的核心理由在于,對風險源的控制和利益享有者,應對其可能造成的危害負責。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兩個維度予以討論:其一,是車內乘客受損情形。在私有模式中,車輛所有人被視為保有人,若無合同關系的乘客(如“好意同乘”)因事故受損,保有人需基于無過錯責任進行賠償。這種安排既符合車輛作為風險源的特性,也與現行司法實踐和判例相呼應。在商業運營模式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823條,運營商需對乘客傷亡承擔無過錯責任。尤其是在自動駕駛出租車領域,由于自動駕駛系統的高風險特性,以及公眾對其安全性的高度關注,運營商需承擔更高的保障責任。這不僅是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也有助于提升社會對自動駕駛技術的信任。其二,是車外第三人受損情形。無論私有或商業車輛,若自動駕駛汽車致第三方受損,保有人需承擔無過錯責任。自動駕駛車輛雖具備高安全性,但其在復雜環境下仍可能存在感知、決策和執行上的局限性與網絡安全風險。因此,必須有主體對這種潛在的危險承擔相關責任,而自動駕駛汽車保有人因其控制車輛且享有使用利益,應當被課以此種責任。此外,確立保有人的無過錯責任與現行的交強險制度能較好銜接,使責任承擔機制更加完善。
明確自動駕駛汽車的保有人責任與生產者、系統開發者的產品責任后,需要進一步厘清這兩種責任之間的互動機制,以構建完整的責任鏈條。受害者如認為事故源于產品缺陷,可以選擇產品責任作為賠償依據。但此時,受害者需依法舉證,證明自動駕駛汽車存在缺陷且該缺陷導致了損害結果,才能獲得生產者或系統開發者的賠償。受害者也可以選擇保有人無過錯責任為賠償依據。在這種情況下,保有人或其保險公司需先行承擔賠償責任。如果保有人認為事故并非自身過錯,而是因產品缺陷引發,則可以根據產品責任向生產者或開發者追償。追償過程中,生產者或開發者可以主張發展風險抗辯及其他合法免責事由。對于涉及自動駕駛系統缺陷的事故,產品責任與保有人無過錯責任沒有法定的優先適用順序,受害者可以根據自身情況自由選擇。為了更好地保護受害者,在地方立法探索中多優先由保有人承擔責任。保有人或保險公司完成賠償后,可通過追償向生產者或開發者索賠。如《深圳經濟特區智能網聯汽車管理條例》第54條規定,若自動駕駛汽車在交通事故中因存在缺陷導致損害發生,車輛駕駛人、所有人或管理人在按照本條例第53條對受害者進行賠償之后,有權向汽車的生產者或銷售者提出索賠。這種安排既能督促運營商與開發商承擔相應責任,又能免除受害者繁重的技術缺陷舉證負擔,從而更好地保護其權益。
綜上所述,自動駕駛汽車責任劃分體系應構建以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融合機動車肇事責任、產品責任的整體架構。因為,對自動駕駛汽車產業而言,重要的不是哪一種歸責理論更為科學或者更為精妙,而是哪一種歸責理論更為契合自動駕駛的技術因素與商業模式,從而供給清晰可行的責任規則。不可否認的是,責任規則的變動會改變甚至重塑自動駕駛產業格局。
(作者陳吉棟系上海市人工智能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同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