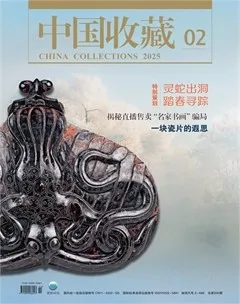“收納”珍寶古人自有妙招
家具的使用歷史悠久,作為實用工藝品,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關,更承載著明確的社會功能,反映出不同時代的審美特征。明清時期,傳統家具的制作水平是中國古代家具發展歷史上的鼎盛期,柜架類家具作為家居陳設、物品儲存和珍玩展示等多項功能的載體,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架格陳設文房
架格亦稱為“書格”,是用來陳設、擺放物品的家具。其最基本的樣式是以立木為四足,四足之間施橫棖與順棖,用以安裝隔板,隔板一般有三層或四層,常用于書房存放書籍文玩。為了增加其整體穩固性和耐用性,通常會在最底層格板下面施加牙條和牙頭。

故宮博物院所藏黑漆嵌螺鈿山水花卉紋架格(圖1)是典型的架格。其整體結構為四面開敞的方材,共分四層。每層橫棖與順棖間打槽裝板,板下用三根穿帶承托,底部為黃銅套足裝飾。框架邊緣滿飾以彩色薄螺鈿和金銀片托嵌而成,內部鑲嵌螺鈿山水、人物、花果、草蟲等精美圖案。
此架格在造型上遵循著明式家具的基本樣式,但在裝飾上卻運用了精湛華美的漆藝,呈現出簡約與繁復裝飾的對比之美。尤其是在架格中間一層底面刻有“大清康熙癸丑年制”款,表明其制作于1673年,這種帶有紀年款的家具較為稀見。
歷史上較早記錄架格的學者是“ 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的曾孫文震亨,他在其所著《長物志》中將架格分為大小兩種,“大者高七尺余,闊倍之,上設十二格,每格僅可容書十冊,以便檢取,下格不可置書以近地卑濕故也,足亦當稍高”。明代的一尺與今相差不大,高七尺余基本上就是2.1米左右,這一高度基本屬于正常身高的人舉手曲臂就能夠輕松取放書籍,方便檢索使用。書中還強調了架柜下層的格不宜放置書籍,以免書籍受潮致損,因此最下層的格板要與地面保持一定距離,這表明了作者對南方濕潤環境的考慮。
亮格柜展示器物
亮格柜是明式家具中的一種,由架格和柜子相結合而成,常見的形式是架格在上,柜子在下。架格的高度一般與人肩齊,或稍高一些,便于展示、觀賞器物。其整體設計注重下部分重心,有利于家具的穩定性。北京匠師稱上部開敞無門的部分為“亮格”,下部有門的部分為“ 柜子”,二者結合起來就形成了“亮格柜”。這種家具兼備陳列展示與收藏存儲兩種功能,實現了美觀與實用的統一。

按照存放物品的層次和結構設計,亮格柜可分為單層亮格柜與雙層亮格柜兩種。北京藝術博物館所藏明代黃花梨亮格柜(圖2)屬于單層亮格柜,上層架格部分裝有后背板,其余三面裝有壺門圈口牙板。架格的左右兩側以攢斗的手法做出萬字紋飾。下方柜子部分對開兩門,柜門采用鑲嵌的素板來凸顯材質之美。在傳世的亮格柜中,單層亮格的款式要比雙層亮格更為多見,這主要是由于雙層亮格柜需要同時兼顧亮格與柜子的功能,所以容易陷入兩個空間分配的矛盾中。
多寶格切割空間
多寶格是清式家具的代表之一,由明式家具中的架格演變而來。與傳統架格相比,多寶格在設計上使用橫板與豎板,將空間切割成若干個高低不等、大小各異的格子。這種柜架款式大致出現在明末清初。
多寶格的出現是明式家具受到滿族傳統家具影響的例證。1644年清軍入關后,滿族傳統家具便與明式家具相融合。其中一種用于展示、陳放物品的家具,叫作額林。《欽定滿洲源流考》載:“庋橫板楣棟間,以貯奩、篋、缾、甕諸器具,兼幾案、匱櫝之用。”楣棟指的是房屋的正梁和次梁,在正梁和次梁之間裝橫板便是額林。與傳統家具部件有所不同,額林更像是建筑的一部分。

在故宮博物院漱芳齋中有一套五件的多寶格,緊貼墻壁擺放,與房間融為一體。一些格子鑲嵌有不同形態的拐子紋角牙,而總共12個小抽屜的面板則呈現出不同的圖案。通過設計,5件多寶格之間切割出了100多個空間,擺放對應的器物,整體和諧統一,琳瑯滿目。這套多寶格與建筑的結合,依稀能夠看到額林的影子。
即便到了乾隆時期,滿族傳統家具仍被當時統治者所重視,比如乾隆帝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叩祖謁陵的途中作詩《盛京土風雜詠十二首》,其中就有一首涉及“額林”:“橫拖木板置楣振,家計精粗具畢陳。菽栗為文莫忘古,雕幾作器漫求新。”

除滿族傳統家具的影響外,文人的影響力也一直在發揮作用。明式家具之所以具有簡練、厚拙、空靈等特點,與文人的需求和品位息息相關。明末清初時期著名戲劇家和文學家李漁在其代表作《閑情偶寄》的“ 器玩部”中,詳細記錄了對幾案、椅杌、床帳、櫥柜等家具的獨到理解與建議,明確表達了對于櫥柜類家具的兩個意向——其一是多設隔板,可以在每層的兩邊釘細木二條、增設活板。這樣當需要放大體量物品時,可以撤掉活板,增大空間;放置較小物品時,再放回活板,實現一層變兩層的效果。其二是多設抽屜,抽屜內部應該分割為大小不同的格子。這兩個意向對多寶格的產生有著深遠的影響。
從傳世實物來看,清早期的多寶格還處于探索階段,樣式并不固定。比如清康熙時期的黑漆嵌螺鈿花蝶紋架格(圖3),雖然還被稱為架格,但第一層分成兩面開敞及三面開敞的兩個格間,中間出現了隔板,一層格下還懸一抽屜;第二層四面全敞,格板上有一紅漆描金拐角幾。種種變化與明式家具的架格并不相通,反倒是很符合李漁所提倡的多設隔板、多裝抽屜的理念。這可以算是架格發展為多寶格進程中的一個例子。
又如一件清雍正至乾隆時期的紫檀多寶格(圖4)打破了以立木為四足的定律,采用以紫檀木做邊框、內部為髹漆板的做法,以隔板和邊框將空間切割成不規則的形狀。
此時期的傳世文物較多,空間切割的形式也各不相同。但總體來看,清早期的多寶格樣式不一,沒有清中后期的程序化制作。抽屜、隔板的使用增多且靈活,抽屜可大可小,出現的位置可上可下。橫板與豎板的組合可長可短,很少規矩的等量分割空間。開光不僅是在豎隔板上使用,還會出現在背板及兩側山,形狀也有方形、圓形、扇形、菱形、方勝形等。在切割出的格子內,還會放入小幾之類的家具進一步將空間切割,同時放入的小幾本身也作為一件珍玩展示。其所用材質也不局限圖4 清雍正至乾隆 紫檀多寶格長107厘米 寬50厘米 高155厘米于紫檀花梨等硬木,髹漆多寶格也很多。
柜格盛極一時
這里所說的柜格,特指上部為多寶格,下部為柜子相結合的一類家具,也有稱其為“書柜式多寶格”的。其最早出現于清早期,清中期之后開始流行起來。
多寶格中用柜子來切割空間的方法從清早期就已經出現,但并不是只要多寶格中出現柜子就是柜格,而是根據柜子的大小,對開柜門要占整體空間一半左右的、寬度要與整體寬度等同的,才被稱為柜格。

故宮博物院所藏《雍正帝行樂圖》描繪了冬天季節,雍正皇帝坐在火盆旁讀書的情景。背景中出現了一組柜格,展示了雍正時期多寶格與柜子相結合的柜格面貌。畫中呈現了黑漆描金柜格,上半部分為多寶格,中間平設兩具抽屜,下部是兩對對開門的柜。多寶格通過橫豎板切割展示空間,每一格都采用欄桿、角牙或圈口進行裝飾。其右側設兩個小抽屜,中間有一個較大的抽屜,每個抽屜的面板修飾各不相同。格內擺放著書籍、包袱、印章、瓷瓶等珍寶。下部的柜子,兩對柜門裝飾黑漆描金山石花卉紋。
清中期之后,上部為多寶格、中間平設抽屜、下面設柜子的形式變得非常流行。清中期紫檀嵌琺瑯柜格(圖5)分三部分,多寶格的設計高低錯落,每一格均安裝琺瑯西蕃蓮拐子花牙,背部及格頂則鑲有玻璃鏡。格下設抽屜兩具,底部兩門對開,嵌五爪龍紋琺瑯片。柜門之下施鏨胎琺瑯西蕃蓮卷草紋牙條。
柜格之所以能在清早期就出現,應是受到了亮格柜的影響。在架格發展為多寶格的同時,人們也注意到了不同組合相互搭配之下產生的新的家具形式。比如架格與柜子相結合產生亮格柜,多寶格與柜子結合便產生了柜格。而由亮格柜產生的架格與柜子爭搶空間的問題,也因為多寶格靈活多變切割空間的特點所解決。
明式家具與清式家具在我國家具發展史中皆是璀璨的明珠。明式家具尚意,盡管雕飾不多,但榫卯結構精巧合理、各構件處理得當,簡約而不簡單。而清式家具則重形,其品種豐富,追求奇巧,選料考究,不計人工。同時,清式家具還善于將其他工藝融合其中,吸收西方藝術特點。明清兩種家具各有特點和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