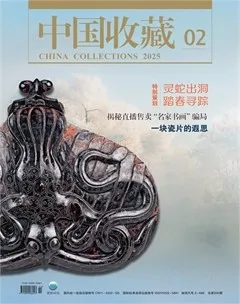“描白”銅鏡工藝待解

2017年4月底,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舉辦了“必忠必信”銅鏡專題展,其中有一面西漢晚期“描白”工藝的特種工藝鏡。從存世器物看,“描繪”工藝大致可分“描黃”“描白”兩類。有專家認為,黃色是金質,白色為錫質。“描黃”者如《中國青銅器全集·16(銅鏡)》圖69;“描白”者即此鏡。此類特種工藝另在春秋戰國兵器中有見。此鏡博局紋為凹面框,鈕座均柿蒂紋,乳釘呈下凹狀。
上海博物館譚德睿研究員認為,此鏡可能應用了雙重涂覆的“液態富錫工藝”,即先在鏡背上通體涂覆一層富錫涂料,待固化后再用筆蘸取另一種含錫量更高的液態富錫涂料,于已有涂層上描繪出纖細紋飾,再經加熱而成。
自春秋至明代的銅制兵器、銅鏡等銅器表面,常見一種色澤亮白的銀色,民間稱為“水銀沁”,以往之謂錯銀、鎏銀、烙銀等,這與事實不符,多系猜測。經科學檢測,古代銅鏡表面呈亮白銀色的原因,除少數為鑲嵌銀絲或復貼銀片外,大多數為銅鏡表面經富錫處理后而呈現的銀白色效果。“富錫”之謂,是因該處表面的含錫量遠高于銅器本體,且與銅器本體之間產生了相互擴散的物理化學(非機械附著)作用,形成新的銅錫合金組織——富錫相,銀白色與耐磨蝕是其兩大特點。
古代有三種此類工藝:粉末富錫、膏劑富錫、液態富錫。近年來,譚德睿已將這三種失傳工藝挖掘出來并應用于生產實踐。
粉末富錫即用已失傳的含錫含汞之粉末狀磨鏡藥,在常溫下摩擦鏡面,即可生成厚度為納米級的富錫層,光亮可鑒。因為涂覆層太薄,日久即恢復本色而照容不佳,故出現了磨鏡的行業,早在《淮南子·修務訓》中就有記載:“明鏡之始下型,朦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

膏劑富錫是用含錫量較高的銅錫合金粉末,摻以天然粘接劑等配料制成膏狀,涂覆于銅鏡表面,固化后加熱,富錫膏劑中的錫即向銅器本體擴散,在表面形成富錫組織,其厚度近以毫米級。舉世聞名的越王勾踐劍和吳王夫差矛表面之菱形紋飾即如此。此外,漢唐銅鏡背面具一定面積(非線條)之銀白紋飾,也是由此工藝形成。
液態富錫則是用含錫量較高的銅錫合金粉末,摻以天然懸浮劑等材料,配成墨汁狀之狀態,可用毛筆蘸取后描繪于銅器表面,再經加熱,形成微米級的富錫層,自漢代至明代的銅鏡等器物上皆有所見。
除了西漢晚期特種工藝“描白”銅鏡外,同好摯友曾提供過一張戰國時期的狩獵紋“描白”鏡照片,言其直徑11.8厘米,重90克。此外,《清華銘文鏡》圖42,直徑13.9厘米,重454克,這也是當時采用“液態富錫工藝”的一種經典實例,在鏡背的凹面方框與博局紋處,皆呈現出亮白的銀色。
甲辰仲秋,在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技術遺產》第一輯中,譚德睿發表了《漢唐以來若干金屬器物成型與裝飾工藝待解之謎概覽》,文中圖24即為本文講述的西漢晚期特種工藝“描白”銅鏡。他在文中指出:“此鏡屬西漢時期‘規矩’鏡。常見的規矩鏡其L、T形浮雕周邊有凸起線條構成紋飾,鑄造而成。‘描白’鏡的L、T形浮雕周邊滿布銀白底色,其上又有突起的云紋等十分纖細流暢的白色線條,極罕見。從表面剝落狀態觀察,白色似涂繪而非表面合金化形成,應屬彩繪工藝,精致華麗……這種歷經兩千多年仍保持白色的涂層,由含高錫的銅-錫合金形成,其配方和涂繪工藝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