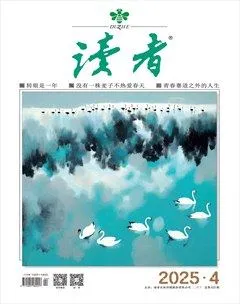青春賽道之外的人生

一
我第一次見到安安是在上高中的第一天。
當我從校門口的分班榜單上看到自己被分到年級最好的班級時,激動得手舞足蹈。一回頭,我看見一張憤怒的臉。一個女孩向她的母親不滿地喊道:“叫你不要找關系把我分到快班,你偏不聽。我就算去了也跟不上!”
她便是安安。
安安的成績差得離譜,全班倒數第一。老師將她安排在第一排,跟高度近視的我成了同桌。但我一開始不和她說話——從小到大,我媽都不喜歡我和成績差的同學交朋友,害怕他們把我帶“壞”了。媽媽理想中的好朋友是朝陽學姐那樣的。
朝陽學姐比我高兩屆,和我住在同一個家屬院。在學習上,她是我們院子所有小孩的榜樣。朝陽學姐高二那年,參加全國奧林匹克化學競賽得了一等獎,被保送到復旦大學。這個消息在整個院子炸開了鍋,家長們成群結隊地到她家“取經”。
我就是在那個夏天被媽媽送到朝陽學姐家去的。
當我羞澀地推開她臥室的門時,一個扎著丸子頭的女孩正坐在木地板上聽CD。見我怯生生地站在門外,她抬起頭沖我一笑,有如春風拂面。
那天,我并沒有討教到什么學習經驗。她表示自己并不是一個學習機器,她只是喜歡化學,參加競賽,拿到了獎。她還告訴我,她媽媽一直建議她讀金融專業,可她一點兒也不感興趣。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只要你專注于自己喜歡的事,沒有道理不成功。”她堅定地告訴我。
她還給我聽了她CD里放的歌,那是她最愛的樂隊演唱的。耳機里傳來的音樂喧囂而雜亂,震得我耳朵發疼,我一點兒也不喜歡。但我覺得她整個人酷得發光。
二
我再次聽到朝陽學姐CD里的那首歌,是在安安的MP3里。
一個炎熱的下午,安安在體育課間隙坐在樹蔭下聽歌,腳尖跟著節奏打著拍子。我被蟬聲吵得焦躁,也過去坐在她身邊,她突然把耳機往我耳朵里一塞。
音樂響起的那一瞬間,我的雞皮疙瘩都起來了。一個不入流的“學渣”竟然擁有和學霸一樣的音樂品位,我不禁對安安肅然起敬。
安安告訴我,歌名是《別哭》(Don't cry),一首“槍炮與玫瑰”樂隊創作的搖滾樂。樂隊成員們留著長發,穿著很朋克,手臂上布滿文身。
安安也很“朋克”。她的耳骨上打了一排耳釘,頭發頂部燙著當時流行的“玉米須”,裙子很短。每次學校抓校風校紀,她都會被責令整改。
但外表的叛逆只是一個方面,安安還擁有“搖滾”的內涵:憤怒。她是一個易怒的女孩,像煙花一樣一點就炸。我們班不少同學都怕她,只有我常和她待在一起。
我們經常一起去逛書店。書店一角有許多好看的小文具,但價格偏貴,安安和我從來只看不買。有一天,她興奮地告訴我,書店要做周年慶促銷活動,買文具的小票面值每滿200元就送12元現金券,還可疊加使用。她說:“我們去書店門口找買了文具的人要購物小票,他們留著也沒用,一定會給我們的。”
我拉不下臉,遠遠地躲在一邊。安安大大方方地站在書店門口,見人就問對方是不是買了文具。那天,安安要到的購物小票面值加起來接近2000元,共兌換了9張12元的現金券。她一口氣買了6個筆記本和一把中性筆,讓我挑走一半。
我想要卻覺得受之有愧,尷尬之余,忍不住開口打破沉默:“你為什么不直接找你媽媽要錢買呢?”
“我才不要她給我買。”安安搖頭說,“用了她的錢就要聽她的安排,就像我不愿讀咱們班也被硬塞進來一樣。我的人生要自己做主。我最期待的就是經濟獨立,過自由自在的生活。”
媽媽對我和安安越來越近的關系感到不滿。她覺得倒數第一的女孩將來一定不會有出息,這樣的“壞”坯子不會成為一個“好”朋友。她多次告誡我不要和安安來往,還讓班主任把我和安安的座位調開,阻斷我們倆的一切聯系。
三
高一下學期文理分班之前,我經常去找朝陽學姐。
沒有高考壓力的學姐生活得非常灑脫。她參加了校乒乓球社團,跟著一群專業的體育生南征北戰。升大學前,她拿到了國家二級運動員證書,古箏過了10級。
我在學姐家讀完了《巴別塔之犬》。她為了讓我改掉看了開頭就看結尾的壞習慣,一直陪著我讀書,等我要回家時就把書收回。
直到她去上大學,我也沒來得及向她咨詢我該讀文科還是理科。
這之后,我和安安被分到了不同的班。她的理科班教室在3樓,而我的文科班在頂樓,我們只能見縫插針地湊在一塊玩。
我們倆現在回憶起高考前的那兩年,都覺得苦大于甜。我說她當時上學跟上刑似的,她說我補課跟補鈣一樣。
高考成績出來后,成績不理想的我選擇了復讀。安安去了杭州某專科學校。
復讀期間,迷茫的我給朝陽學姐寫了封郵件。學姐很快回復了我,還把她新學期的作息時間表發給了我——每一天都排得滿滿當當,充實得像我的一周。她說自己一直計劃讀研,所以從大一開始就按照申請全額獎學金的保研標準在做準備,本科讀完將赴香港大學繼續深造。
我把學姐的郵件打印出來,復讀期間,每次覺得自己即將崩潰時,就拿出來看看。
安安常給我打電話,鼓勵我咬牙堅持。
她的大學生活并沒有她想象的那么美好,她和舍友的關系很不融洽,課很無聊,連談戀愛也索然無味。她宅在寢室里逛論壇、貼吧,還學會了網購。
時間過得飛快,第二年高考,我終于考上了一本。
四
我的大學生活既不像朝陽學姐的那樣充實,也不像安安的那樣無聊。我按部就班地上課、考試。
有一年寒假回去,媽媽說朝陽學姐在香港大學談了個男朋友,對方家境優渥,同樣品學兼優。媽媽總是不放過任何一個說教的機會。多年來,她從我的生活和學習過程中發現,我和她理想中的女兒背道而馳。我安于現狀,畢業后最想做的工作是圖書館管理員,泡在圖書館里看海量的書籍,掙夠用的工資,過平淡的一生。
也是那年寒假,安安告訴我她申請了一家網店,專賣衣服。她教我開通了網銀,讓我在網上下單,給她刷評價。
我對她的網店事業并不看好,身為學生,不好好學習反倒賠錢做生意,不是舍近求遠嗎?但安安認為如果自己現在就能掙到錢,誰還在乎讀不讀大學。
安安的網店事業并沒有做起來。她開店一個月,真正成交的只有一單,沒掙上錢,反而虧了一個月的生活費。
在朝陽學姐研二那年,我和安安去香港找她玩。
多年沒見,學姐已然發福,常年堅持的運動應該停下了。她的寢室不大,卻擺滿了東西。床頭散放著許多音樂專輯,課桌上立著一個相框,里面放著一張她和一個高個子男生在香港太平山頂的合照。
學姐的男朋友早已畢業,在上海找到了工作。他勸學姐放棄讀博,畢業后去上海,可她并不愿意。對于自己在化學領域的深造,學姐也有些動搖。同一所學校的,化學專業應屆畢業生的工資只有計算機專業畢業生工資的一半。過幾年,收入差距會越拉越大。她不知道選擇讀博到底對不對。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學姐搖擺不定。我發現在前進路上高歌猛進的她,也不過是個普通人。
我不知道該如何安慰她。
安安卻充滿干勁地拍了拍學姐的肩膀,說:“等下次痛仰樂隊巡演的時候,我們一起去現場聽《公路之歌》。”
“好啊。”學姐點點頭。
從香港回來,安安發現香港的化妝品價格比內地的便宜,她打算重新開個網店賣化妝品。我問她貨源是哪里,她說在學姐所在學校的公共游戲室認識了一個女孩,留了聯系方式。那個女孩家境一般,支付香港這邊的學費和生活費挺吃力。內地學生在香港不能打工,她可以給安安當買手。兩個人按比例分利潤。
我以為安安又是心血來潮,沒想到她真的做起了化妝品代購。后來開通微信,她就天天在微信朋友圈大張旗鼓地叫賣,產品種類越來越豐富。
后來,聽我媽說朝陽學姐和男朋友分手了。我想起學姐床上的音樂專輯。她都從搖滾聽到了民謠,誰又能保證愛情一成不變?
而安安和朝陽學姐相約一塊去看痛仰樂隊的巡演,一直未成行。
五
朝陽學姐申請到了美國弗吉尼亞大學讀博的全額獎學金。
她臨走前回了一趟老家。我發現她并沒有特別高興,她父母也十分平靜。學習上的成就再也不能給予他們全家意氣風發的喜悅了。
我們還是像以往一樣,坐在地板上聊天,學姐臉上卻是一片迷惘。她的學業瓶頸早已出現:資質雖不差,但已觸及天花板。現在她常質疑自己不夠變通,沒有魄力,錯過了轉行的最佳時機。她本科的一些同學畢業后自主創業,有的在互聯網行業,有的進軍房地產,短短幾年已小有成就,可她還一事無成。
同一時期,在風口發展起來的安安已實現財務自由。作為最早的一批代購者,安安從“港代”起步,逐步發展成多國代購,有了規模不小的代理團隊,日進斗金。
現在,安安還會直播代購的過程,在直播中向粉絲推薦好用的貨品,告訴大家衣服怎么搭配才好看。她受到一群粉絲的熱捧,儼然一位時尚達人。年紀輕輕的她已經在二線城市買了車和房。
我媽對安安如今的成就感到不可思議。每年春節安安回老家上門來找我,我媽都格外熱情,叫我多跟安安學習,說我們這種從小一起玩、知根知底的交情最可貴。她仿佛忘了,自己曾經用盡一切辦法想要拆散我和安安。
我媽再也不把朝陽學姐掛在嘴邊當榜樣了,反而覺得她讀書厲害又有什么用,也沒見她多孝順父母,掙的錢還不如安安這個大專生多。評價相當功利。
人生路那么長,不走到最后誰也不知道結局會怎樣。
畢業后,我進入一家報社做編輯,一待就是5年,薪資的增幅完全趕不上通脹的速度。我媽常說我是只沒出息的青蛙,只會坐井觀天,被溫水燉熟了還沾沾自喜。如今紙媒式微,我還是不愿離去。天天和報紙相伴,也算曲折地實現了自己當圖書館管理員的愿望。
最近,我無意間翻出我們在香港拍的合照,想起安安和學姐之間那場未能履行的約定。我上網找出痛仰樂隊的《公路之歌》,在線試聽。
“夢想,在什么地方,總是那么令人向往。我不顧一切走在路上,就是為了來到你的身旁……”
那時的我們還非常年輕,未來正閃閃發亮。
(章期帆摘自臺海出版社《真故·女性敘事》一書,本刊節選,陳 曦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