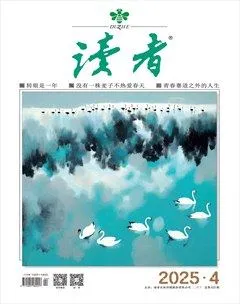胸口上的刺青

深夜1點40分,在救護車上待命的我們接到無線電呼叫:“77歲男性,心搏驟停……”
拒絕的刺青
深夜的紐約,交通沒有白天擁擠,救護車幾分鐘就趕到一棟看起來有點老舊的公寓大門口。我們迅速拉出擔架,帶著電擊器和其他基本設備,往患者家中跑去。
大門開著,一名中年男子一看到我們,立刻帶領我們穿過客廳,進入臥房的浴室。我們看到倒臥在浴室地上的老先生,似乎沒有了呼吸和心跳。當我用隨身攜帶的剪刀剪開他的上衣準備進行電擊時,赫然看到老先生胸口上有著大大的刺青:Do Not Resuscitate!
Do Not Resuscitate,簡稱DNR,通常是指病人或其法定家屬所簽署的一份同意書,同意當病人瀕臨死亡或沒有生命跡象時,不施行心肺復蘇,也就是不急救。
這是一份需要本人、見證人及公證人共同簽署,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原始文件由病人或家屬保管,醫療機構會留一份復印件存檔。但是,在緊急醫療事件中,除非當場看到具有法律效力的DNR文件,否則緊急救護員還是會以搶救為優先做法。
我很確定,在身上刺寫的DNR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他用洗不掉的刺青寫在急救時不可能看不到的胸前,就是希望在他無法親自傳達此信息的重要時刻,以此表明他的意愿。
自己的心愿
心肺復蘇,是患者心臟停止跳動后,為恢復患者自主呼吸和自主循環而采取的急救方式。在急救的過程中,需要用極大的力量反復在患者胸腔上施壓,有人甚至用“暴力”來形容這一過程。常聽說在心肺復蘇過程中有患者肋骨被壓斷,從而刺傷其他臟器的事件發生。這也是有些重癥末期的患者或家屬愿意簽署DNR的原因,它實際上是為了使患者少承受一些不必要的折磨。
當時我愣了一下,隨即看了一下旁邊的人,并大聲詢問:“有DNR的證明嗎?”一位老太太坐在床邊,好像還沒從驚嚇中回過神來。帶我們進來的中年人好像是患者的兒子,站在門口一臉困惑,“DNR?”他激動地大聲嚷道,“什么DNR,趕快搶救!還在等什么?”
“不要急救。”突然,老太太開口了,“我們討論過了。這幾年他的身體狀況大不如前,病痛不斷,能夠這樣走是他的福氣。”
“病痛不斷?你在說什么?”兒子一臉不可置信,“我從來沒聽你們說過啊,救人要緊!快救人啊!”
“你住得那么遠,不清楚我們的生活狀況。我們確實討論過了,他就是希望當自己遇到危急情況時,可以不被干擾,平靜地離開人世。他怕找律師簽同意書要花很多錢,所以特地在胸前刺了Do Not Resuscitate。”老太太指著老先生胸前的刺青說。
“什么?”兒子顯得六神無主,但還是堅持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么!不管怎樣,先救人再說!”
我再次跟老太太確認:“你們沒有簽不要急救的相關文件嗎?”老太太搖了搖頭。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別無選擇,一定要急救。我一邊跟老太太解釋,一邊著手電擊。看著強大的電流通過老先生的身體,把他震得從地上彈起來,老太太轉身離開。兒子目不轉睛地看著整個急救過程。經過一連串電擊、心肺復蘇后,老先生又有了心跳。一有心跳,我們就立刻將他移上擔架,送進救護車,駛往醫院。一路上,我們還是得繼續用人工方式幫助他呼吸。
平凡的瑣碎
一星期后,我回到老先生所在的醫院。詢問后得知,當天急救后,老先生雖然恢復了呼吸和心跳,但再也沒有醒來。在加護病房住了數日,最后家人還是決定放棄。我想,假若這位老先生生前能利用住院的機會,詢問一下醫護人員或社工,獲得關于“不要急救”的正確信息,事情也許會有不同的發展。
現代社會中,許多子女都住得離父母有段距離。但生活常常是由許多瑣碎的細節組合而成的,若是雙方分居兩地,要了解對方的生活,確實很有挑戰性。
我有個朋友住在美國得克薩斯州,雖然平常忙著工作跟照顧孩子,但還是常常惦記住在國內的父母。有一次我回國,他要我幫他帶些東西回去,有訓練記憶的小游戲,做運動時用的各種器具,等等。
當來到他父母家時,我看見大大的房子里只住著二老,有一間房里堆滿了子女托人帶回的各種東西。我有些遲疑地將朋友委托帶回的記憶游戲拿出來講解,卻注意到伯父的視力已經弱到無法閱讀的地步。再取出做運動用的器具時,我看到伯母需要用拐杖才能從沙發上站起來,餐廳旁還放著一輛輪椅。
生活,是由每天、每時、每刻的點點滴滴累積而成。而人們偶爾聯絡,會著重于敘述不平凡的經歷。雖然現在科技發達,人們隨手按一個按鍵就可以經由網絡看到對方,但很難通過這樣的對話想象對方生活中平凡的瑣事。例如,父母未必會提到他們現在無法一覺睡到天亮,半夜一定會起來上廁所,有時甚至不止一次,所以睡不好;現在食量不比從前,晚餐吃三個餃子就飽了;以往天天去小區里做晨操,最近雙腿無力,已經有一個星期沒去了……
獲得優質時間,或是高質量的相處時間,可以讓彼此在沒有壓力的狀態下呈現自我,分享生活。這其中的要點,在于自處和相處。
(小 小摘自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生命這堂課》一書,劉 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