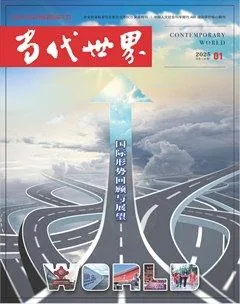顛覆性技術與地緣政治視域下的歐洲產業政策回歸
【關鍵詞】顛覆性技術" 地緣政治" 歐洲產業政策" 技術政治
近年來,以生成式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可控核聚變等新技術為代表的顛覆性技術革命,已開始顯現聚合性的加速突破效應,由此引發技術自創生(Technical Autopoiesis)的能力進一步涌現,如典型的“美第奇效應”(The Medici Effect)正在推動各類全新技術的隨機組合與深度融合。跨域技術的交互性和融合性將引發從技術到內容、從硬件到軟件的全方位技術和產業綜合體重構與再構,繼而催動新一輪國際技術全面競爭。在技術飛速發展帶來的時代轉折大背景下,全球產業競爭已不再僅僅關乎經濟,而是帶有更多地緣政治意蘊。在此背景下,許多國家開始重新重視產業政策。[1]2024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顯示,2023年全球出臺了超過2500項干預性產業政策,其中超過一半來自美國、歐盟和中國,最活躍的行業則是軍民兩用技術,包括半導體芯片、低碳技術以及關鍵礦物。[2]歐盟曾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堅定支持者和傳統產業政策的最強烈反對者,如今已經成為新一輪產業政策競爭的先行者和主要推動者。歐盟內部越來越多的聲音認為,僅僅依靠加強貿易防御手段來保護歐盟免受來自第三國的工業和地緣政治政策的侵害是不夠的,歐盟應該自發性地制定更強有力的產業政策,以實現加速綠色轉型、數字轉型和加強歐盟戰略自主權的三重目標。[3]
顛覆性技術與地緣政治發展重塑產業政策
1995年,美國學者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首次提出“顛覆性技術”(Disruptive Technologies)這一概念,認為顛覆性技術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取代現有主流技術。[4]回顧歷史上三次科學技術和產業革命,不難發現,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推動生產力的快速躍升,并引發全球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政治架構改變。因此,顛覆性技術本身可以超越克里斯坦森基于市場概念的認知,并且這一技術作為全新的生產要素,可以對生產關系的建構發揮關鍵作用。基于此,顛覆性技術可界定為能夠通過創新性突破徹底改變現有行業格局、重塑市場并影響全球政治經濟力量平衡的技術及其應用。在當今時代,顛覆性技術是以生成式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可控核聚變等為代表的尖端技術,這些技術彼此成就、相互賦能、迭代突破,并能夠顛覆眾多領域現有的底層技術。顛覆性技術發展開辟了傳統技術發展軌道之外的新技術應用領域,不僅使各國圍繞生產力發展和提升國家實力的競爭愈發激烈,而且改變了國際格局特別是基于傳統地緣要素的國際競爭邏輯和地緣政治現狀,由此加劇世界政治的體系性變革。
與傳統的尖端技術相比,顛覆性技術通常具有幾大顯著特性。一是突破性。傳統技術通常是在現有技術基礎上通過漸進改良來提升性能或效率,屬于線性發展模式,如硬盤容量的增加、計算機處理器的性能升級等。顛覆性技術則遵循完全不同的技術原理,開辟出全新的發展路徑。以量子計算為例,它不再依賴傳統的二進制計算,而是基于量子疊加和糾纏等原理,這種革命性的計算方式可以實現指數級別的運算速度提升,顛覆了傳統計算架構。二是融合性。顛覆性技術的發展是不同領域技術的交叉融合,涉及諸多復雜的系統和相互關聯的因素。多領域技術融合會形成一個持續進化的反饋回路,加速技術的迭代和突破。例如,大數據與機器學習相結合推動深度學習算法的優化,而深度學習算法的優化又反過來提升大數據處理的能力。這種技術之間的相互促進形成了一個“創新涌現”的環境,使顛覆性技術能夠以更快的速度實現應用和推廣,帶動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三是不可預測性。顛覆性技術的應用場景通常在研發初期難以完全預見。例如,互聯網最初僅用于軍事和學術研究,但最終引發了信息革命,應用于社會的各個領域。正是由于顛覆性技術的發展速度、規模和具體形式難以預見,其涌現將會引發對技術領導權的爭奪。國家一旦在顛覆性技術領域取得優勢,將會輻射經濟、軍事、社會等各個方面,從而在國際博弈和合作中具備更強的談判能力和競爭優勢。


顛覆性技術所呈現出的突破性、融合性和不可預測性等,通常會打破原有的技術路徑依賴和市場格局,推動各類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重新配置。這一過程不僅會催生許多新興產業,還將迫使傳統產業深度轉型與升級。在顛覆性技術走出實驗室之初,具有較強技術創新能力的國家或企業,通過加速布局研發、政策支持和技術基礎設施建設,可以在全球競爭中迅速崛起,而另一些則可能被技術淘汰而走向衰落。在顛覆性技術發展帶來的大國競爭與博弈明顯加劇的當下,產業政策作為國家競爭戰略工具和手段的回歸與使用,使國家可以通過國內政策對全球價值鏈進行干預性介入和強力性重構。產業政策也開始從傳統的“經濟導向”轉向由技術本身主導的“安全導向”,其中以美國產業政策的變化最為顯著和直接。美國已經將顛覆性技術創新視為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在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等關鍵領域。近年來,美國逐步通過立法(如《芯片與科學法案》)、出口管制和投資限制等方式,試圖限制關鍵技術向競爭對手國家流轉,同時加強自身在顛覆性和戰略性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
歐洲產業政策回歸及其動因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著名的“看不見的手”概念,強調自由市場對經濟的調節作用,認為自由市場中的個人利益追求能夠促進社會整體的繁榮。過去幾十年來,歐盟的經濟模式一直遵循亞當·斯密的這一理論,認為競爭和自由市場能夠有效驅動效率提升和創新,減少政府干預帶來的資源浪費。二戰結束后,歐洲國家面臨嚴重的經濟和社會重建問題。為了避免國家間競爭導致新沖突,推動國家間經濟合作成為歐洲的重要選擇。在1957年簽訂的《羅馬條約》中,歐洲明確提出創建一個共同市場,促進商品、資本、服務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以實現更大的經濟效益。之后,歐洲又通過《單一歐洲法案》(1986)、《歐洲單一市場》(1993)等一系列政策,推動形成區域內統一的經濟治理體系,避免成員國政府過度干預導致資源不適配,以提升歐盟整體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5]
近年來,在地緣政治沖突及技術突變的雙重影響下,越來越多的經濟體認識到,不僅需要重新審視全球價值鏈時代的相互依賴,而且有必要在供應鏈薄弱環節加大產業政策的支持力度,以確保自身安全及著眼自身的未來競爭力。由此,歐洲主要國家均不同程度地調整了經濟政策,各國政府傾向于在經濟事務中扮演更加積極主動的角色,如法國的“新工業法國”計劃和“未來工業”計劃、德國發布的《工業戰略2030》和《時代轉折下的產業政策》等系列高級別戰略文件等。有研究表明,德法兩國作為歐洲最大工業國和產業領導者具有實施產業政策的物質基礎,可以產生“有產業之產業政策”效應,其出臺的政策必然對整個歐洲產生“泛歐洲性”影響。[6]在歐盟層面,2023年9月6日,歐盟委員會內部市場專員蒂埃里·布雷頓(Thierry Breton)在布魯蓋爾年會上發表題為《歐洲式產業政策》的演講,這是歐盟官員對歐洲產業政策基本思路的一次系統闡述。歐盟及其成員國的戰略文件導向與政策行為顯示,在技術優勢減退、保護主義上升,特別是在地緣政治的外部推力共同影響下,歐盟產業政策已經開始發生明顯轉向。
首先,顛覆性技術領域的落后(投資、研發等)使歐盟在全球產業競爭中處于弱勢,而歐盟內部對技術轉型的迫切需求不斷增強。從對顛覆性技術的投資力度看,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NSB)的統計數據,自2008年以來,美國、中國和日本牢牢占據了世界研發支出前三位。2021年,中國的研發支出比歐盟的第三大支出國(法國)高40%,研發強度(研發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也高于歐盟。[7]從投資領域看,過去20年,歐盟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化學、汽車工業等成熟技術領域,這些技術出現突破的潛力相對有限。相比之下,美國在通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可控核聚變等顛覆性技術領域持續加大投資,不斷培育技術新業態,資源逐漸流向具有高生產力增長潛能的部門。在此背景下,許多歐洲創新公司傾向于遷出歐洲。2008—2021年,近30%的歐洲獨角獸企業將總部遷到海外,其中絕大多數遷往美國。[8]對顛覆性技術投資的忽略導致歐盟慢慢落入“中等技術陷阱”(Middle Technology Trap),最終呈現工業結構相對固化、創新能力不足、無法跟上全球科技發展前沿步伐的糟糕景象。2024年9月,歐盟委員會發布《歐盟競爭力的未來》報告指出,歐盟每年必須增加約8000億歐元投資,才能保持經濟競爭力,不被中美等國拉開距離;如果得不到這些投資,那么歐洲將不得不面對在與中美等國競爭時持續失速的“緩慢痛苦”。[9]
其次,歐盟推動戰略自主以應對國際競爭與技術轉型的雙重壓力,其中針對性產業政策是關鍵一環。歐盟的戰略自主與產業政策回歸是一個相輔相成的互動過程,前者提供了政策轉型的理論基礎和實踐驅動力,后者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工具和手段。新冠疫情全球肆虐期間,歐盟因在醫療物資、疫苗生產等領域對中國、美國和印度等國出現高度依賴而引發警惕,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2020年度盟情咨文演講中就明確提出“歐洲需要一個新的戰略自主政策”。[10]而應對烏克蘭危機不力,則暴露出歐盟在防務、能源、數字技術和供應鏈上的嚴重不足。為此,歐盟相繼出臺《芯片法案》、構建碳邊境調節機制等以強化供應鏈韌性和技術競爭力。由此可見,歐盟已將戰略自主理念深度嵌入其產業政策框架,并通過強化關鍵領域自主性,提升其產業政策的戰略高度與協調能力。
最后,地緣政治格局轉變與大國競爭加劇,共同推動歐盟產業政策的回歸與重塑。新冠疫情和烏克蘭危機等突發性事件疊加沖擊,加速了全球供應鏈重組,暴露出全球諸多領域尤其是關鍵物資和高端制造領域供應鏈存在的問題,歐洲在這方面的問題尤為突出。在此背景下,歐盟出臺了一系列產業政策以實現供應鏈的多元化和本地化。例如,2022年出臺的《歐盟關鍵原材料法案》明確提出,到2030年,歐盟關鍵原材料的本地化開采比例需達到總需求的10%,而加工比例需達到40%。此外,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溢出效應也使歐盟重新審視自身對關鍵技術的依賴。歐盟在關鍵技術,如芯片設計、云計算、人工智能應用等領域高度依賴美國的核心技術支持,而在供應鏈的關鍵節點,如稀土、鋰等戰略礦產等方面則高度依賴中國,上述關鍵技術與礦產都是現代化產業體系至關重要的構成要素。美國加大對華技術遏壓也進一步促使歐盟推動“開放的戰略自主”政策落地,尤其是在半導體、人工智能、綠色能源等領域加大本地化生產力度。例如,《歐盟芯片法案》計劃在芯片領域投資430億歐元,吸引包括英特爾、三星、臺積電等企業在歐盟設廠。歐盟這些舉措旨在減少對中美技術和原材料的依賴,增強在全球科技和產業競爭中的獨立性。
歐洲產業政策回歸的新特征
歐洲產業政策回歸是對全球地緣政治變革、顛覆性技術涌現、全球化轉型的綜合應對。在戰略方向上,追求戰略自主是當下歐洲產業政策的核心目標之一。隨著中美科技競爭加劇以及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顯現,歐盟目前正在尋求降低在多個關鍵領域的戰略依賴。但與歐盟傳統產業政策相比,當下產業政策回歸在理論框架和實踐形式上都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從而反映出歐盟對顛覆性技術創新、全球競爭格局以及內部市場整合的深刻思考。
第一,從自由市場邏輯到政府主導的戰略干預。長期以來,歐盟被視為奉行多邊主義與自由貿易的重要力量,其經濟政策與內部統一大市場實踐具有強烈的開放和自由色彩。其中,歐盟競爭政策嚴格限制國家對企業的直接干預。《歐盟運行條約》明確規定,控制政府援助行為的種類、規模和數量,以最大程度降低國家干預行為對內部市場的消極影響。但當下,歐盟已經放寬對這些規則的限制,并呼吁成員國賦予其更多的權力以協調歐盟政策工具,更高效地應對第三國以地緣政治目的對歐盟及其成員國采取的“經濟脅迫”。[11]自2021年5月開始,歐盟委員會相繼出臺《外國補貼管制規則草案》《歐盟投資審查年度報告》《保護歐盟及其成員國免受第三方經濟強制》等多項政策文件,通過對“經濟強制”的靈活定義,防止域外經濟力量對歐洲企業構成威脅。[12]在2024年4月舉辦的歐洲產業政策會議上,法國、德國和意大利代表共同呼吁歐盟需要制定一項共同戰略,以應對來自中國和美國的挑戰。[13]
第二,聚焦關鍵技術和戰略性產業。從歐洲過往產業政策特點來看,其多遵循新自由主義經濟治理理念來應對產業政策競爭力下降的問題,即偏好混合的“橫向”措施,而非針對戰略部門或技術的“縱向”措施。然而,隨著顛覆性技術迭代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產生全面嵌入性影響,技術高溢出性影響也反作用于傳統地緣和主權治理架構。歐盟在意識到顛覆性技術發展遲滯導致“落后”的背景下,開始聚焦關鍵技術和戰略性產業以應對挑戰。2023年6月,歐盟委員會發布首份經濟安全戰略文件——《歐洲經濟安全戰略》,并于同年10月3日發布包含10個技術領域的關鍵技術清單。關鍵技術領域的確定,為歐盟進一步在上下游進行政策部署提供了方向和依據。在上游,歐盟通過《關鍵原材料法案》以確保關鍵制造業能夠安全、充足地獲得所需原材料;在下游,通過出臺《芯片法案》和《凈零工業法案》,提出重點發展包括核能以及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內的“戰略性技術”。同時,歐盟成立歐洲半導體委員會,旨在推動相關芯片計劃和項目落地,進而謀劃歐洲未來在顛覆性技術領域建立產業領導地位。

第三,以手段多元化加強產業安全“長臂管轄”。歐盟不僅通過自身政策資源推動本土企業發揮競爭優勢,而且政策導向還延伸至產業安全與技術外流的防控方面,主要體現為嚴格的限制外資收購、發起反補貼調查、提高關稅等。例如,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于2021年和2023年先后出臺《外國補貼白皮書》《外國補貼規定》以收緊對外國補貼或外國財政資助的規制,并明確指出這些法案適用于“對歐盟具有戰略意義的部門和關鍵基礎設施”。2023年10月,歐盟委員會主動對原產于中國的電動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2024年10月,歐盟委員會表決通過對中國進口純電動汽車征收反補貼關稅的提議。這一系列行動旨在通過多元化手段強化行使“長臂管轄”的權力,以維護歐盟的供應鏈和技術安全,而這種以“安全”為導向的產業政策延伸則會產生地緣政治的溢出效應。當更多的產業聯系和供應鏈依賴從外部市場切除后,歐盟在地緣政治上將更多依賴本土的經濟基礎支撐,而這對過往的全球化模式而言將產生結構性影響。
歐盟產業政策回歸的影響
從內部看,歐盟產業政策的回歸為其應對全球技術競爭打下了一定基礎。一方面,保證技術供應鏈安全是歐盟在全球技術競爭中獲取主動權的重要前提。通過出臺《關鍵原材料法案》《芯片法案》和《凈零工業法案》等一系列法案,歐盟強化了對本地化供應鏈建設的政策和資金支持,從而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外部風險。同時,歐盟試圖通過加強在關鍵技術領域的戰略布局來彌補自身在芯片制造領域的長期弱勢,并構建起完整的技術生態系統。另一方面,歐盟產業政策回歸對其經濟治理理念與實踐構成巨大挑戰。歐盟本質上是一個發揮規制性職能的后現代聯盟,其綜合績效更多的是依靠規制性政策建構實現的。而產業政策則要求歐盟及其成員國在經濟運行中發揮更重要作用,這與歐盟長期以來強調的政府只發揮規制性作用相悖。在如何平衡市場自主性與政府干預的界限方面,歐盟內部尚未達成共識,尤其對產業政策是否會造成歐盟單一市場的分裂、是支持自由市場競爭還是支持產業政策扶持等問題還存在巨大爭議。[14]

從外部看,歐盟產業政策強調對新興技術的掌控,這將加劇歐盟和美國等技術強國的競爭。近年來,雖然美歐在科技與經濟領域的戰略協作頻繁,彼此的溝通也呈現機制化趨勢,但美歐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并未消弭,未來雙方將極有可能圍繞顛覆性技術領導權、技術標準制定權等展開競爭。2022年8月,美國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和《通脹削減法案》,向本土綠色技術企業提供巨額補貼,這也引發歐盟各界對美國“新保護主義”的擔憂。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IFRI)2023年10月發布研究報告指出,歐洲是“中美經濟競爭加劇的主要受害者”,美國產業政策的實質是依靠損害歐洲的利益來增強自身實力,同時美國又逼迫歐洲遵守美國的禁運政策,放棄對華貿易機會,這對歐洲商業利益造成了雙重損害。[15]歐盟產業政策與美國的《通脹削減法案》《芯片與科學法案》等政策在戰略目標上存在趨同性,但在執行方式和結果上呈現競爭態勢。與此同時,歐盟強化本土制造業和技術自主的政策舉措,也可能對美歐科技合作形成挑戰,這種政策競爭可能引發跨大西洋經貿關系的結構性緊張,至于其是否會影響跨大西洋地緣政治同盟關系則有待觀察。
從全球視角來看,歐盟產業政策的回歸正在深刻推動全球產業鏈調整,具體體現為供應鏈重構和技術標準提升。首先,歐盟試圖通過政策支持(如補貼、優惠貸款等形式)推動本土制造業復興,進一步突出國家政治在經濟與生產網絡中的角色和權重,尤其是在半導體、稀土材料、電池等戰略性行業。同時,隨著全球性產業政策的回歸,歐盟產業政策與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類似政策的協同,可能加速“逆全球化”趨勢,全球供應鏈將轉向更封閉、更區域化的供給模式。其次,多年來歐盟在國際標準化領域一直保持強大影響力,在國際標準競爭中擁有技術先發優勢。2024年3月13日,歐洲議會高票通過《歐盟人工智能法案》,這是全球首部綜合性人工智能監管法案,旨在推動歐洲人工智能規則和技術標準的全球化。此舉將高技術產品和服務的出口與戰略利益綁定,將可能引發與其他大國技術標準的競爭。最后,歐盟作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政治經濟實體之一,其政策轉向對于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也會產生深遠影響。在此背景下,歐盟將如何平衡與中美的關系以及如何重新審視“全球南方”市場,都與地緣政治密切相關。
結語
當下,技術變革下“萬物摩爾定律”的實踐正在顛覆生產流程,改變全球供應鏈形態和全球生產網絡組織形態。歐盟產業政策的回歸不僅是其應對全球顛覆性技術競爭壓力的戰略調整,還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全球政治經濟競爭范式,同時也會對地緣政治產生潛在深刻影響。在顛覆性技術革命背景下,提升國家技術競爭能力已并非歐洲的區域個案,過去開放的技術流通和交流體系,會因各國設置技術邊界而不斷減緩,技術本身的全球流動與擴散也會隨之減緩。[16]在技術政治化背景下的技術競爭與國家博弈將是未來影響全球發展及地緣政治格局的主要因素之一。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顛覆性技術發展對新型國際關系形塑研究”(項目批準號:23amp;ZD33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1] Peter Bofinger, “Industrial Policy: Is There a Paradigm Shift in Germany and What Does This Imply for Europe?” Social Europe, May 27, 2019, https://www.socialeurope.eu/industrial-policy-in-germany.
[2] Simon Evenett/Adam Jakubik/Fernando Martín/Michele Ruta, “The Return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Data,” IMF Working Paper, Janurary 4, 2024,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23/12/23/The-Return-of-Industrial-Policy-in-Data-542828.
[3] Green European Journal, “The Return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February 7, 2023, https://www.greeneuropeanjournal.eu/the-return-of-industrial-policy-in-the-european-union/.
[4] Bower J. Christensen C.,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Catching the Wav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5, Vol.73, No.1, pp.43-53.
[5] Sebastian Dullie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Industrial Policy,” Intereconomics, 2024, https://www.intereconomics.eu/contents/year/2024/number/5/article/european-industrial-policy-in-the-2020s-rationale-challenges-and-limitations.html.
[6] 余南平、張翌然:《德國產業政策轉向探究——技術與地緣政治的分析視角》,載《德國研究》2024年第4期,第4-28頁。
[7] 參見歐盟統計局網站: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R%26D_expenditureamp;oldid=551418。
[8][9]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Competitiveness,” September 2024, https://commission.europa.eu/document/download/97e481fd-2dc3-412d-be4c-f152a8232961_en.
[10] European Commissio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Plenary,” September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ov/SPEECH_20_1655.
[11] 鐘藝琛:《歐盟委員會的擴權與歐盟對華政策的嬗變》,載《歐洲研究》,2023年第4期,第1-29頁。
[12] 忻華:《歐盟:在大國戰略競爭旋渦中艱難追求“戰略自主”》,中國歐洲學會,2022年1月12日,http://caes.cssn.cn/yjdt/202201/t20220112_5388050.shtml。
[13] Science Business, “France, Germany, Italy Call for Single EU Industrial Strategy,” April 9, 2024, https://sciencebusiness.net/news/industry/france-germany-italy-call-single-eu-industrial-strategy.
[14] 同[3]。
[15] Institut Fran?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China/United States: Europe off Balance,” April 2023, https://ifrimaps.org/china-united-states-europe-off-balance/geopolitical-challenges-2/introduction-2.
[16] 余南平、馮峻鋒:《新技術革命背景下的歐洲戰略重塑——基于技術主權視角的分析》,載《歐洲研究》2022年第5期,第1-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