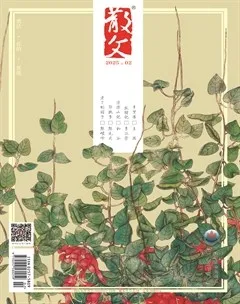蘋果,永遠是一個隱喻

一
金牛座的何小竹,平時話不多,走路有點慢,抽煙很兇,喝酒也蠻厲害;在生人面前有點淡漠,讓人覺得不太好接近;和朋友在一起相當平實可親,讓朋友們非常信賴。反常就只是酒喝多的時候, 如果突然開始滔滔不絕霸占席間話語權, 就表明他喝多了,這個時候的他甚至非常淘氣,會產生喜劇效果。
小竹,朋友們都這么叫他,只有他太太安柯叫他何小竹。小竹說,當安柯叫他小竹時,他會吃上一驚,然后意識到這是讓他幫忙倒杯水或者洗個蘋果啥的。
認識小竹的時間我記得很清楚,1998年。當時我剛生了孩子不久,他是我先生李中茂的朋友,上門探望。我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摻茶, 小竹趕忙站起來說我自己來自己來,這個場景,我一直清晰地記得。
之后,小竹成為我和中茂共同的朋友。2000 年,我出版隨筆集《華麗轉身》,請小竹為我作序, 他在序言里面給了我一個盛大的贊譽:“既能將兒子養得虎頭虎腦,又能將文章寫得妖里妖氣。”作為一個勤勉的母親和作家,我對這個評價非常感動。
后來, 我們兩家在城南一個小區買了房子,成了鄰居,多年來串門、喝茶、聊天、吃飯,土特產拎過來送過去,看著彼此的孩子逐漸長大,看著彼此的狗狗逐漸離去。兩家人一同外出參加活動、應酬、聚會,就商量好開誰家的車出去,回程時安柯當司機,中茂和小竹可以喝酒。
很多個晚上, 小竹和中茂這對酒友會在我家小酌幾杯。有時候,小竹喝到有點二麻二麻的時候止住了,然后慢慢站起身來,撿起桌上的煙、打火機和手機揣進兜里,說:好,我走了。一般這種情況下,那個打火機都不是他自己的。在外面聚會時,他經常下意識地把桌上別人的打火機隨手揣進兜里, 回家掏一堆打火機出來。他很不好意思,下次聚會就揣一把出去,放到桌上讓別人取用。他說,下意識揣打火機的習慣可能是因為經常在家里怎么都找不到打火機,就只好開煤氣灶點煙。估計打火機真成了他的一個情結, 這幾年小竹做一個詩歌公號,推送很多詩人的作品,一周三更,相當活躍。這個公號就被他取名為“兩只打火機”。
很多生活中這樣的喜劇感, 都被小竹帶進了他的小說中, 尤其是早年的短篇小說集《女巫制造者》,這種喜劇感表現得尤為突出。后來這本小說經過修訂再次出版,改名為《女巫之城》。
小竹在“女巫”系列中所制造出的那種味道,飄蕩在成都這個城市的空氣里,并蔓延到其他城市。那些年,成都媒體、藝術、詩歌以及時尚寫作圈的女性聚會, 都有意無意地自稱或被稱為“女巫聚會”,這個稱謂雖不能說發端于小竹的小說, 卻被他強化了,又被“女巫”們自己所認同,于是也就傳播開去了。這幾個女性圈子互有交叉,關系盤根錯節, 但都和小竹有著友好且深厚的交道。
我不知道那種“味道”究竟該怎樣來描述,統而言之是巫氣,細細辨別一下,是清淡、恍惚、自戀、倦怠,是廢話連篇和妙語連珠,是瞬間的清醒和總體的迷茫,是郁悶和歡愉的穿插往來, 也是虛無和現實的相互搭救。這是一個族群的精神狀態和情緒狀態的寫真。如果非要延伸到什么主義上去,那就是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 還有一些浪漫主義。這話小竹不愛聽,他最怕“主義”,這個比較宏大的詞總是讓他皺眉頭。
其實,與其說小竹“制造”出了一種味道,不如說他“提煉”出了一種味道。這種味道是都市的、女性的、當下的,既鮮明又曖昧, 既養人又傷人, 既讓人向往又令人厭倦;它一直散發在女人的眉間嘴角,散發在成都的火鍋店和酒吧里面, 散發在一個個曲終人散意興闌珊的夜晚里, 它們像女人身上的香水、手中的煙和杯中的酒以及愛慕發生時的荷爾蒙氣息一樣,散發開去,然后,被小竹捕捉并描述出來。
在《女巫制造者》之后,《潘金蓮回憶錄》《愛情歌謠》《藏地白日夢》《他割了又長的生活》等小說陸續面世,到了中篇小說集《動物園》, 小竹正式地向他的導師卡夫卡致敬。《動物園》所包括的四個中篇的四個場景——動物園、 排練場、 夜總會、 電影院——人的生存的無解和荒誕盡被他寄寓其中。
何小竹的敘述是平易隨和不動聲色的,就跟他本人的說話方式一樣。你可以輕松進入其作品隨意前行,但是,越讀越覺得有點不對勁, 卻又說不出在什么地方不對勁,且找不到任何邏輯破綻。這種情形有點像一直覺得有人在后面跟著你, 但你每次回頭,背后都空無一人。直到你真的看到面前有了一個從后面投射過來的影子, 一切為時已晚,一張荒誕的網,已然兜頭罩下。
何小竹集成都男人的優點于一身,卻幾乎沒有成都男人的缺點。成都男人的優點是溫存、風趣、有分寸和負責任;缺點也很明顯,懶散,無厘頭,慣于遲到。我們見慣了身邊將這一好一歹結合在一起的成都男人, 小竹近乎完美的為人便有令人驚奇的效果——男男女女要想在背后說點他的壞話,仿佛是一樁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一般來說,不招非議的人都是很悶的,但小竹全然不是,他的幽默感幫他從“好人皆悶蛋”的模式中解脫出來。我們說不了他的壞話,但可以說他的閑話,然后把這閑話再說給他本人聽。他聽了,呵呵一笑,然后,寫到小說里去了,一點也不浪費題材。
小竹最新的作品是自選詩集《時間表:2001—2022》,這部詩集的時間跨度是二十一年,從他三十八歲到五十九歲。這部詩集之后,始終保持“凍齡”容貌的小竹也即將邁入通常意義上的老年了。厚厚的《時間表》, 是一部十分美妙的令人恍惚的作品,我讀這本詩集,一路很多的莫名其妙、莞爾一笑、若有所思、黯然神傷,這種層層堆積的閱讀體驗,讓人一言難盡。
有一天, 我從小區的菜鳥驛站取了快遞走出來, 見朝左邊的路上走著一個背著背篼的男人,正是小竹。他在網上買了一個背篼,用來取快遞用,偶爾也背著它到小區門口去買菜。這個背篼說來也是他的一個看點,看起來有點滑稽,但仔細一想,真是很實用。那天他背著背篼,手里還拎了一個塑料袋,慢慢走遠了,我沒有喊住他。那袋東西,圓圓的,有紅色透出來。我想了一下,可能他是先到小區門口的菜市場買了菜,然后再到菜鳥驛站取快遞。那袋紅圓的東西,多半是番茄,也有可能是蘋果。就是蘋果吧。
早年, 小竹有一首詩,《夢見蘋果和魚的安》。李中茂以此為題畫了一幅油畫。在《時間表》里,我又讀到了一首蘋果——
能有一只蘋果放在那里
我已心安,吃不吃已無所謂了
所以才有這一次時間的放棄
以便它在所有的時間
都散發出誘人的芳香
所以,對我來說
蘋果永遠是一個隱喻
其實,何小竹并不喜歡吃蘋果。什么水果,他都不喜歡吃。
二
2024 年5 月8 日的夜晚,玉林的白夜花神詩空間擠滿了人, 半城的熟人都到場了。“時間表:2001—2022——何小竹詩歌繪畫展”開幕。這一天,是白夜二十六周年生日,也是何小竹的生日。
熟悉何小竹詩作的讀者, 都對他精準捕捉日常瞬間的能力印象深刻。這些瞬間,在何小竹的筆下呈現, 總是帶著一些詼諧的荒誕和難以言說的況味,于是,讀者也總是可以從中觀照到自己的日常, 獲得一種莫名的慰藉。
何小竹的詩,對景物、事件、細節、氣氛、情緒、心境的書寫,似乎是一種結結實實的記錄。但在持續閱讀之后,人們又會有一點疑惑:這種很像現實的詩,真的是現實嗎?會不會僅僅“可能”是現實?“仿佛”是現實?
讀到一定的時候一定的體量, 比如閱讀《時間表:2001—2022》這部詩集,到后來,就會恍然大悟——
它們跟現實很像,但其實并不是現實,那一絲虛空,或者說那一點扭曲,就是詩。而拿捏住這種微妙之所在, 就需要憑借詩人的才華、見識、境界,還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淬煉出來的手藝。
這些難以察覺但又能確實感受的虛空點和扭曲度,究竟在哪里呢? 這一次,我們似乎可以通過“時間表”這個詩畫展一窺究竟。
何小竹的油畫作品, 與他詩句中經常攜帶的淡定、茫然、無奈、恍惚、失焦以及些許的欣喜和微微的苦澀……有著契合度很高的對應,它們都被埋藏在畫面之中,又從畫面溢出。詩與現實之間的那一點錯位,在何小竹的畫里, 也許就是那些模糊的筆觸和色塊。
關于詩作中我很喜歡的那首《蘋果的隱喻》,何小竹創作了兩幅畫:邊緣模糊的圓形的綠色塊, 一個沒有面孔的人與桌上的一個青蘋果對視。這些表達,都相當到位地與詩的氣息鏈接在了一起, 同質效果十分明顯。在我讀來,詩與畫各自的創作邊境是開放的,也就是說,我可以由畫走到更多的話語形態之中, 也可以由話語形態想象衍生出更多的畫面內容。
對于何小竹來說,在用繪畫對應(而不是闡釋)他的詩的時候,有著不同角度的尋找。有好幾首詩,他都用了好幾幅同題畫來對應,《蘋果的隱喻》有兩幅,《暗號》有四幅,《屋頂花園》有三幅,《回頭草》有五幅,《隱》有四幅……詩人/藝術家對一個主題的反復呈現, 表明了詩作內涵的豐富性觸及了繪畫創作的興奮點, 衍生出了更多的方向和角度。但是,對于讀者/觀眾來說,如果把一首詩的四幅同題畫僅僅理解為四個角度四個層次四種情緒, 那就是對欣賞與闡釋的雙重設限。
在何小竹這里,詩與畫,呈現著各自的秘密,它們相互回應,但不能相互覆蓋,兩種藝術形式可以彼此轉化, 但不能彼此替代。作為著名且資深的詩人,何小竹在轉換另一種表達形式時,選取這樣的繪畫語言,想來是自然,也是必然。在閱讀“時間表”這個畫展時,如果把詩作為畫的解讀,或者把畫作為詩的注解, 這樣固然會使我們感到比較輕松便捷, 但是同時也很有可能就錯失了另一種深入且有趣的結構和景觀。
何小竹的詩和畫, 它們并不是對方的“灰色空間”,而是彼此獨立、其間有一條廊道相連的兩個建筑空間。
責任編輯:施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