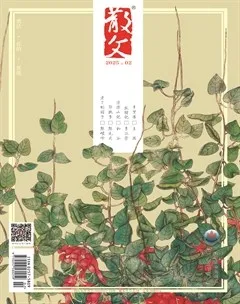麻煩的盡頭·風爐

風爐是逆現代化的。在有一個靠山且經常有風的陽臺后,我放了一只風爐,煙火通神明, 試圖在真實生活中做個與各種概念之“道”相接的實驗。
實驗的前奏,是一小段現代文明贊歌,感恩現代化和城市文明的優越, 一位女性能選擇逃離, 嘗試獨自擇山而居的生活方式,其根本是時代發展之福利。有足夠的縫隙容下不同的活法,有淘寶、拼多多和美團這些服務體系支撐, 才敢放個風爐在陽臺上當起各種改良版微型田園復古人士——如果真在燒炭燒煤時代, 我定是積極推動燃氣化和電器化的新派分子。把風爐從過時的日常器物中提取出來, 讓生活重新染上炭火味,自有樂趣,但真回到農業時代去伐薪燒炭,又未必是樂事,最好還是兩邊的便宜都占著。
麻煩的盡頭是宇宙萬物都唱起歌
風爐的稱呼源自茶圣陸羽, 是炭爐在茶領域的專用說法。因為跟茶沾邊,做得比一般炭爐要精致小巧一點。從廚房粗器到茶室雅物,實現了階級躍遷,也是因為茶,在智能掌管一切的未來, 作為一種精神與文化,相信它依然會有一席生存空間。在學喝茶之初,我徒有附庸風雅的心,跟著裝備黨買過一次風爐, 一用就嫌。此物十分麻煩,沒有生火技能,也缺乏扇風待火慢慢把水煮開的耐心,煙火氣弄不好,就是煙熏火燎。于是很快就放棄了,轉手送人。就像當年炭爐煤爐退出生活一樣, 沒人會留戀它們,電水壺是新文明,象征急切的心奔赴干凈便捷的現代化生活。
真到了以茶為命的時候, 麻煩與便捷之戰便不再勝負分明,不厭其煩,反而是茶道之精髓。逐漸形成了幾套喝茶的水火方案:工作或外出中用保溫壺燜茶最為簡單,有只保溫壺就行,機場、高鐵及各種長途,燜上熟悉的茶葉, 就能迅速用茶布下一個私人的結界;不忙但怕麻煩時,就先用電水壺燒開, 再倒入陶壺放置電陶爐上小火保溫,有效保留了電力時代的便捷;不忙且想認真喝一道茶時,就燒戶外燃料罐,打火機點燃即得小火苗,麻煩的是,最好陸續少量多次添水,不然就得跟客人聊天,打發等水開的漫長時間。在一些茶友眼里,明火煮水才算得上一點樣子, 但現代燃料還是不道地的次級方案。
橄欖炭、風爐和青篾扇,適合在不忙不急泡好茶時出場。要有回到原始人的耐心,重新學會和火打交道。
燒火技能大規模消失已經三十余載了。炊煙裊裊消失在田野和竹林掩映的青瓦屋頂,若不是茶道復興,是很難有機會以手忙腳亂的方式去直觀體會這種煙火氣的。火勢確定要壯大時通透舒展的煙味,和欲燃未燃的煙味是不一樣的。伴隨著輕微的噼啪聲,你知道這火被你控制了,你站在了文明的源頭,養護著光明與溫暖。
最好用的是潮汕沙銚, 輕薄的胎體和四百五十毫升左右的大小, 是多少代潮汕人的選擇。水開的時候,蓋子會在恰好的范圍內跳舞, 火勢控制升騰的水汽剛好讓蓋子以一定的節奏掀起又落下, 在細小清脆的咔嗒聲和氣鳴里, 心里滿是無憂無慮的溫柔和誠懇。
這樣大費周章起好的炭爐子、茶、器和態度,都隨之調節至和諧的配搭,所有程式化和儀式感都有了底氣。我無條件尊重能夠有條不紊控制爐火的人; 遇著陰雨濕冷的天氣,煮上一壺茶,炭火燃燒的香味若有似無,清透穿透綿密,對潮濕有著四兩消千斤的神力。溫暖變成一種干燥的嗅覺。茶是老白茶或老熟普,經文火慢煮有粽葉香氣,喝一口暖至小腹,里里外外融而化之,六感六識全開, 就能懂得何以茶能帶動那么多事物飛躍階級。是雅,是空,一切玄妙起來,再拔高到精神能量和生命境界, 也說得過去,發輕汗、毛孔散的狀態下想象肌骨清和通仙靈也不難。如有幸得到二三子共飲,也最好正處于令人愉悅的靜謐默契中——唯是這樣,才能聽到宇宙萬物都在唱歌。
陸公的文化教材
茶桌諸事,講究起來沒有天花板。茶與茶器、泡飲程式、審美文化、修行境界……每個維度都可通往無限, 得益于茶圣陸羽把起點和基礎做得踏實, 細節清晰又出塵清高。他在《茶經》里詳列了喝茶要用的二十四器,是相當成熟的茶文化原點,由此輻射向整個東方世界。
其中第一件,就是燒火用的風爐,然后是裝炭用的筥、碎炭用的炭撾和夾炭用的火筷。跟人類原始文明一樣,解決火的問題是一切的基礎。畢竟到唐代了,火已被馴化至乖巧,灶火燈火窯火都是尋常人間煙火,冶煉業不僅生產出制作精致爐子的金屬,還刺激了燒炭業的發達, 爐子鑄造技術也是熟練的, 可以支持陸羽這樣經典知識分子的造器思想。
陸羽對風爐寄予厚望。爐型取自古代青銅鼎,他的古代,特指夏商周三代,也是儒家知識分子的精神原鄉, 從孔子起就代表著對正統、理想世界的追崇,連帶著對三代青銅器也有了根深蒂固的膜拜。
北宋士大夫呂大臨說這種對青銅器的崇尚是“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以求“觀其器、誦其言,以意逆志”,萬萬不敢視之為玩物。唐代的陸羽作為前輩,思想反而更自由開闊,懂借鑒活用,既把今人帶回到古代,培養崇敬之心,又將古代文化品位納入當下,得生活之樂趣。儒家士子素來被嫌棄過于拘泥古板, 這些有生活小愛好的則例外,著力小事物,也能解放創造力和藝術生產力。
風爐通常由銅、鐵或者揉泥制作而成,關于里外尺寸, 如何尊重空氣動力學開口開窗,營造炭火燃燒環境,在唐代是基礎技術。陸羽的文化水平,主要體現在他刻在風爐上的字詞和圖案紋樣。風爐三只腳上分別是“坎上巽下離于中”“體均五行去百疾”“圣唐滅胡明年鑄”,三個窗口上分別是“伊公”“羹陸”“氏茶”, 還有爐口被凸起的垛,被分為三格,分別畫著野雞、彪和魚三種動物。能畫能寫的地方都有內容,解讀起來要動用諸多易經八卦、中醫五行與歷史典故,硬生生地把一只爐子做成了傳統文化教材。
“圣唐滅胡明年鑄”是交代時間,也就是安祿山之亂平定的次年。盛唐昂揚多彩的大環境正在衰退,當時陸羽二十九歲,懷才不遇, 常常一個人獨行野外游山玩水讀佛參禪,“自曙達暮, 至日黑興盡, 號泣而歸”——自傳里寫的是每每玩到天黑,忍不住哭泣。“伊公羹、陸氏茶”六個字,暴露了這位茶人希望能憑著茶藝實現政治仕途上的愿望, 跟借調羹術成為一國之相的商代大廚伊尹一樣。結果,陸氏茶的影響力并不在朝堂,而是把陸羽送上了“茶圣”的寶座。一千多年下來, 茶的種類和泡飲方式一直在變,但追根溯源,誰都繞不過他。
“坎上巽下離于中”幾個字和魚、彪、野雞圖案,對應著水、風、火幾元素,意思是風能興火,火能燒水。“體均五行去百疾”一句又說到了五行和健康的關系, 木火土金水在風爐中可以簡單地看作是:金屬做體,泥土在內,以木生火,火再煮水。茶事在燒水環節就已經五行俱備了, 跟天地自然和人體相呼應,如此都兼顧到,則可以治百病。道理是對的,古代人對“去百疾”是執著又濫用的期待,倒也不必太過當真,但作為一種制器思想,不把這點加上也是不完整的。
風爐小巧有文化,讓火變得自由,可隨身攜帶,從書房到門廊到戶外,茶席在哪兒都可以布置起來了。于是在古詩古畫中,我們可以看到松下有爐,溪邊有爐,夏日竹風中有爐, 冬日雪亭中有爐……跟廚房里的灶火不同,風爐進入生活趣味和精神世界,可陪人度過漫漫長夜,是溫暖的陪伴侍從。
《小窗幽記》中說:“寒坐小室中,擁爐閑話。渴則敲冰煮茗;饑則撥火煨芋。”識字的中國人都能從中讀出向往之心來。“煨”是一個跟著柴火炭火淡出生活的烹飪方法,把食材直接放在帶火的灰里慢慢燒熟,也叫“煻煨”,紅薯、山芋、板栗等用這種簡陋的食法說不上哪里好,就是有滋有味,能同時吃到一種安慰。無論烤箱、空氣炸鍋還是電燉盅,都不會理解這個“煨”字的余燼溫柔。同樣的電磁爐電陶爐在拼市場占有率的時候,風爐卻不愿意降低使用門檻,要求閑心、耐心和熱情俱備,然后才回報一點打折的溫暖,畢竟它的理想環境——雪夜、山溪、松竹之風以及其他二十三件茶器搭檔, 現代人想要集齊它們, 也實在是太難了。
我身體和精神里的炭火元素
風爐文化能傳承下來, 還要感謝潮汕人,他們是我見過最能喝茶的族群。在來廣東之前, 我看到的喝茶方式就是抓一把茶葉放進杯子或者大水壺里,管半天。有些老爺爺喜歡用小壺直接對嘴喝, 或者是從電影里獲得的遺老遺少的經典印象, 后來保溫杯橫掃過來, 以絕對的優勢成為新的主流。
潮汕人更新了一個湖南人對茶的認知。他們到處開店、開公司和開工廠,無論大大小小的老板, 無一例外地都有自己的茶臺:或是極占空間的大樹根款濕泡臺,或是柜臺角落一個圓形小茶盤, 上面小壺小杯大同小異。蓋碗神技是他們從小就掌握的,似乎人人手指都變異出了免燙神經,滾燙的開水絲毫不影響他們動作的絲滑優雅。“韓信點兵”“關公巡城”是人人都掌握的程式動作,已經化為肌肉記憶,九位數的生意談判也不耽擱手中茶水紛飛。燙壺燙杯,投茶洗茶,不動聲色地一個細節都不落下,沖出來的單樅茶極濃釅。
若是用風爐燒水, 一杯茶經過繁復的程序喝到嘴里不容易,也就容不得牛飲,人也不免收斂客氣起來。有幾年在深圳做城市生活類周刊的記者, 常走訪潮汕老板密布的茶葉批發市場、餐廳、大排檔,以及著名的華強北電子批發市場, 發現他們幾乎都有這樣的泡茶裝置,我稱之為“廣東地區潮汕籍中小企業家款”。大部分包括能夠顯示溫度、自動抽水的電水壺和不銹鋼煮茶盆套裝裝置,小部分是一只潮汕泥風爐,堅持用炭火——最佳搭檔是橄欖核炭和側把沙銚——又名玉書煨燒水。 用孟臣款小壺或小蓋碗,茶葉塞滿,開水倒進去再輪流注入三小只茶杯,壺空杯滿天衣無縫。
飯一天最多三頓, 茶可一天都要喝無數道。潮汕人自幼就習慣了圍繞茶桌的生活,早早就能把壺和蓋碗用到飛起。頗有族群辨識度的為人處世哲學、家庭觀念還有做生意的習慣, 就這么隨著喝茶習慣一起內化了,影響不比九年義務教育小。
如果你現在下單一個風爐, 大概率是潮汕泥爐, 可能也只在這個地區小炭爐還算民間用器,唐式的、日式的,是更小眾的領域。我第一只常用的風爐是朋友嫌在室內生炭火過于麻煩而轉送的,潮汕簡易款,沒有陸羽式的高足和銘紋。一年后去她家,發現又有了三只, 依然包括更為精致的潮汕式,還有柴窯土陶款,以及配煮茶側把碗的專用款, 且為了方便點火又配置了起炭器。我們起炭火用銀壺煮水,安排三個茶的順序,茶器排兵布陣一般,出將入相,絲毫不覺麻煩,反而有一切可控的安慰,獲得了很稀缺的情緒價值。好像就是從那天起,風爐和炭火,連接上了上千年的生命力,被植入我們的習慣, 我們開始認為事情本該如此,不會被輕易淘汰了。
在潮汕工夫茶之外, 時下流行的茶席美學深受臺灣人文茶道影響, 一批新茶人成型后開始自由連接各地風物, 茶桌器皿有新有舊,建盞、青瓷、白瓷、柴燒,鐵壺銀壺,非遺手工、日式舊物……無論是窯口產地,還是復古工藝,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盡可以自由調度,有各種選擇,大套裝的茶器淪落到鄙視鏈下游,有風格的配搭成了樂趣和品位的建構——這種不厭其煩折騰生活的勁頭與姿態以前也是有過的,比如有《長物志》誕生的晚明。風爐穩扎穩打下來,又成了高端新寵。
傳統器物要跳出文化象征符號式的羈囿,破局的關鍵是親身體驗和日常生活,身心感受將我們帶回到它們所屬的那個世界——有實實在在的勞作、 消費和享受的時代。經歷了野蠻求生的時期和快捷方便的現代化,土地豐饒然而疲憊,莊稼不必努力然而迷惘,被大數據們討好著,生命反而不知該如何是好。于是在陽臺上起一爐炭,也就有了對抗的含義,不一定是陸羽歸來,也不一定煮茶,烤個建水豆腐、紅薯玉米也完全可以, 像風雨夜的原始人守著火堆和食物,倒可爽快定性為靜好時光。溫暖和安全感是人類基因里最原始的依戀, 這種本質需求最好加上文化的“無用性”來調味,趣旨和意義就更加深遠了, 所以別問潮汕的民用泥風爐門口為何還要配上兩句“茶聯”,這是把麻煩和文化重新引進來,正是這些非必要甚至無用之事, 讓我們樂此不疲,也從中構建與生成了一個更完整的“我”。
責任編輯:施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