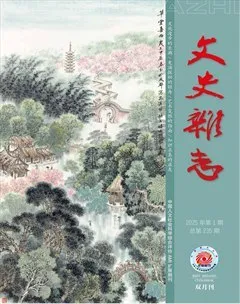古蜀文化區當為中華文明起源類型的一大板塊



摘 要:古蜀之“蜀”早在漢代文獻里就有明確記載。從營盤山文化開始,古蜀文化便有了一個鮮明的發展脈絡。惜乎以往的一些學者忽略了其“自我”的一面,在劃分史前文化區時,或漏劃,或將其視為不可感知的“他者”形象,或將之與巴文化同列入一個類型。其實巴、蜀兩族各有自己的成長背景與發展路徑。在他們的文化秉性中,異質性要多于同質性。就蜀文化而言,是一個富有創造性、創新性的原生性質的文明。所以將古蜀文化區單列為中國史前文化的一大區系,很有必要。
關鍵詞:蜀;營盤山;文化區系;異質性;自成一系
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的三四十年間,以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為代表的古蜀文明(屬長江上游文明)的考古學面貌逐漸清晰起來。這是一個在自成單元的特殊地理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新石器文明和青銅文明,又是一個極富創造性與創新力、特點鮮明、有別于長江中下游文明和黃河文明的古城—古國—方國文明,也是一個能接納四方、熔鑄萬象的復合性文明。按照考古學的基本原理和歷史邏輯,理應將古蜀文化區單列為中華文明起源類型的一大板塊。
一、古文獻中的“蜀”
說到“蜀”,無論就族名還是地名、國名而言,幾乎所有的工具書對該字的釋義都指向四川,所以,人們一見到古代文獻和考古材料中的“蜀”字,多會聯想到在四川地域的古蜀國。
甲骨文自1899年被發現以來,已出土15萬余片,其中出現有許多“蜀”字,寫法各有不同,孫海波先生在《甲骨文編》中列出20種;高明先生在《古文字類編》列出4種;徐中舒先生主編的《甲骨文字典》列出9種。有關“蜀”的甲骨卜辭,姚孝燧先生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里也列出了67條,其中還包括僅有一兩個字無法確定其內容的卜辭。
應該說,甲骨文中的“蜀”,絕大多數都是地名,但多在今四川之外,如《逸周書·世俘解》中的河南新鄭西南之“蜀”,《左傳》“宣公十八年”“成公二年”中的山東泰山附近之“蜀”,周穆王班簋銘文“秉繁、蜀、巢”所指的安徽巢湖之“蜀”;山西、陜西也還有叫“蜀”的地方。
《逸周書·世俘解》記載武王伐紂,牧野之戰得勝后四個月時間里發生的事情,講周人攻取殷商都城后,繼續剿滅不肯順服的諸侯國:“……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蒙文通先生就此指出:“蜀在梁州,梁州以外還別有個蜀。《逸周書·世俘》說:‘庚子,……新荒命伐蜀,乙巳,新荒蜀歷至,告禽’。從庚子到乙巳,不過五天,往伐蜀的將帥就回來了。這顯然不是梁州的蜀,而是距離牧野不遠的蜀;也就不是從武王伐紂的蜀,而是與紂同黨的蜀。這必然別是一個蜀。決無剛剛敗殷于牧野的幾天之后,就來伐自己伙伴的道理。”[1]
古史文獻明確以“蜀”指代今四川地域者,最早見于西漢賈誼(前200—前168)的《過秦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稍后司馬遷(約前145或前135—?)《史記·楚世家》有:肅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茲方。”又見《史記·秦本紀》: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25年),“伐蜀,取南鄭”。(按,《華陽國志·蜀志》則載:“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褒、漢即褒中、漢中。漢中即南鄭)惠文君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司馬錯伐蜀,滅之”。再如劉向(前77—前6)編《戰國策·秦策一》:“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
蒙文通認為,古蜀人是由岷山河谷發展到成都平原的。“江源、臨邛正是岷山河谷,蜀的文化可能是從這里開始的”;“成都平原反是第二步的發展”。蒙文通還指出,巴蜀的文化自古就很發達,其并非始于文翁興學;在文翁之前,天文歷算、黃老、詞賦就已成為巴蜀古文化的特點。[2]蒙文通的這些觀點,為后來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所逐步證實。
二、從營盤山開始的古蜀文明
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西北部茂縣發掘了營盤山遺址,其年代約在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600年。考古工作者在這里發現了大型的中心聚落,密集的房屋基址及多座人殉坑,所出文物包括四川地區發現的最早的陶質雕塑藝術品,國內發現的時代最早的人工使用朱砂的遺物,長江上游地區發現的時代最早及規模最大的陶窯址等,彩陶出土數量亦為四川之最。營盤山遺址地處岷江上游東南岸三級臺地,是古羌人從大西北南下成都平原的中轉站,也是古蜀人心心念念的一處故鄉。它也因此成為弄清古蜀族形成、遷徙、交融,以及黃河上游與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聯系的鑰匙。
約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600年的什邡桂圓橋文化是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器考古學文化遺存;約在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1700年的寶墩文化則處于古蜀文明的古城—古國—方國的早期時候,也是古蜀文明的初起階段。(營盤山文化與桂圓橋文化可視為古蜀文明的先聲。)寶墩文化遺存即為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1995—1996年發掘的新津寶墩古城遺址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城址面積60萬平方米左右(外城面積276萬平方米),為雙城墻結構,是繼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陜西石峁、湖北石家河之后發現的國內第五大新石器時代遺址,也是我國西南地區龍山時代最大的城址。它與都江堰市芒城遺址、崇州市雙河遺址和紫竹遺址、郫都區古城遺址、溫江區魚鳧村遺址、大邑縣鹽店古城遺址及高山古城遺址等7座史前遺址共同形成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城址群。其考古文化時代相當于三星堆遺址的第一期(約距今4500年至3600年),所筑城的面積10萬—60萬平方米不等。這些城址大多選擇在河流臺地上,沿河流方向平行修筑。各個城址都有高聳的土筑城墻,有的還有寬大的壕溝。城址具有明顯的防御功能,也可能與治水有關。
2014年在成都市溫江區紅橋村附近的寶墩三期遺址發現的水利設施,護岸堤由泥土夯筑,臨水護坡用卵石堆砌;護岸堤上有8道人工開挖的溝槽,內有密集的柱洞,為安插木樁所留,起加固作用。寶墩遺址的水利設施,在時間上與傳說中大禹治水的年代相當,而比李冰的都江堰工程要早約1700年。后者應該吸取了前者的經驗。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治水經驗,古蜀人才得以先后在廣漢三星堆,在成都金沙、十二橋立住腳跟,發展壯大。“水利是生命之源,是興國之本;善治國者必先治水”——古今皆然。
從營盤山文化開始,古蜀文明便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演進面貌,表現為:上承黃河上游馬家窯文化(公元前3700年至前2050年)而來的營盤山—桂圓橋文化(公元前3300年至前2600年)→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為支撐的寶墩文化(公元前2600年至前1700年)→以三星堆遺址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公元前2500年至前900年)→以金沙遺址和十二橋遺址為代表的十二橋文化(公元前1700年至前500年)→以成都商業街船棺葬、獨木棺葬及“成都矛”為典型器物的戰國青銅文化(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316年)。公元前316年司馬錯伐蜀,成都平原及川西北高原的古蜀文明迅速融入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大格局,在此后一個較長時期(直至兩漢之交)仍在大中國的西南一方熠熠閃光。
三、幾個史前文化區系
不用說,古蜀文明自有其鮮明的發展脈絡。盡管它的包容性(屬中華文明五大特征之一)極強,熔鑄八方文明為己所用,但是,其獨立生成、獨立發展與創造性、創新性的特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其對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進步所作出的努力與貢獻是史有銘記的,如三星堆大型青銅立人像、青銅神樹、青銅神壇,金沙太陽神鳥金箔飾等。然而,過去一段時期,學界對此的關注度與之并不匹配,甚至避而不談;或將之視為不可感知的“他者”(即未被明確記錄或未被充分認識的存在)形象,而忽視了其“自我”的一面。
(一)蘇秉琦的“六大區系”
1981年,蘇秉琦與殷瑋璋在《文物》1981年第5期聯合發表《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一文,率先提出中國考古學的區系類型學說。蘇、殷二先生把考古學文化分成三個層面來理解,即區(塊塊)、系(條條)、類型(分支)。他們把中國大地上的史前文化劃分為六大區系:
1.陜豫晉鄰境地區;2.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3.湖北和鄰近地區;4.長江下游地區;5.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地區;6.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在這里,蘇、殷二先生并未將四川地區納入其六大區系。當然,這似乎也可以理解:因為在蘇、殷撰文之前的四五十年間,蜀地只在20世紀20年代于成都西門白馬寺見有青銅器(被人誤為“夏器”)出土;1934年對廣漢遺址進行了一次正式發掘,雖然引起過川內學界的一陣歡呼,并帶來衛聚賢等于1942年“巴蜀文化”命題的提出,但畢竟未造成舉國轟動的效應。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半葉以后,三星堆兩個“祭祀坑”(1986年)一醒驚天下,蘇秉琦也頷首稱贊,說:“現在已經抓住了蜀中考古的生長點。”[3]“蜀文化的生長點,就在這里。”他還把三星堆定性為“古文化—古城—古國”遺址。(1987年)[4]遺憾的是,蘇先生在臨終前完成的《中國文明起源新探》(1997年)一書里,雖然把四川盆地列入到六大考古學文化區系里,但卻是將其與環洞庭湖“捆綁”在一起。具體而言,即是:1.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2.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3.以關中(陜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4.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5.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5]
蘇先生說:“六大區并不是簡單的地理劃分,主要著眼于其間各有自己的文化淵源、特征和發展道路。這又集中體現于每一大區系中不大的歷史發展中心區域。”[6]對此,我們認為,就西南部而言,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不僅相距遼遠,而且文化屬性亦差別甚大:前者為楚文化,后者為巴蜀文化。當然,巴人與楚人關系要緊密些:不僅地域相鄰,而且文化相近——《下里》《巴人》就是在郢中(戰國時楚國都)唱響的。這兩支歌是巴人的歌。將巴人地區與環洞庭湖劃歸為一個中心倒是無話可說,但將蜀人地域也硬塞進來,便顯得有些唐突了。
蘇先生在《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里提出了著名的“滿天星斗”說。他認為,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在中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已經分布著許多不同的文化遺址(至20世紀70年代,僅新石器時代遺址便數以萬計)。這些散布在中華大地上的各具特色的史前文化猶如滿天星斗,不斷融合交流,相互影響,共同發展,最終形成中華文明的燦爛星河。
(二)嚴文明的“六個民族文化區”
與蘇先生史前文明“滿天星斗”說相映成趣的是嚴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論。他在《文物》1987年第3期發表題為《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的署名文章,從考古學的角度將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劃分為六個民族文化區,即中原文化區、燕遼文化區、甘青文化區、山東文化區、江浙文化區、長江中游文化區。后“五個文化區都緊鄰和圍繞著中原文化區,很像一個巨大的花朵,五個文化區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區是花心。各個文化區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時又有不同程度的聯系,中原文化區更起著聯系各文化區的核心作用。”“假如我們把中原地區的各文化類型看成是第一層次,它周圍的五個文化區是第二個層次,那么最外層也有許多別的文化區,可以算作第三個層次。……它們同第二個層次的關系較同第一個層次更為直接也更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個中國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個巨大的重瓣花朵。”
嚴文明先生的這篇文章,是參加在美國弗吉尼亞州艾爾萊召開的“中國古代史與社會科學一般法則國際討論會”時提交的論文,時間在1986年6月。彼時離三星堆一號祭祀坑的發現還有一個月。所以,嚴先生這時的“重瓣花朵”圖(即“中國新石器文化分區圖”)里并未單列巴蜀文化區,即便在“五個文化區”(屬第二層次,即第一重花瓣)外的第三個層次(屬第二重花瓣)里,也未見有四川的新石器文化。[7]
34年后,嚴文明又在《國學研究》第四十四卷發表《中國文明的起源》一文,重提“重瓣花朵”說。他認為:“花心是中原文化區,內圈的東、東北、東南、南、西南、西北和北部都自成一個文化區”。他接著歷數中原文化區、海岱文化區、燕遼文化區、江浙文化區、湘鄂文化區于新石器時期(包括龍山時代)走向文明的具體情況,但依舊不提西南方向文化區文明的生成與發展。不過,他在“龍山時代(約公元前2900年至前2000年)”題下還是列出了一段文字來談西南區的情況:
在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這時也突然出現了一系列環壕土城,包括新津寶墩古城、郫縣魚鳧城、雙河古城、都江堰芒城、高山古城和三星堆一期古城等將近十座。從出土陶器來看應該是受到長江中游屈家嶺文化的影響。那里河流縱橫,水網密布,有利于種植水稻。其中寶墩古城最大,外城近圓形,約300萬平方米,城內大部分是水稻田,中間的許多小土包當是農家房舍所在。內城為長方形,約60萬平方米。城內有宮殿式建筑,可見寶墩古城即是成都平原最初的都城。后來中心移到了廣漢三星堆,并發展出了高度的青銅文明。[8]
嚴文明先生其實是看到了寶墩文化與三星堆文明的實際面貌的,只是不知為什么并未于其“重瓣花朵”說里給予明白的地位,實在令人困惑。
(三)劉慶柱的“七大區域”
之所以會出現上述情況,粗略分析,不外以下三點原因:一是在1986年三星堆兩祭祀坑大發掘前,古蜀(或巴蜀)文化區的考古資料尚未達到“驚天下”的層次;二是爾后雖然有了大發掘,一些學者仍囿于舊識,并未予以特別關注;三是在如何劃分文化區系的問題上,側重于考古文化屬性,而忽略了地理特點與民族文化的特征。(按嚴文明先生雖以“民族文化區”冠名,實則未涉及民族文化的具體特征,只在字面上出現有“夷人”“東夷諸族”等詞匯。)
近些年,也有學者注意到這些問題,如劉慶柱先生在《中華文明認定標準與發展道路》一文里,便將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文化從空間上分為七大區域,即中部的中原文化區、東部的海岱文化區、西部的甘青文化區、南部的江漢文化區、東南部的江浙文化區、西南部的成渝文化區、北部的北方文化區。[9]
劉慶柱的“七大區域”的劃分顯然注意到文化區系的地理特點。但是他將成渝地區的兩種文化——巴文化與蜀文化拉扯在一起,卻未注意到它們在民族學屬性上的分野。
四、巴蜀兩文化的異質性
其實,從總體上看,先秦時期的巴國與蜀國并不是兩個友好國家,巴文化與蜀文化的異質性要多于同質性;至少在秦統一巴蜀前,四川地區不存在渾然一體的巴蜀文化。
巴人的主體民族最先活動于長江中游,于清江地區的今湖北恩施立國建都,后來發展到今四川地區的中東部。他們在夏商時期稱為巴方,納貢服役,始終是中原王朝的附庸。在商朝末期,巴人參與了周武王伐紂戰爭,前歌后舞,表現勇猛,被封為巴子國。《華陽國志·巴志》說“封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從此巴人就因這個宗親關系與周王室綁縛在一起。
蜀人的祖先在主體上是古羌人的一支。他們較早從華夏文化中分化出來,與匯聚蜀地的其他民族一道共同創造了與中原文明大相異趣的古蜀文明。
《華陽國志·蜀志》也講過黃帝族“封其支庶于蜀,世為侯伯,歷夏、商周”,但那是漢晉人的偽托。蜀人的先祖就是從大西北通過岷山河谷來到成都平原的。他們歷經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五個時期(可能為部族—古國—方國時期),諸王嬗替,脈絡清晰。他們的蜀國始終不是中原王朝的附屬諸侯國,不向當時的中原王朝納貢,這一點與巴國有顯著的區別。歷代諸蜀都保持獨立的身份。所以在古籍中,有“巴方”一辭,卻沒有“蜀方”一說。
就新石器考古文化而論,龍山時代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與重慶地區的中壩文化(分別為兩地新石器晚期文化的代表)也有很大區別:前者馬家窯文化—營盤山文化的因子多些,后者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因子多些;前者陶器多盤口或敞口圈足尊,后者陶器多盤口罐、圈足或假圈足碗、折腹缽等;前者一般為仰身直肢葬,后者主要是屈肢葬;前者以稻作農業為主,后者以黍粟農業為主;前者擁有龐大的城池群和大型木骨泥墻建筑,甚至擁有大型的禮儀性建筑——廟殿(或用作宗教祭祀),后者文化聚落較小,社會復雜化程度不高;前者即將邁進文明社會的門檻(或說已進入文明社會初期);后者在由新石器文化向青銅文化轉變上則慢了一個節拍。
《華陽國志·巴志》說:“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是說沿江一帶一半是楚人,楚對巴的影響,不僅表現在文化上,還表現在人口互動或交流上。《華陽國志·巴志》又說,巴東“郡與楚接,人多勁勇,少文學,有將帥才”;又云:“巴有將,蜀有相”。這是說,巴人性格剛烈、熱情奔放、果敢忠義、重然諾、輕生死,故多出軍將;蜀人性格溫和、典雅含蓄、頭腦機敏、多禮尚文、喜游樂、重飲食,遂屢見佐相。又或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實是巴人講的話。巴楚從來是一家。巴與楚的關系好過巴與蜀的關系。巴國有亂便向楚國借兵,如巴蔓子,這是信任使然。巴蔓子戰后未踐承諾,便以死謝罪,巴、楚兩國皆以上卿禮葬之,這是忠義同感。所以巴文化或可納入楚文化的范疇。巴文化與蜀文化的差異其實也是長江中游古文化與長江上游古文化的差異。不過,由于巴、蜀兩國疆域相鄰、犬牙交錯,勢必相互影響,所以兩個地域或兩個民族的文化在異質性外也還有同質性。這便導致“巴蜀文化”命題的產生。即使如此,巴人與蜀人仍然頑強地保留著大相迥異的文化傳統。諺云: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巴文化所處地域以大山大江為主,其秉性便剛強豪爽;蜀文化所處地域多為平原淺丘,溝渠密布,其性情則溫婉包容。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公元前316年秦統一巴蜀后,在此地分設了巴、蜀、漢中三郡,由此導入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政治體系。巴、蜀間彼此更多的是聯系與交流,不再敵對,同質性日益增加,所以,巴蜀地區在秦漢時期強勢崛起的文化才算得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洽互融的巴蜀文化。
只是,當重慶在1997年脫離四川成為直轄市后,那里的許多學人就不再提巴蜀文化而自個提出“巴渝文化”。這便將蜀文化與巴文化原先在民族學屬性上的異質再度凸顯出來,決絕地與往昔的情分“斷舍離”,真令人無語。
五、自成一系的古蜀文化區系
應該說,蜀文化與巴文化在考古學上、民族學上的差異畢竟客觀存在。它們各有自己的地理環境、成長背景及民族秉性,各有自己的文化淵源、發展路徑與創造性、創新性。就蜀文化而言,從根本上看,乃屬于由川西北高原孕育、在成都平原生成和成長起來的原生性質的文明。以寶墩文化為代表的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文明以及以三星堆—金沙文明為代表的川西地區令世界震撼的青銅文明給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浩瀚星空平添了一份輝煌。所以三星堆與金沙遺址有足夠的自信去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就連提出新石器時代“六大區系”(未曾單列古蜀地)的蘇秉琦先生也承認:“我確信,成都及其附近幾縣從距今五千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至距今三千年前存在著自成一系的古蜀文化區系。”[10]蘇先生是1984年在成都講的這話。那時他在博物館的庫房里“看到了真正的‘古蜀文化’”[11],因此頗生感觸。
總之,為還原歷史的本真、理清古蜀文明面貌與發展脈絡,以便更為科學和有力地推進中華文明的國際傳播,亦為便利學者研究的暢達、治學的深入,將自成單元(無論從地理環境、發展脈絡、文化性格、歷史貢獻來看,皆自成一系)的古蜀文化區單列為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的一大文化區系、或者說中華文明起源類型的一大板塊,是有必要的,也是不成問題的。孔子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誠哉斯言!
注釋:
[1]蒙文通:《巴蜀古史論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頁。
[2]參見蒙文通:《巴蜀古史論述》,第78頁、80頁、98頁、103頁、106頁、111頁。
[3][4][5][6][10][11]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84頁,第83頁,第35頁、37頁,第38頁,第83頁,第83頁。
[7]參見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物》1987年第3期。
[8]嚴文明:《中國文明的起源》,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第四十四卷,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21頁。
[9]參見劉慶柱:《中華文明認定標準與發展道路》,王巍等:《溯源中華文明》,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3年版,第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