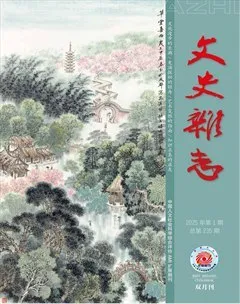民國初期川滇黔省際張力格局與“孫熊之爭(zhēng)”

摘 要:在護(hù)法運(yùn)動(dòng)期間,孫中山與滇系軍閥唐繼堯聯(lián)手,對(duì)同為國民黨人的四川督軍熊克武開展“倒熊”戰(zhàn)爭(zhēng),致使護(hù)法陣營同室操戈。“孫熊之爭(zhēng)”的根源在于民國初期的川滇黔省際張力格局,代表四川本地勢(shì)力的熊克武與滇黔客軍之間的矛盾難以調(diào)適。孫中山致力于在四川開拓護(hù)法基地,并因護(hù)法陣營內(nèi)部紛爭(zhēng)而選擇聯(lián)滇制桂。這便決定了孫中山在川滇黔張力格局中的站位,從而導(dǎo)致“孫熊之爭(zhēng)”無可避免。
關(guān)鍵詞:熊克武;孫中山;唐繼堯;護(hù)法運(yùn)動(dòng)
1905年7月,剛滿20歲的四川青年熊克武痛感于“清廷腐敗,列強(qiáng)侵凌”,毅然東渡日本,向?qū)O中山誓言“愿意聽從先生的指示,準(zhǔn)備隨時(shí)為革命效力。”[1]此后,熊克武馳騁四川軍政舞臺(tái)凡二十年,自認(rèn)為“都是秉承中山先生直接命令”[2]。學(xué)界肯定熊克武是孫中山的忠誠戰(zhàn)友,并言及他在護(hù)法運(yùn)動(dòng)中“對(duì)穩(wěn)定四川局勢(shì),使人民一度得以休養(yǎng)生息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3]。
然而正是在護(hù)法運(yùn)動(dòng)期間,孫、熊二人漸生齟齬,以致孫認(rèn)定熊“于救川救國之計(jì),根本不能相容。”[4]親歷者朱德將熊克武稱作“一度曾是革命派的人怎樣轉(zhuǎn)變成為軍閥”的“X號(hào)標(biāo)本”。[5]“孫熊之爭(zhēng)”固然是近代中國民主革命“褪色”的表征之一,但要揭示革命蛻變的深層次動(dòng)因,還需明晰護(hù)法運(yùn)動(dòng)前后的“川滇黔省際張力格局”以及時(shí)勢(shì)中人的因應(yīng),亦探究“孫熊之爭(zhēng)”的根本動(dòng)因,從而明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限界。
一、客軍入川與川省自治:
民國初期的川滇黔省際張力格局
“倒熊”之戰(zhàn)中的對(duì)立雙方,一方是滇軍首領(lǐng)唐繼堯主導(dǎo)的滇黔客軍與孫中山主導(dǎo)的四川民軍結(jié)成的“倒熊”聯(lián)盟,另一方是四川督軍熊克武與劉存厚、劉湘等川軍軍閥。除劉存厚外,參戰(zhàn)各方都為護(hù)法陣營中人。這場(chǎng)同室操戈的癥結(jié)在于民國初期的川滇黔省際張力格局。辛亥革命后,滇黔軍閥屢次在四川與南下的北方軍閥交戰(zhàn),四川軍閥內(nèi)斗時(shí)也多引滇黔客軍為奧援,后者遂入據(jù)四川。這之中,最為典型的是滇軍首領(lǐng)唐繼堯,圖謀借大義名分聯(lián)黔并川,主宰西南,進(jìn)而逐鹿中原。
外來勢(shì)力擴(kuò)張必然招致本地勢(shì)力反彈。1916年護(hù)國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后,蔡鍔率領(lǐng)滇軍入川討伐北洋軍,熊克武也隨之回川,并被任命為重慶鎮(zhèn)守使。蔡鍔任四川督軍兼省長后不久喉疾發(fā)作,離川就醫(yī)。臨行前,蔡鍔將四川軍政兩職分別交給滇系的羅佩金與黔系的戴戡,認(rèn)為“川事有羅、戴擔(dān)任,可保其必能翕然無間,漸就安理”[6]。
但在蔡鍔走后,四川“暗潮日甚一日”,其中“最大之兩派相持最烈者”即“滇川兩派”。而“滇派之所以勝利者,又在國民黨之關(guān)系”,以劉存厚為代表的“非滇派又非國民黨”的本地川軍是為“川派”。[7]隨后羅佩金主持裁兵造成“川滇黔軍隊(duì)留汰不勻”,引起“川派”極大不滿,最終導(dǎo)致1917年4月至7月間的“劉羅”“劉戴”混戰(zhàn)。時(shí)人感慨:“得不令人益低徊于蔡松坡其人不置也。”[8]
1917年6月,孫中山通電西南各省,號(hào)召武力護(hù)法。滇軍中人向唐繼堯提議出兵四川“名號(hào)始終以護(hù)法靖國為主”,實(shí)則“以北討親為名,而先靖川難,至于后來果否北討與否,不必計(jì)也”。唐對(duì)此表示“所見亦是”。[9]8月,唐繼堯宣布支持護(hù)法,表示“惟川事不定,實(shí)為大局之梗”,要“先行收川”,委托孫中山促熊克武“與滇黔一致”。[10]熊克武于當(dāng)年12月通電護(hù)法,孫中山要他與唐合作,強(qiáng)調(diào)“川、滇、黔唇齒相依,誼等一體。”[11]
1917年12月,唐繼堯以三省靖國聯(lián)軍總司令名義任命熊克武為四川靖國各軍總司令。1918年2月,聯(lián)軍攻克成都后,唐又任命熊兼任四川督軍、省長。孫中山認(rèn)為唐繼堯此舉“以滇督地位,任命川督,稍挾征服之威,足生反應(yīng)之患”[12]。當(dāng)年10月,唐繼堯在重慶聯(lián)軍會(huì)議上要求熊克武交出四川軍政、民政、財(cái)政大權(quán)。熊予以拒絕,雙方不歡而散。然而,“時(shí)四川供云南月餉,定銀幣二十五萬,云南軍輒自征之,月至四十余萬,川人怨益深”[13]。
在省際張力格局中,熊克武既主持四川軍政大權(quán),必然要考慮本省利益,從而逐步與唐繼堯相對(duì)立。受孫中山委托隨唐入川的章太炎對(duì)此洞若觀火,表示“云南不過欲得四川,借護(hù)法之虛名,以收蠶食鷹攫之實(shí)效”,而四川“非無力而易欺者也,強(qiáng)與抑制,必有內(nèi)爭(zhēng)”[14]。張力發(fā)展至1920年初趨于頂峰。3月17日,孫中山密電唐繼堯,表示“倒熊”一事“今當(dāng)促其速舉”。[15]唐繼堯亦密電滇黔客軍要“下大決心、有大準(zhǔn)備”[16]。熊克武先于4月17日通電辭職,旋即于5月4日宣布復(fù)職,隨后通電聲討唐繼堯“必欲憑恃武力割據(jù)川、滇、黔三省”,標(biāo)榜自己興兵是“為鄉(xiāng)國除殘去穢”。[17]
“倒熊”之戰(zhàn)是川滇黔省際張力格局發(fā)展的結(jié)果,而其亦推動(dòng)了四川“川省自治”思潮的發(fā)展。滇黔客軍盤踞四川致使“滇川惡感,醞釀甚深”;“所有兵匪團(tuán)警以及男女老幼,均一致仇視滇軍”。[18]出于“覺悟久仰他人勢(shì)力之非計(jì)”,“川省自治”運(yùn)動(dòng)逐漸興起;而面對(duì)“川人治川之語”,即使唐繼堯“亦有所不敢違”。[19]
在“川省自治”的旗號(hào)下,熊克武與劉存厚結(jié)成同盟,依靠“民心與軍心一致,官心與兵心一致”,最終于1920年10月?lián)魯 暗剐堋蓖恕5ㄜ姷膱F(tuán)結(jié)景象“遂以漸衰”[20]。滇黔客軍被逐出川,川滇黔省際張力格局遂告終結(jié),而此后川中仍舊兵戈擾攘。當(dāng)日后回憶這場(chǎng)苦澀的勝利時(shí),熊克武感慨:“同志變?yōu)槌鹑耍嗣裨馐艿満Γ谡紊鲜鞘×恕N沂窃肛?fù)一定責(zé)任的,惶愧無已!”[21]
二、置身事內(nèi)與西南紛爭(zhēng):
護(hù)法運(yùn)動(dòng)期間孫中山的川事抉擇
護(hù)法運(yùn)動(dòng)期間“孫熊之爭(zhēng)”的演變頗耐人尋味,最初孫中山不滿于唐繼堯與熊克武二人接近,但最后卻是孫、唐二人聯(lián)手“倒熊”。為此需要考察孫中山關(guān)于“川事”的抉擇歷程,從而理清“倒熊”的歷史經(jīng)緯。
在護(hù)法運(yùn)動(dòng)前,國民黨重視四川便為世人所察,有時(shí)評(píng)稱“假令川省一旦歸入民黨手中,則民黨關(guān)于西南諸省之連絡(luò)既成”,因而“民黨現(xiàn)頗以川省問題為民黨休戚之重大問題也”。[22]1918年2月,北京政府任命的四川督軍劉存厚、四川省長張瀾被逼離川,空出來的川省軍政交椅隨即成為爭(zhēng)奪焦點(diǎn)。當(dāng)月25日唐繼堯任命熊克武兼任四川督軍、省長。27日孫中山任命熊克武麾下的川軍第五師師長呂超暫行代理四川督軍。孫、唐二人的矛盾隨之展開。孫中山于3月1日獲悉唐繼堯的任命電,轉(zhuǎn)而決定爭(zhēng)取“軍民分治”,由國民黨“實(shí)業(yè)團(tuán)”派的楊庶堪為省長;同時(shí)表示“至督軍若非錦帆不可,亦火速公電推舉,此間方能任命,倘再遲延,轉(zhuǎn)恐錦忌,且無以對(duì)蓂帥。”[23]
對(duì)于孫中山“去二留一”的任命,熊克武予以忽視,依唐的任命兼攝四川軍政大權(quán)。黃復(fù)生請(qǐng)孫中山任命熊兼代省長,而孫在復(fù)電中認(rèn)為“(熊)尚未表明受軍府川督任命,縱再特加任何益?且恐熊兼,則滄伯難入川。”[24]與此同時(shí),孫中山又因人事問題同唐抵牾。唐繼堯稱“川、粵相距遼遠(yuǎn),恐我公未能盡悉內(nèi)容。以后川省用人,尚乞先行密商熊督,俾免窒礙”[25]。孫中山一邊對(duì)唐表示“尊電命錦帆兼任軍民,固亦見為必要”[26];另一邊對(duì)黃復(fù)生言及“熊錦帆至今未有電來”,而“唐帥側(cè)重熊一方,而又有忌軍府之意”,不滿之情溢于言表。他也因此希望“實(shí)業(yè)團(tuán)”推動(dòng)川中“一致堅(jiān)決表示擁護(hù)軍府”,使唐“可息自樹勢(shì)力于川之私意。”[27]
孫中山認(rèn)為:“川事之壞,責(zé)在重私仇,而輕大義。”[28]不過,孫、唐二人雖因爭(zhēng)奪四川而結(jié)怨,卻最終攜手“倒熊”,乃出于護(hù)法軍政府之內(nèi)斗使然。孫中山與陸榮廷之間“孫陸不相能”,在護(hù)法軍政府中“局道相逼”,破局之法“如弈棋,內(nèi)困則求外”[29]。為了聯(lián)滇制桂,1918年4月,孫中山向唐繼堯表示:“民國前途,希望惟在執(zhí)事一人”“川局諸賴維持”。[30]孫中山支持唐繼堯以川滇黔三省領(lǐng)袖行事,其在省際張力格局中的站位也就此錨定。此后,當(dāng)孫中山與岑春煊等人因改組軍政府一事交惡,熊克武對(duì)后者的聲援,觸及了孫“當(dāng)今急務(wù),在于先滅桂賊”的政治底線。[31]在孫看來,打倒桂系“必須合川、滇、黔全力圖之”,而熊的此番舉動(dòng)使他認(rèn)定“熊克武不去,則不能紓后顧之憂”。[32]
孫中山曾認(rèn)為“熊氏已走,川局自可大定,今后惟望主客各軍極端融洽”[33]。然而“倒熊”不滿一月,“因兵工廠造幣廠屬川屬滇之問題,呂與唐又成水火”[34]。對(duì)于“川、滇致爭(zhēng)之由”,孫中山感慨稱:“果使一方無侵略之野心,一方亦無閉拒之私意,則彼此猜疑盡泯,何事不成?”[35]可見他雖洞悉問題的核心,卻對(duì)之無可奈何。
與此同時(shí),孫中山亦改變了經(jīng)略四川的態(tài)度。發(fā)動(dòng)“倒熊”后,唐繼堯提議護(hù)法軍政府與國會(huì)移駐重慶,表示“利用滇、川、黔勢(shì)力,促進(jìn)大局,非以該地為總樞不可”[36]。其后三省軍政要人電促孫中山赴渝,孫乃復(fù)電稱“當(dāng)隨諸君后”[37]。但因廣東進(jìn)攻桂系“甚為得手”,孫中山認(rèn)為“不必往蜀”。[38]他向在川領(lǐng)兵的石青陽表示:“川禍連年,皆因內(nèi)訌,非力圖向外發(fā)展,終無寧謐之日”;而“刻下粵事極為得手”,要其待形勢(shì)有變時(shí)“務(wù)必舍去川中一切”,以“達(dá)吾等遠(yuǎn)大之目的”。[39]可見孫中山始終是從全局著手經(jīng)略四川,而川省并非唯一可持之地。此后川中“倒熊”同盟兵敗,石青陽為此向?qū)O中山指出:“此次川中戰(zhàn)事,本屬全勝之局,乃以意見不愜,遂至喪敗如此。”[40]
三、結(jié)語
概而論之,護(hù)法運(yùn)動(dòng)期間的孫熊決裂是一場(chǎng)兩敗俱傷的悲劇,其癥結(jié)在于民國初期川滇黔省際的張力格局。主導(dǎo)四川軍政大權(quán)者難以避免同滇黔客軍勢(shì)力沖突,熊克武與唐繼堯的矛盾、“倒熊”陣營內(nèi)部的矛盾均印證了這一點(diǎn)。孫中山為實(shí)現(xiàn)護(hù)法救國的理想,尋求經(jīng)略四川以建設(shè)革命基地。但他為西南護(hù)法陣營內(nèi)部的張力格局制約,在實(shí)用主義的驅(qū)使下選擇聯(lián)滇制桂。孫中山并非不知化解川滇黔省際張力格局的關(guān)鍵在于團(tuán)結(jié)主客一致對(duì)外,但囿于時(shí)勢(shì),卻不得不在張力的兩端之間做出抉擇。這是護(hù)法運(yùn)動(dòng)期間孫熊之爭(zhēng)的根本動(dòng)因。
在時(shí)人看來,孫熊之爭(zhēng)與護(hù)法陣營的內(nèi)斗是“武力之外,濟(jì)以權(quán)術(shù),聯(lián)彼攻此,詭計(jì)無窮,以如是黨爭(zhēng)而猶謂誠意言和,人誰信之”。[41]親歷者朱德“陷入了一種懷疑和苦悶的狀態(tài)”,進(jìn)而認(rèn)識(shí)到“用老的軍事斗爭(zhēng)的辦法不能達(dá)到革命的目的”。[42]馮自由向?qū)O中山進(jìn)言:“向來本黨員一入政界,即與黨中辦事人意見各走極端,不能一致。此實(shí)本黨前此失敗之最大原因。”孫中山對(duì)此表示:“所言極得我心,然辦法一時(shí)尚未確定。”[43]找尋“辦法”遂成為此后孫中山開拓革命新進(jìn)路的要旨。由此觀之,孫熊之爭(zhēng)雖是近代民主革命的昏暗處,但卻為人們提供了經(jīng)由實(shí)踐得出的思想資源。傳統(tǒng)政治力量與民主革命理想間的捍格促使人們反思既有道路的局限,從而探索革命的新路徑。這或許是所謂“X號(hào)標(biāo)本”的另一層深意所在。
注釋:
[1]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5頁。
[2]成都市政協(xié)文史學(xué)習(xí)委員會(huì):《成都文史資料選編》防區(qū)時(shí)期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頁。
[3]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習(xí)仲勛論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13年版,第387頁。
[4][11][15][23][24][26][27][28][30][32][37]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40頁,第291頁,第416頁,第334—335頁,第350頁,第359頁,第360頁,第305頁,第365頁,第416頁,第442頁。
[5]〔美〕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著,梅念譯,胡其安、李新校注《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shí)代》,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頁。
[6]蔡端:《蔡鍔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頁。
[7]《川省暗潮中之假聯(lián)邦說》,《申報(bào)》1916年9月4日,第6版。
[8]步陶:《雜評(píng)二:川人致岑西林電》,《申報(bào)》1917年8月14日,第11版。
[9][10][18]云南省檔案館編《云南檔案史料》1983年第2期,第35頁,第33—34頁,第35頁。
[12][16][17][21]四川省文史研究館:《四川軍閥史料》第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頁,第253頁,第320頁,第20頁。
[13][14][29]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36頁,第340頁,第317頁。
[19]《變幻莫測(cè)之川局》,《申報(bào)》1920年9月7日,第7版。
[20]《川軍復(fù)渝后之局面》,《申報(bào)》1920年11月9日,第7版。
[22]《收拾政局根本問題之索隱》,《益世報(bào)》1917年5月16日,第2版。
[25]云南省檔案館編《云南檔案史料》1983年第1期,第56頁。
[31][33][35][38][39]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頁,第190頁,第200頁,第201頁,第220—221頁。
[34]續(xù):《國內(nèi)要聞:北京通信》,《申報(bào)》1920年9月19日,第6版。
[36][40][43]谷小水:《孫中山史事編年》第7卷,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3598頁,第3697頁,第3703頁。
[41]默:《岑之宣言》,《申報(bào)》1920年6月22日,第7版。
[42]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朱德年譜》(新編本),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頁。
本文系2024年重慶市碩士研究生科研創(chuàng)新項(xiàng)目“新中國糧果矛盾的形成及其因應(yīng)研究(1949-1984)——以重慶長壽為中心的考察”(項(xiàng)目編號(hào):CYS240126)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 民族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