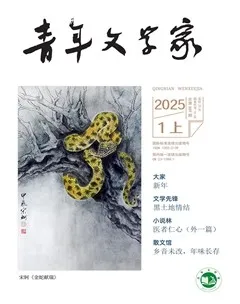家鄉的蘆葦
一絲涼風掠過,帶來了秋天的信息,家鄉的河堤下、池塘畔,一片片蘆葦在微風中搖曳成一幅絕美的畫卷,仿佛在深情訴說著秋天的故事。
在我們家鄉,蘆葦有個通俗的名字—大柴,而蘆葦花卻被稱作毛線花。
在貧窮的年代里,大柴是蓋茅草屋的材料,毛線花可以抵御寒冷。
白露前后,池塘畔和水泊旁,成簇成片的蘆葦花潔白如霜,隨風起舞。農婦們穿行在蘆葦叢中,剪下一株株大而蓬松的蘆葦花,放在柳條編的匾子里,曬上一些時日。曬干的蘆葦花又軟又綿,毛茸茸的,貼在臉上暖暖的、癢癢的,鋪在床上就是抵御寒冷的墊被。在那時的農家,墊被顯然是一種奢侈的東西,更多的人家是用蘆葦花編織毛窩(棉鞋),穿在腳上暖腳御寒。寒從腳底生,腳上暖和了,身上也就不覺得冷了。
在毛窩底釘上合適的木板,用一兩寸高的木塊做前掌和后跟,便成了村民口中的高木屐。冬天雨雪多,穿著它,就不用擔心雨雪浸濕鞋幫而凍腳了。
我隨父親回到原籍時,曾在西莊的吳家臨時棲身。吳家大爺四十多歲時雙目失明,老人家坐在床的邊框上,雙手摸索著編織毛窩。編毛窩除了蘆花為當家花旦外,還需草繩、麻繩等配角。稻草繩編的毛窩鞋口粗糙磨腳,吳大爺就先用細麻繩編,再續上細布條收口。吳大爺編的毛窩穿在腳上既舒適、暖和,又美觀、結實。
在紀念父親百年誕辰時,聊起當年的歲月,還想起吳大爺給我們編的毛窩,一股暖流自腳底升騰,緩緩地流進了心窩。
莊子上有個駝背老漢,干不了田里的活兒,春、夏、冬三季,用柳條或荊條編草簍筐、魚簍等,秋天編毛窩,逢集時拿到集市上賣。駝背老漢僅一個秋季編毛窩賺的錢,曾讓村里不少身強力壯的漢子眼紅不已。
入冬后的蘆葦洗盡鉛華,葉莖枯萎,由綠變黃,葦稈由枯黃至金黃,頂上的葦花變成銀白色,像一柄拂塵,堅韌地挺立在嚴冬里。此時的蘆葦蛻化為蘆柴,在外形上成了鄉親口中的大柴。
收割蘆柴的活兒很辛苦,光腳踩在水中,水寒徹骨。一只手攬著蘆柴,另一只手握著鐮刀在水面下蘆柴根處一下一下地砍。留在水底的根利如刀戟,扎在腳上血流如注,一股股殷紅回旋在池水間。有時,水面上結了一層冰,還要先把冰敲碎。在農村的那幾年,分給我們家的池塘中的蘆柴大多是父親和妹妹割的。妹妹當年十五六歲,褲管卷到膝蓋上,赤腳站在刺骨的池水里,臉龐凍得青紫,小腿上豎一道橫一道地滲著血,讓母親心痛了好多年……
那時的農村,清一色的茅草屋,房頂下鋪屋面是用柴笆子或是柴把子。先在地面上用蘆柴編織好柴笆子或捆扎成柴把子,然后鋪在橫條上,下口搭在墻體上,上口搭到屋脊上,用木條或者是竹片釘子等固定好,再在柴笆上面抹上一層稀泥,最后鋪上麥秸稈,房頂就大功告成了。
鋪屋面用蘆柴,間隔房間也是用蘆柴,柴笆子抹上稀泥便是一堵泥笆墻。村里人家鋪在床上的柴席和一圈一圈用來囤糧食的積子都是用蘆柴破開后編織而成的。
生命的美麗并不只在于綻放,更在于面對困難與挑戰時的堅韌與不屈。在雪花紛飛的嚴冬,收割了蘆柴的水下已在孕育著蘆葦的又一個春天。
迎春花開時,蘆葦的嫩芽迫不及待地從淤泥中探出尖尖的腦袋,不經意間已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左顧右盼,笑靨如花。桃花初綻時,蘆葦已是亭亭玉立,婆娑起舞,輕盈若夢,青翠欲滴,出淤泥而不染。
春天的葦葉是孩子們的短笛。摘一片嫩綠的葦葉,卷成圓管,一端輕壓成扁平,便是一支葦笛。放在口中輕輕一吹,清脆而悠長的笛音在春風里飛揚,在鄉間小路上蕩漾……
在蓮葉接天、荷花映日的夏季,茂密的蘆葦根植于池畔、泊邊,恣意鋪張著遠古的綠色,葉片豐腴,葦稈挺拔,裊裊娜娜,清風拂過,綠波蕩漾。入夜后,繁星點點,月光如水,螢火蟲在蘆葦叢間飛舞,如同一盞盞綠色的燈籠,為夏日的蘆葦增添了一抹神秘和浪漫的色彩。
夏日里的葦葉承載著汨羅江的傳說,端午前后,摘一疊豐腴的葦葉,卷成漏斗狀,裝滿糯米裹成粽子,紀念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他的詩句在耳畔激越,在心中跌宕。
桂子飄香的深秋,池塘畔水泊邊的蘆葦疏密有致,葦葉漸漸變細,色澤由綠變黃,葦花如雪,飄逸靈動。葦花應該是自然界里開得最遲的野花。萬木凋零時,葦花依然輕柔、恣意,像云,像霧,像雨,又像風。用它獨特的美,承載著深秋的溫柔與詩意,詮釋著大自然的神秘與魅力。
在歷史的長河里,蘆葦宛如一幅滄桑的歲月畫卷,家鄉淮安清口樞紐順黃壩埽工遺址,也有蘆葦身堵決口、固堤護岸堅韌而不拔的身影。這幾百年前的歷史遺跡是全世界運河史上的一個奇跡,不禁讓人肅然起敬。
蘆葦見證了生命的律動,也見證了生命的美麗不僅是綻放,還有無怨無悔的付出,以及面對困境與挑戰時的堅韌與不屈。
在季節的輪回里,蘆葦宛如一首古老的歲月之歌,從《詩經》里款款走來,衣袂飄飄……
家鄉的蘆葦在水一方,搖曳在記憶深處,搖曳在綿綿的鄉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