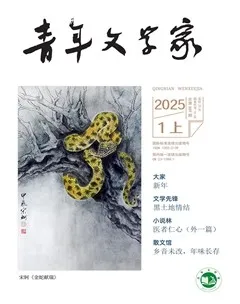如“鏡”的寶水:拉康鏡像理論視角下《寶水》中地青萍的身份建構
《寶水》是喬葉所著的一部長篇小說,聚焦于現代鄉村世界,展現鄉土中國的變遷。文本以主人公地青萍為第一敘述人,講述其見證了鄉村發展的同時,自身對童年時期創傷記憶的態度也經歷了從逃避過渡到了主動和解這一漫長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平衡又波折的精神轉變體現出了精神分析學中的鏡像理論。自我確認這一過程的完成,符合拉康的鏡像理論對主人公身份建構的切入,鏡像場域因素的對比也影響了她從身份焦慮到自我定義的過程。最終,在后鏡像時期她完成了主體身份的建構。
一、他者的構建:初期身份的探尋
拉康繼承了弗洛伊德的思想,并在其鏡像理論中提到,嬰兒在6~18個月的成長過程中,通過鏡子中他人和自我的映射逐漸完成自我感知,從完全依賴他人向自己獨立轉變,從而確認他人與自我的關系。在自我意識的建構過程中還存在著代表社會法則和文化秩序的“大他者”與代表自我投射和理想自我的“小他者”。
在寶水村這個“大他者”的環境中,出身于福田莊和象城的她并不能清楚地分辨自己在寶水村的身份。雖然主人公與寶水村的住民都出身于豫北農村,但由于文化人的身份標簽,使得她在介入寶水村建設的大事小情時只能以一種介于“自己人”和“外人”之間的微妙地位自處。她覺得自己“既不是白蒸饃,也不是黃窩頭,好像就是花卷,一層黃,一層白,層層卷著,有時候能利落分開,有時候根本就不能掰扯清楚”(喬葉《寶水》),身份焦慮一直在困擾著她。而主體只能在與他者的碰撞和相處中才能發覺自己的存在。于是,剛進入寶水村的地青萍從他者的目光與話語環境中開始構建自己在寶水村的定位。如在村委會工作,擔任婦女主任一職的大英、鄉建專家孟胡子等人都視她為外鄉來客;在西掌組長張大包、秀梅和小曹等人的眼里,她是人見人敬的“地老師”;在與她處于親密關系的老原和九奶眼中,她是孝順認真的好兒媳和好閨女……在此過程中,主人公不斷修正著自我的身份,來自外在他者的感性形象形成了她的自我主體。即使是在她面對村民口中的“地老師!原家的”這一調侃時,在“渾身的血就突然熱了一下”的感覺過后,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酸澀又真實的情感。她雖然在寶水村生活著,但她內心依舊存在著與村莊、村民之間的隔閡,不過在生活了一段時間后,她有了適應這里的想法。這是處于分裂狀態下的自我,組合成最初形象之后邁入“小他者”的第一階段。
語言的使用變化對自我身份的建構也起到了逐漸推進的作用。索緒爾的語言學構成了拉康對主體意識的研究方法,他認為那種無意識的“我”也是靠著一個巨大的意指關系的能指鏈來運作的。在地青萍的人生發展階段中,她回憶起自己剛從福田莊去象城讀書時,因語調里的鄉氣被大家嘲笑的過往。她的那句“怪卓哩”被城市里的同學們爭相模仿,讓初來乍到的她產生了自卑感,這種表現其實是一種能指鏈的斷裂。同樣,在寶水村乍一聽到不知所云的土家話時,對于剛從象城到寶水村并早已熟悉普通話的地青萍來說,也總會產生一種與自己所習慣的生活環境毫不搭邊的割裂感。在“扯云話”這一最普遍頻繁的敘事場景內部,不管是“接生毀眼”的典故還是“種谷要種稀溜稠,娶妻要娶個剪發頭”的民歌,都給她展示了最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土壤和語言環境,為她編寫著獨屬于寶水村的文化符碼。在城市與鄉村兩棲的她,語言交流的困境也使她在原地周旋,得不到他者的認同是造成地青萍自我身份困境的根本原因,與寶水村獨具特色的語言文化相順應、融合也是她的手段之一。于是,她帶著別扭與陌生的體驗再次被他者建構,去嘗試融入寶水村的能指鏈條,這便逐步形成了“土話—普通話—土話”的主體話語構建過程。
二、鏡像場域的碰撞:追尋主體的助推器
拉康認為,在可供觀測的場域中,自身是被凝視的一幅畫,對鏡中世界的旁觀定會造成對真實本我的構想。文本提供的客觀具象影響著主人公主觀內心的情感世界。在主體身份的認知與建構的過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自身存在的場域。在《寶水》這部作品中,寶水村和福田莊、九奶和奶奶這兩組影響因素構成了影響地青萍身份建構的鏡像場域。從他者的投射中,她會不由自主地將自我的成長經歷形成比對,這充當了她在寶水村中形成主體意識的助推器。對地青萍來說,從福田莊到象城再到寶水村,她不僅重新獲得了再度踏入鄉村的寶貴機會,同時也邁進了一個二次審視主體和情感記憶的鏡像世界。
從村莊的角度來說,在寶水村的日常生活與人情往來會無意識勾起主人公在福田莊的記憶,所以她用福田莊的主體來嘗試構建自己在寶水村的身份,在此過程中她產生了明顯的情感變化。如在與老原基于二者進行關于老家的對談中,老原說寶水村與福田莊一樣,都屬于懷川縣,怎么不算老家時,地青萍用五六十公里的距離為自己構建了一道厚重的心理屏障,她認為自己只是參與性的旁觀者,所以她說:“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喬葉《寶水》)但提到“水”時,地青萍卻因“寶水村”的村名含水,而勾起了自己對福田莊算命五行缺水和七十二個泉眼的記憶。看到寶水村的老祖槐便能想起福田莊院子里的槐樹,從聰明伶俐的曹燦身上看到了小時候在福田莊生活時沒心沒肺、胡天胡地的自己。她將自己對鄉村的依附感投射到了寶水村的一切,所以她已經開始從旁觀者逐漸步入了“既內且外”的階段。
在地青萍以寶水為鏡重新體認鄉村與自我的過程中,老原的親奶奶—九奶也起到了關鍵作用。九奶的存在讓地青萍想到了與福田莊聯系最為密切的、自己的奶奶。比如與九奶一起睡覺時,她回想起小時候因那封“玉蘭吾妻”的唯一信件與奶奶共同經歷的“閨密”夜談;關于人情,九奶與奶奶都有著各自的態度:九奶為了救人而受傷,她說:“人在人里,水在水里。活這一輩,哪能只顧自己。”(喬葉《寶水》)她的仁義與智慧也映照出了在福田莊的奶奶煞費苦心“維人”的道理:“人情似鋸,你來我去。”截然不同的情感牽連再一次激發了地青萍對人情的再理解與再認識。回想起奶奶這套人際往來的方式間接帶走了父親的生命。她失掉親人的苦痛以及對奶奶“維人”道理的逃避與苛責,構成了自己對奶奶和福田莊詛咒與厭惡的來源。
經過這兩組鏡像場域的碰撞和對自我本質的探尋,地青萍獲得了多次鏡像認同,逐漸在寶水村找到了主體的復雜情感,主動邁出直面過去的腳步。那些曾帶給自己苦痛與悔恨的回憶,她也不再將其懸置上空,而是選擇向內窺視,并自我接納。她因失眠癥將自身從大城市中抽離后來到寶水村,再度被激活的土家話使她在與村民的交流中如魚得水,重新銜接上了語言的能指鏈。地青萍從人際交往與情感體驗中實現了對鄉村邏輯的重新梳理,不僅包含了自己內省性的身份探索,更是在他者的世界中逐漸看清了主體身份的本質,并將多股錯綜復雜的情感紐結進寶水村這一“大他者”中。
三、和解的達成:身份建構的最終確認
在與大英、老原和楊鎮長等村民的人際互動中,地青萍感受到了療愈的力量,從初期的身份隱憂和保持懸置的參與觀察,到逐漸融入與不斷內省,終于在最后與過去的自我達成了和解。土話與普通話的先迭更替讓她在自身的語言系統里不斷完善著自身與再構建的世界。這在一定程度上屬于“他者”幫助“主體”找到歸屬感與安全感的后鏡像時期。
面對之前傷害過父母親的福田莊,帶著創傷性記憶的地青萍一直對它保持著厭惡與躲避的態度,甚至等奶奶咽氣之后才趕回故地。望見平原曠野時,老原詢問她是否見到福田莊時,雖然沒有真的看見,但她心里卻想著:“可其實我不是一直都在看見她嘛。寶水如鏡,一直都能讓我看見她。”(喬葉《寶水》)主客觀的矛盾展現了她內心對鄉村從對峙到和解的心理過程。她對九奶更是將其視為自己在福田莊的奶奶,有了一種不愿看自己的奶奶再死一次的依戀。最后,當七娘替奶奶轉述完“能恨出來就中。不悶著就中”時,地青萍終于為她落下了眼淚。九奶去世也讓她想起了奶奶去世前的以“好”為終結的話。在九奶和寶水村的感召下,地青萍產生出了一種詛咒越毒、心里越痛的愧疚和懺悔心理。主人公既介入又懸置的敘事姿態終于在最后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平衡,獲得了更貼近村莊內部的觀察位置。地青萍在鄉村中得到了療愈,最終完成了自我的身份建構,在他者和主體的統一中走向趨同。
地青萍完成了身份建構的過程,也顯影出了土地、風俗對人精神創傷的療愈與修復。作者很注重小說中“土地”的描寫,寫道:“最能讓人較真的也就是地。”主人公的姓氏也可以窺見作者的用意,可見在地青萍找尋自我的過程中,土地始終與她產生著緊密的聯系。她作為適應城市生活的知識分子來到另一個陌生的鄉村,對未知生活的隱憂和對福田莊的懷念與逃避催生了她的身份焦慮,但寶水村自然風貌和風俗文化的和諧統一使她在鏡像場域的互動中強化了建構主體的自信。寶水村的自然環境無聲地建立起對主人公的保護機制,讓地青萍在主體與他者對話、碰撞的過程中不斷認識自我。“花草不分家”中銅錘草和金雞菊兩種花卉吸引了地青萍的注意,她聞到它們細細的香氣時,竟也覺得“有一種神奇的治愈性”;她哄睡九奶后和老原返回中掌的路上,看到了淡如牛奶、無處不在的白霧,呼吸間發覺自己早已與它互相融合,化作了它的一部分。除卻自然風光對返鄉者的療愈,村莊的風俗文化也不斷加深她與寶水村的聯結,不管是摘香椿、打艾草、悶壇肉還是“扯云話”,作者精心雕琢的日常生活正以悄無聲息的方式治愈著地青萍的身份焦慮與精神創傷。對寶水村的現代化治理也在拉高主人公在鄉村生活的存在感,“孟胡子”建立寶水村村史館的提議勾起了她對福田莊記憶的回味與依戀;她的創意使名為“一青三梅”的抖音賬號擴大了村莊的影響力,趕上了鄉村旅游熱的浪潮;地青萍和利用假期支教的研究生暢聊的“廢話文學”也讓自己逐步適應著城鄉流動過程中的身份轉換。作者喬葉的用意不只是讓讀者了解地青萍在寶水村找尋自我的過程,更是想揭示出現代人“還鄉”情結對土地、鄉村的親昵。
借助拉康的鏡像分析理論,《寶水》中地青萍自我身份的建構過程可以得到更為清晰的審視,影響其身份建構的場域因素也在她自我認同的路上被收集、探索,最后得出她達成了自我和解的圓融狀態這一結論。這不僅折射出人本身對所居土地既依戀又逃避的情感,還體現了主人公在成長過程中主體與他者密不可分的關系,由此能聚焦到土地與人之聯系的思考和對命運的敬畏,以及隱現出的鄉土精神文化對身份焦慮的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