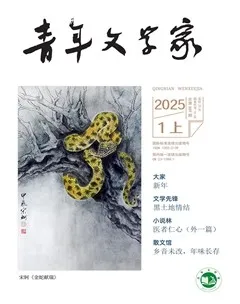《詩經·大雅·公劉》人物形象考
公劉,周人祖先之一,同時也是《詩經·大雅·公劉》的主人公。《詩經》共三百零五篇,但涉及公劉的詩只此一篇。《詩經·大雅·公劉》作為周人史詩之一,圍繞祖先公劉展開,敘述了他率領族人由邰遷豳的史績。詩共六章,第一章寫周族人民遷徙前的準備工作,第二、三章寫公劉反復視察豳地,尋找滿足周人生活條件的地址,第四、五、六章寫公劉定居后的一系列建設工作。本文旨在通過對《詩經·大雅·公劉》內容的研究,探討公劉積極進取、盡職盡責、足智多謀的人物形象。
一、積極進取的開拓者
從《公劉》第一章可知,公劉在邰地擔任首領時,該地被治理得井井有條。農業上“廼(乃)埸廼疆,廼積廼倉”,軍事上“弓矢斯張,干戈戚揚”。雖然邰地呈現出一幅豐衣足食、蓬勃向上的景象,但是公劉明白這只是偏安一隅營造出的表象,周部族的實力是遠遠不夠的。高瞻遠矚的他沒有被眼前的繁華所迷惑,積極帶領族人去探索新的領地,提升周部族的上升空間。
公劉時期的邰地之所以如此繁華少不了歷任統治者的努力。據《史記·周本紀》記載,從始祖后稷到公劉歷經四代統治者,分別是后稷、不窋、鞠和公劉。但有人對此質疑,認為后稷之后的世系有脫落,從后稷到公劉不止四代而是十多代。這個問題在文獻上無從考察,所以邰地究竟經歷了幾代王的治理也不得而知。但是無論后稷到公劉中間經歷了幾代,經過數年沉淀的周部族此時已經擁有了不容小覷的實力,“廼埸廼疆,廼積廼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便是最好證明。
“埸”和“疆”都是田界的意思,這里用作動詞。我國古代村社實行井田制,規定定期平均分配土地,因此需要定期修理整治田界,也就是詩中說的“廼埸廼疆”。從后稷起周人就將農業作為安身立命的基礎,到了公劉時期已經形成了系統的土地制度,周民在制度的管理下勤于勞作實現了“廼積廼倉”。“積”是露天的糧倉,“倉”是倉庫,這里也是用作動詞,指周人將收割的糧食儲存進糧倉,說明周人已經實現了糧食自由,糧食產量不僅可以解決人民日常的飲食還能有多余的糧食存進糧倉,以備不時之需。“廼埸廼疆,廼積廼倉”,這短短八個字揭示了周民族在農業上繁榮的發展現狀。“弓矢”是弓和箭,“干戈”是矛和盾,“戚”和“揚”都是指斧子,“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的意思是周族人在出發前收拾整理兵器。這句話表面上是描述出發前的準備工作,實際上是在暗喻周族的軍事力量。公劉率領族人由邰遷豳,豳地是戎狄所居之地,不論是遷徙途中還是在豳地定居期間都有被侵犯的風險,但是周民族順利抵達了目的地并展開一系列建設活動,想來是戎狄對這支軍隊有所忌憚。由此可知,公劉在邰地時無論是農業上還是軍事上都有了一定的實力,但他并不滿足于現狀,依舊保持一顆不斷向上的心,帶領族人去開拓新的疆土,壯大周部族的實力,是一位積極進取的開拓者。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公劉遷都的原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說法是由于公劉自己“變于西戎”而遷移,《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第二種說法是為了躲避戰亂,《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中載婁敬所言:“公劉避桀居豳。”第三種說法是公劉想壯大周族實力。其中,第一種說法不可信,它是將不窋被罷官后逃竄至戎狄這件事附會到了公劉身上。第二種說法更不可信,從《公劉》這首詩的內容可知遷移這件事是按照計劃一步一步完成的,沒有一點避亂避難的慌亂樣子。只有第三種說法是可取的,《公劉》開頭說“匪居匪康”,“匪”通“非”,“居”和“康”是安居、安樂的意思,就是說公劉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遷移是為了振興周族。
二、盡職盡責的統治者
在公劉的帶領下,周人順利到達豳地。對于他們而言,這是完全陌生的環境,需要花時間慢慢摸索。公劉作為部族的首領自覺肩負起責任,獨自去巡視豳地的領土,尋找合適的居住地址。確定居住地址后更是不辭辛苦地“相土”“度地”,在熟悉該地的地理環境后進行了合理布局,最終營建了一個新的聚落。
營建新聚落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十分復雜。首先需要盡快確定居住地址。《公劉》第二章開頭寫“篤公劉,于胥斯原”,“胥”,觀察之意,“原”即原野,是地形平坦或起伏較小的一個較大區域。公劉所“胥”之原“既繁既庶”,“繁”和“庶”都是眾多的意思,可見此處物產豐富,土壤肥沃。周人以農為本,“斯原”無論是地形還是土壤都適合種植農作物,滿足了周民族農耕的需要,適合作為定居地。“陟則在巘,復降在原”,“巘”是小山,登上小山從高處俯瞰原野,接著下到原野,在低處再觀察四方。經過反復巡視公劉最終選定該地作為新的聚落地址。接著便是國都的選址問題,對于這件事公劉著實花費了一番心血。第三章的“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廼覯于京”都是對公劉選定國都地址的敘述。“逝”,往也,公劉沿著原野的水系繼續走,發現了“百泉”,雖然此處水源充足,但是靠近河流容易發生洪澇災害,不適合建設國都。“瞻”有低處往高處仰望的意思,公劉沿著“百泉”到了地勢低洼的地方,從低處仰望廣闊的平原,此處地勢過低易坍塌也不適合作為國都地址。接著他又登上了南面的山脊,在俯瞰原野時發現了地形較高的“京”,最終將國都建在了“京”處。雖然此處沒有明說在“京”建都這件事,但是第四章的“于京斯依”可以證實這一點。“依”是族眾集體活動用的廳堂,有團結宗族和鞏固統治秩序的作用,是建設國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于京斯依”,“依”建在了“京”上,由此可知“京”便是國都的地址。
地址已定,接下來便是對聚落空間的謀篇布局,這也是營建新聚落的核心環節。布局需要因地制宜,因地制宜的前提是了解該地的自然條件,故文中寫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鄭《箋》解釋“流泉”為:“流泉浸潤所及。”“觀其流泉”是觀察地下水和地表徑流的情況。朱熹《詩集傳》解釋“陰陽”為:“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相其陰陽”意思是觀察不同陽光照射的山坡情況。公劉了解完該地水流和光照情況后,根據這些基本情況做出了“其軍三單”的布局。“其軍三單”這句話一直都有不同的解釋,至今沒有形成統一的看法。本文認為“軍”是聚居地,古代軍民一體,成年男性亦兵亦農。“單”字可以借鑒甲骨文中的“四單”,意思是分布于聚落中心的四方地域。公劉已經選定國都的地址,“京”便是聚落的中心位置,那么“其軍三單”就是以“京”為中心,在它的周圍規劃三塊聚居地。至于為何是“三單”而不是“四單”,原因是有一方不合適,這一點后文會提到,此處便不展開敘說。此外,公劉還進行了煩瑣的測量工作。“度其隰原”,“隰”和“原”在《詩經》中經常對舉,《毛詩箋》曰“高平曰原,下濕為隰”,意思是測量高處的旱地和低處的水田。丈量土地后公劉便有了“徹田為糧”的計劃,“徹”,治也,即開墾土地,生產糧食。這里與前文公劉選址的內容有所呼應,“斯原”的自然條件十分適合種植農作物,水源充分且土壤肥沃,公劉“徹田為糧”的舉措是明智的。除了測量田地,公劉還“度其夕陽”,“夕陽”是山的西面,度量山西邊的土地。聯系前文的“其軍三單”,可以推測出“京”的東、南、北面是平坦的土地,西面是山,故只能規劃三個聚居地。西面的山地形比較復雜,山的西面仍然有可以開發利用的土地,山離聚居地不遠,坐落在“原”上,很有可能是第二章提到的“巘”。關于山西面的土地,文中并沒有涉及它的開發利用,可能只是將其作為發展備用地。確定了聚落的布局,公劉率領族人建造房屋,人們在此定居,繁衍生息,同時吸引了諸多民眾歸附。隨著人口的增加,最初規劃的聚落空間也逐漸充實起來。從確定地址到空間布局,整個過程公劉都全身心地投入。無論是視察領土還是建造房屋,他都積極地肩負起屬于首領的職責,盡最大努力去做好營建新聚落這件事,是一位盡職盡責的統治者。
三、足智多謀的建設者
在豳地建設新聚落的過程中,公劉在政治制度建設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開創了“君之宗之”的政治制度和“其軍三單”的軍事制度。這兩項制度后續一直被周族祖先沿用并不斷革新,為鞏固穩定周族政權發揮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政治制度的建設,《公劉》第四章記載:“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幾。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這段話的意思是公劉在“依”宴請群臣,眾人按照次序依次入座,席上舉止有禮,好不和諧。宴會結束后他們推選公劉為部族首領并實行“君之宗之”的政治制度。鄭《箋》曰:“為之君,為之大宗也”,意思是公劉是國君也是大宗,突出公劉的統治地位。豳地原本是戎狄的領地,周人遷徙至豳后,豳地便成了戎狄和周人共同的居住地。若公劉是豳地的國君,那他就是該地最大的大宗,戎狄和周人作為小宗都要服務聽命于他。周人和戎狄是生活在豳地的兩個不同部落,如何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是公劉建立政治制度的契機,君統與宗統相結合的政治制度讓他的權力凌駕于兩者之上,可以滿足自身統治需求。該制度的建立不僅有利于鞏固政權,加強公劉統治,還能防止內部政權紊亂。西周建立后實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其本質便是“君之宗之”,它為西周初期的政治制度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影響了后世歷代政治制度的建設。
其次是軍事制度的建設,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其軍三單”。“三單”上生活的成年男性亦兵亦農,擁有雙重身份的他們同樣也需要肩負起雙重責任,閑時練兵,忙時農耕。公劉并沒有設立單獨的軍事隊伍,而是將農耕和練兵結合,形成了耕戰一體化的軍事模式,這種模式也被稱為農兵合一的軍事制度。周人遷豳后的生存環境是嚴峻的,一方面他們需要墾治農田,發展農業生產;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與周邊戎狄部落發生摩擦,這就需要一定的軍事力量與之抗衡。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公劉開創了農兵合一的軍事制度。該制度的建立不僅為周人在豳地順利進行農業生產提供了保障,也影響了后世周人軍事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公劉在豳地建設新聚落的過程中,基于部落的現實情況創造性地建立了適應周族發展的政治制度和軍事制度,是一位足智多謀的建設者。這兩項基本政治制度被后世統治者繼承并不斷發展,為周朝的發展奠定基礎,可以說公劉用自己的智慧在周族歷史畫卷上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周部族具備一定的軍事實力,但是文獻中幾乎沒有公劉領兵作戰的記載。關于周族的軍事力量,文中有這方面的描述,即“弓矢斯張,干戈戚揚”和“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前一句話是由“弓矢”等多種兵器的名稱組成,一方面是指周人擁有雄厚的武裝設備,另一方面用兵器代指軍事力量,暗喻周部族強勁的軍事力量。后一句話是對公劉服飾的描寫,作為首領公劉隨身攜帶兵器,說明他本人具備一定的作戰能力也十分重視軍事的發展。
綜上所述,周族有較強的軍事實力,但是公劉在與周邊戎狄部落的相處過程中堅持以德治天下的理念,采取教化式的溫和方式。他將種植農作物的技巧傳授給戎狄,經過長時間的交流融合,戎狄的經濟發展模式發生改變,形成了農耕經濟與游牧經濟并存的發展格局。此后,很多戎狄部族臣服于公劉的統治,公劉也逐漸成為整個豳地的統治者,德治理念也被周人繼承發揚,成為周朝延續百年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