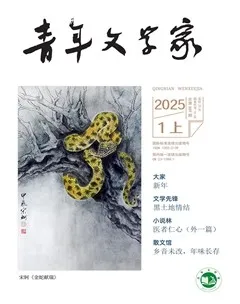清明“借”宴
在惠州搞建筑的老表阿華曾多次寫信并打電話給我,叫我務必在清明節休假時過去玩兒。
到了清明節那天,我剛好輪休,因為在廚房工作的特殊性,所以別人休假時我們更忙。
剛出門,天空就飄起毛毛細雨。經過幾次轉車,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老表的住處,進門看見一幫老鄉正湊在一起打撲克牌。
聽著熟悉的鄉音,我好像回到了魂牽夢縈的故鄉。沒坐多久,就到了吃中飯的時間。我的肚子已經餓得受不了,里面直打鼓。我找個上廁所的理由跑去廚房偷看,里面空蕩蕩的,什么都沒準備。我找到阿華,說:“老表,自家兄弟就不用那么客氣,買些菜我來幫你們煮就好。”阿華聳聳肩,說:“老表,不好意思啊!我今天還真沒有做準備,等下帶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開玩笑:“難道你訂好酒店了?”阿華說:“不要笑話我了,都幾個月沒發工資了。”阿華并沒有顯露出囊中羞澀的樣子,還故意賣關子。他把大拇指同中指塞進嘴里,用力吹了幾下,那幫老鄉一窩蜂似的跑出來。我不清楚阿華到底要搞什么名堂,詢問道:“老表,你這是干什么?”阿華說:“不用急,等下你就知道了,你不是餓了嗎?我現在就帶你去吃大餐。”
老鄉們個個換上一套干凈的衣服,皮鞋擦得亮堂堂的,嘴里叼著香煙,兩手插進褲兜里,昂首挺胸,大步向前走。我膽怯地跟在他們后面,頭也不敢抬。奇怪的是,他們每人腋下都夾著一只空米袋,有說有笑地來到了惠州西湖邊上的一片祖墳山上。
阿華膽子大,他帶頭走在最前面。對面就是當地的祖墳山,山下停滿了各種豪車,滿山都是成群結隊的香港人,他們也是回來祭祖的。
他們隨身帶著在酒店預訂好的祭祖禮品,如白切雞、咸水鴨、福壽魚、扣肉,還有酒水、飲料等等。一些墳冢旁邊還放著水果籃、花籃,或貴重的烤金豬。他們把這些祭祖禮一一擺放在墓碑前,祭拜祖先。
阿華看看手表,招手分工,他帶著我走東邊的墳冢,其余人去西邊墳冢。在上坡處迎面走來一隊香港人,他們看見我們一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地走過來,還主動同我們打招呼:“老板,你們也來拜山啊?”所有老鄉中,只有阿華會說廣東話,他交代大家,不會說就不說,萬一碰面,他們找你打招呼,就“嗯”一下!阿華用熟練的廣東話回答他們。香港人見是老鄉,連忙把從香港帶過來的萬寶路香煙整條整條地扔過來。阿華接過香煙,也散了幾支廣東的紅雙喜香煙作為回禮。我生怕被他們發現破綻,心繃得緊緊的,大氣都不敢出。阿華卻若無其事地同他們打得火熱,有說有笑,還相互拉起家常,我小心翼翼地向前走。
一路上,我們收了十幾條香煙。阿華招呼大家放緩腳步,在原地休息一會兒。等到香港人祭奠完走了,他一聲令下:“快!把所有能吃的、能喝的裝上。”不到半個小時,整片祖墳山上的祭品都被我們這幫老鄉一掃而光。他們還個個炫耀自己捕獲的戰利品,一下子好吃好喝的東西堆積如山,大家一路上一邊警惕后有追趕,一邊慌忙撤退扛回家。
大家擼起袖子,爭著搶著要下廚,我知道他們不是秀手藝,而是肚子實在是太餓了。我看他們弄回來的全都是廣東風味的菜,開玩笑說:“這都是給廣東本地祖先準備的,他們不吃辣椒。如果祭拜我們的祖先,必須做老家的味道,祖先吃了一高興,會保佑我們行大運發大財的。”大伙聽了,開心地笑起來。
我把收集回來的菜分類加工,挑選了一只最大的白切雞。先把白切雞斬件,保持原型拼擺入盤,取一只小碗,放入姜碎、蔥粒、蒜蓉、指天椒碎,加入少許雞精、食鹽,再取熱鍋放油,燒至四到五成油溫,將熱油倒入盛放姜蔥蒜的碗里,加少許生抽調味,最后把味汁淋在白切雞身上,一道湖南風味的白切雞就大功告成了。
第二道菜是烤金豬。把烤金豬斬成小塊,熱鍋放油,燒至六成熱,把斬好的金豬下入油鍋炸至酥脆撈出備用;熱鍋放底油,下青花椒粒、姜絲、蒜片、蔥段、青紅椒塊和少許紅油豆瓣醬一起炒香;把炸好的金豬塊倒入鍋中,灑幾滴料酒、芝麻油,翻炒幾下起鍋,裝盤,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湖南式烤金豬就做好了。大家看著我加工的菜,一個個食欲大增。
菜全部端上桌后,阿華擺上十只空碗,十個空酒杯,分別在每只碗中盛半碗米飯,酒杯分為兩種,一半倒酒,一半倒飲料,每只飯碗上放一雙筷子。
阿華將手臉清洗干凈,把衣服整理一番,朝著太陽升起的方向,很虔誠地跪下,嘴里念道:“各位列祖列宗,各位前輩,今天晚輩請你們吃飯了,你們一定要保佑大家。”說完,阿華指揮大家把碗里的剩飯倒進鍋里再加熱,把杯中的酒水全部倒在桌下,再次盛滿飯,斟滿酒。
祭祖禮儀完畢,阿華端起杯中的酒對我們說:“大家出門在外,不方便回鄉祭祖,今天就把工地上所有老鄉召集過來,借上“偷”來的酒菜敬我們的祖先,這也算借花獻佛。不過這種事不可取,以后不要再干了。”
自那次惠州清明之行后,每當想起那件事,我都對我們的行為感到無比羞愧。后來每年的清明節,不管我身在何處,不管有多忙,我都會提前規劃回鄉祭祖的行程。
今年的清明節,我不想回老家祭祖,想再去惠州西湖邊上,擺上一桌酒宴,回謝一下1995年清明節“借”來的酒菜,為當年的無知說上一聲“對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