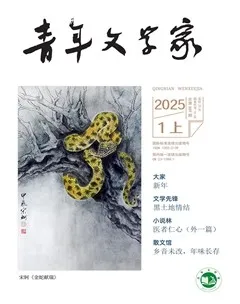情思雁丘園
公元1025年,時年十五歲的元好問由秀容(今忻州)赴并州(今太原)府試,路遇捕雁人講述一則異事:“今旦獲一雁,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
元好問聽后,將這只投地而死的大雁買下,葬在汾河邊,壘起石頭作標志,取名“雁丘”,同時作了一首承托感思的《摸魚兒·雁丘詞》:“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狂歌痛飲,來訪雁丘處。”一雙雁的貞烈感動了一個詞人,一個詞人的感慨問住了我們所有的人。作者運用比喻、擬人等藝術手法,在《摸魚兒·雁丘詞》中將震驚、悲慟、同情、感動化為壯士扶劍般的仰天之問,問蒼天,問大地,問世人,問自己,遂成“千古之問”。
我們來到鐘靈毓秀的汾河邊,秋日的汾河兩岸,秋色怡然,韻味初現,一場雨過天晴后,天高云淡,美麗壯觀。站在好問樓,“來訪雁丘處”—遠望西山,綿延起伏,黛色朦朧;近賞汾河,一泓秀水,柔波輕蕩。望蔚藍無際的鷗鳥飛翔,與近處的湖泊水岸、亭臺樓閣、樹林灌木,以及掩映在山水、林木、河畔之中的棧橋,構成了一幅水墨畫卷。
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曾盛贊大雁有四德:“寒則自北而南,止于衡陽;熱則自南而北,歸于雁門,其信也;飛則有序而前鳴后和,其禮也;失偶不再配,其節也;夜則群宿而一奴巡警,晝則銜蘆以避繒繳,其智也。”講述的是雁之情、雁之有信、雁之機智、雁之禮讓、雁之情義、雁之仁心。
古代詞人,將大雁描繪為浪漫的禽類,雁影分飛、雁陣、雁序、雁書、雁帛。大文豪范仲淹、詩仙李白、詩圣杜甫的筆下曾留有“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彎弓若轉月,白雁落云端”“腸斷江城雁,高高正北飛”等詩篇佳句。
這也讓我想起,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曾風靡全國的電視連續劇《神雕俠侶》中的一段情節:郭靖養了兩只大雕,在一場打斗中一只大雕受傷而死,另一只不愿獨活,撞巖殉情。原來,金庸先生的這段情節設置的典故即來源于此。
此刻正值傍晚時分,夕陽落下,在園區的綠色草坪上、河堤兩岸邊、棧道長廊里,有扎堆休息的,有三三兩兩聚集聊天兒的,有獨自靜神冥思苦想的,有站在那兒眺望遠處風景的……
這里曾是一片荒涼之地,因建雁丘園而聲名遠揚。雁丘園建在亙古綿延的汾河東岸,西鄰汾河水,北望崛圍山,氣勢恢宏的亭臺樓閣、斗拱飛檐的回廊曲徑、巧奪人工的休憩小軒,盡顯晉派風格之古韻典雅。
雁丘石,看起來就是塊大石頭,長約四米,高約兩米,呈不規則橢圓形。頂端有兩只展翅飛翔的大雁雕塑,正面用草書刻了元好問的《摸魚兒·雁丘詞》全文,章法得體,瀟灑自如。站在石旁,我忍不住低聲吟唱:“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走進雁丘園,沿趕考長廊漫步,仿佛走進詩人的闋詞里,思古之情油然而生。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七歲能詩,三十一歲進士及第,有“神童”之譽,善作詩、詞、曲、文,被尊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縱觀先生一生,少年問情摯愛,青年問情詩曲,中年問情鄉愁,晚年叩問家國情懷,一生赤誠真摯。
園內以《雁丘詞》里詞語命名的“雙飛亭”“只影軒”“千山亭”“狂歌亭”等建筑各具特色,寫滿了詩情畫意。如雙飛亭,就是兩個方形建筑套在一起。從里看,內部垂簾柱采用穿插結構,在古建筑、仿古建筑中比較少見;從外看,四周屋頂曲線仿佛延伸至天空,頗有莊嚴、雄偉之態。
園內有兩處自然形成的湖泊,繞湖而行,流連忘返。湖水碧波蕩漾,水邊蘆葦搖曳,水里野鴨游弋。亭臺樓閣倒映湖中,別有一番意境。左湖邊,有一群大雁雕塑,遠望之時,有展翅欲飛的感覺;右湖邊,有一塊石頭上刻有紅色的“雁丘”二字,是趙孟頫的字體。湖四周,有國槐、油松等喬木,有金枝槐、榆葉梅等花灌木,并配有綠籬、草坪等。
據說園林設計者獨具匠心,為深度還原“雁丘”意境,對元好問由忻州赴并州趕考之路、冬春鴻雁遷徙過境之路進行挖掘,精心圍繞“一泓清水入黃河”和周邊山勢起伏、水岸迷人景色,暗合“萬里層云、千山暮雪”的詞意,以開散、自然、野趣為主,一步一景,徐徐展開,將人文歷史與自然景觀巧妙相融的雁丘園呈現在世人面前,給人以無限遐想、意猶未盡的生動體驗。
遠山、秋水、蘆葦、亭臺……每一景,都有歷史的漣漪;每一步,都是現實的光影,沉浸其中可開啟一段穿越之旅。比如好問樓,所有檐柱端部均有“卷殺”,將構件或部位的端部做成緩和的曲線或折線形式,使得構件或部位的外觀顯得豐滿柔和并帶有側角;部分建筑還采用了“乳袱”與“叉手”相結合的方式;又如園區路燈、鐵藝圍欄設計的都是兩只大雁銜燈和在空中飛翔的場景,讓人們時時處處都能感受大雁故事的浸潤,都能簡單了解元好問的身世,都會被兩只大雁的生死故事感動。
光陰枯榮,紅塵陌上,元好問親手壘起的一方小小石冢,在古老的汾水河畔早已湮滅。八百年來,前來故地尋找詞中遺跡的“癡情兒女”卻從未斷絕。雁丘之于世人,已成為詠嘆愛情死生契闊、忠貞不渝的鮮明文化符號,在歷史長河中,晶瑩閃亮,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