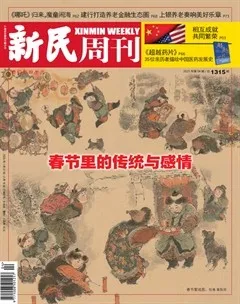汪大文:自由暢快,優(yōu)哉游哉

“我的人生就像一個一個的圓,從上海出發(fā),歷經(jīng)紐約、香港,最后又回到故鄉(xiāng)。值得欣慰的是,無論我走到哪里,都立志讓中國畫這顆小小的種子開出五彩繽紛、絢麗奪目的花朵。”誠如著名畫家汪大文所說的那樣,自己一生足跡串聯(lián)起的故事,仿佛一幅深得中國傳統(tǒng)藝術精髓的長卷,徐徐展開,異彩紛呈,也為她的人生描繪了一道美妙的圓。
乙巳新春,屬蛇的汪大文迎來了自己84歲本命年,在她位于蘇州河畔的畫室“神石軒”中,水仙盛開,伴著墨韻茶香,墻上掛著自己剛完成的新作,案頭擺著素來鐘愛的石頭、硯臺,滿壁的畫作和古色古香的家具擺設相映成趣,更顯溫馨雅致。年過80之后,汪大文并沒有停止自己對藝術的追求,將家中整整一面墻做成畫板,連續(xù)兩年時間里,畫成了好幾幅丈二匹的大畫,多數(shù)都是她最為擅長的荷花、牡丹,水墨、潑彩、重彩、工筆……形式多樣,氣韻萬千,既有謙素的凈白,又有裊娜的斑斕。

閑暇時,汪大文喜歡和朋友、學生靜靜地坐下來,聊聊藝術、家庭和人生,但佐談的絕不是一杯清茶那么簡單,常常是她愛喝的奶茶與好吃的甜品、蛋糕。她也喜歡逛花鳥市場與古玩店,往往一只漂亮的鸚鵡,一塊樸拙的石頭,一朵嬌艷的蘭花,都能讓自己開心上好半天,并樂此不疲地把這些好玩的東西搬回“神石軒”與大家共享……耄耋之年的汪大文就是憑借這樣的心態(tài)活得自由暢快——時而體會筆墨世界為她帶來的揮灑樂趣,時而享受濃濃友情帶給她的溫馨,而更多的則是沉浸于家人、學生在身邊的愛與關懷,絲毫不計較名利得失,永遠畫自己想畫的作品,知音共賞,優(yōu)哉游哉。這種“游于藝”的精神狀態(tài)也為她的生活平添了不少情趣。
程門立雪,嚴師出高徒
汪大文從小與畫有緣,母親丁靜影是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當年為數(shù)不多的女學生之一,父親更是不折不扣的畫迷,與不少名畫家交往過從,甚是親密。在這樣一個以畫為中心,全家與書畫結緣的環(huán)境影響下,小時的汪大文自然而然地拿起了畫筆,她先后拜著名畫家——也是父親的好友錢瘦鐵、唐云兩位為師學畫,前者教授汪大文山水畫技藝,后者則指導其繪畫花鳥的技法。“唐云老師告訴我,雖然我是女兒身,但不能因此拘泥于小規(guī)格作畫。要畫就要‘畫大畫’!所以他常常拿出四尺整張的大宣紙,讓我直接在上面畫松樹、梅花等等,借此鍛煉我的膽量和筆力。”
1960年,剛成立不久的上海中國畫院準備招收5名青年學員作為新中國第一代傳統(tǒng)中國畫接班人,分別從工、農(nóng)、兵、學和少年宮招收5名青年學員,采取傳統(tǒng)的“師父帶徒弟”的辦法,學習中國傳統(tǒng)國畫藝術。正是青春年華的汪大文憑借自己在少年宮出眾的繪畫技藝,被一眼相中,與來自工廠的陸一飛,來自農(nóng)村的吳玉梅,來自學校的毛國倫,來自部隊的邱陶峰等一起,幸運地進入了上海中國畫院學習,而她的授課老師正是一代大師程十發(fā)先生。

汪大文尚清晰地記得自己第一次“立雪程門”時的情景,程十發(fā)兩道粗黑濃密的眉毛,加上一絲不茍的板刷頭,儼然是一副不怒自威的嚴師風范。作為國家布置的任務和使命,程十發(fā)對于自己首位弟子的要求的確格外嚴格,不過俗話說得好,“嚴師出高徒”,老師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汪大文盡早學有所成。認真的程十發(fā)在第一堂課上就親手制訂了詳細的教案,并羅列出完整的閱讀參考書目。不僅要臨摹,還要寫生,練習書法,學習詩詞……汪大文至今銘記老師當年的教導:“要從唐人宋人的畫作開始臨摹,打下良好的基礎。如果學不到唐風宋韻,至少還能追摹明清筆墨。好比攀登珠穆朗瑪峰,即使爬不上,依舊能站在高峰,如果爬一座小土丘,一旦掉下去,豈不跌入溝渠?”
正是這樣通過對傳統(tǒng)中國畫正脈手追心摹的不斷追求,汪大文打下了深厚的傳統(tǒng)中國畫基礎。“我有時候跟當年的老同學聊天,大家依然覺得那段四年的畫院求學的時間是最愉快的,1964年以后我們算畢業(yè)了,就留在畫院了。如今幾十年過去了,回想往昔,老先生們把我們當寶貝一樣,怎么培養(yǎng)每一步都安排得非常好。”汪大文至今對恩師程十發(fā)的一番教導深有感觸,“他說我們畫國畫的,應該首先解決古為今用的問題,先繼承遺產(chǎn),發(fā)揚民族繪畫為前提,民族的東西是一個核心。”
不似之似,實現(xiàn)藝術飛躍
“改革開放”之后,已經(jīng)小有名氣的汪大文過了一段“頗為幸福的生活”,她幾乎天天伴隨在程十發(fā)老師的身邊,從內(nèi)蒙古到洞庭,從黃山到北京……聰明的她看老師揮毫作畫,細致耐心地模仿老師的作品,從中學到了許多筆墨技巧與構圖方法,畫技大進,一度學得幾可亂真。一時間,榮寶齋、朵云軒、友誼商店等紛紛前來訂畫,日子過得寬松舒適。
“如果當初我留在國內(nèi),或許我的風格永遠就是模仿老師的,一成不變。所幸的是,我大膽地走了出去。”自1981年起,年過40的汪大文帶著自己10歲不到的兒子走出國門,在異鄉(xiāng)開始了自己新的起步。當初的這個決斷使她承受了很大壓力,但回頭看來,她的確成功了:無論在香港還是在紐約,汪大文始終很活躍。創(chuàng)作精力旺盛的她時而畫荷花,時而畫觀音,時而又畫起了牡丹……每次拿出的作品都令人耳目一新,甚至得到了眾多西方人的喜愛與追捧。

1981年,懷揣著僅有的400美元,汪大文母子倆踏上了美國的土地。惴惴不安的汪大文帶著老師程十發(fā)的介紹信,叩開了在美國上流社會素有“C.C王”之稱的著名收藏家王己千先生家的大門。想不到,熱心的王老第一句話就說:“程十發(fā)是當代唐伯虎。”當汪大文拿出了老師親筆寫下的介紹信時,王己千意味深長地說道:“你有這樣一位好老師是你的幸運。為此你應該加倍努力。”在此后的日子里,王己千在生活和藝術上給了汪大文母子極大的幫助,毫不吝嗇地將畢生所藏借給汪大文臨摹、學習,開闊了汪大文的眼界。除了王老,身為婦科醫(yī)生的華人畫家楊思勝先生也極為熱心,他無私地為這位素不相識的國內(nèi)同行推銷畫作,使汪大文在美國收獲了第一桶金。不久,頗為著名的“華美協(xié)進社”又邀請汪大文教美國學生畫中國畫。“當時我可能是大陸去美國最早的一批中國畫家,之后不久又來了陳逸飛、陳丹青等人。至今回想起來,那時在紐約的華人真是很友善!他們都毫無回報地幫我的忙。所以我在美國那么多年,很幸運從沒離開過中國畫。”除了創(chuàng)作與展覽,她還先后教學和示范于美國紐約市立大學、達拉斯大學、達拉斯中國畫苑等高等學府十多年,成為中國當代畫家中作品上拍于佳士得和蘇富比等國際大拍賣行的少數(shù)人之一。

對于汪大文在美國時期的繪畫作品,藝術評論家丹尼士·偉普曼有這樣的評說:“近30年來,西方漸漸認識到現(xiàn)代中國畫并感到驚訝。令人吃驚的不單是東方藝術家在國際美術技巧上的表現(xiàn),而且他們雖狂風似的以各種姿態(tài)出現(xiàn),卻又不失其傳統(tǒng)技術,現(xiàn)代中國古典畫家汪大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汪大文本人也表示:“來到美國后藝術視野打開了,我的畫也開始變化了,越來越絢爛,越來越抽象,但保留著中國畫的筆法與精神。”盡管畫的仍是傳統(tǒng)的荷花、觀音,但無論色彩還是筆墨,都有了許多“中西結合”的韻味……
從“酷似乃師”到“有別乃師”,汪大文完成了自己藝術上的一次“不似之似”的飛躍。當她將自己創(chuàng)新的作品送到恩師程十發(fā)上海畫室的案頭時,古稀之年的程十發(fā)極為高興地說了句:“這才是我的學生汪大文!”
回到起點,像一個畫壇隱士
汪大文在美國取得了成功。不久之后,她來到了香港,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開始了新的探索。由于香港中外文化交匯的獨特優(yōu)勢,使得汪大文更是如魚得水,不僅兩度在“萬玉堂”畫廊舉辦了個人畫展引起轟動,還成為了香港大學的教授,專門教授國畫藝術。
2004年,飄泊了整整24年的汪大文回到了自己的故鄉(xiāng)——上海,并在母親河——蘇州河畔擁有了一間頗為寬敞的大畫室“神石軒”,回想起曾經(jīng)的種種經(jīng)歷,汪大文別有一番感悟:“回到起點了,我找回了自己的根。”
又是二十多個春秋過去了,即將迎來84歲本命年的汪大文,在“中西合璧”的藝術追求上,有了更深刻的體會與實踐。她擅長運用酣暢淋漓的墨色,在宣紙上形成游離變化的墨跡水痕,用來顯示荷葉的自然肌理,再大膽地點綴金色,既豐富了墨彩的層次感,又提升了中國畫的色彩感和光線度,這種雍容華貴、水墨淋漓、渾厚華滋的境界,既是具象、傳統(tǒng)的,又是寫意、現(xiàn)代的,在講究筆墨、色彩和結構的同時,也在不斷追求虛實和諧的統(tǒng)一。正如王己千先生所評價的那樣:“汪大文的作品充滿了律動感和情趣美,有的刪繁就簡,以形寫神;有的筆飛墨走,難辨始終;有的墨意巧妙,情趣橫溢。畫家慧心巧思,不拘囿一格,揮毫無羈,探索畫有盡而意無窮的奧妙。”

心無維摩詰,筆墨是長春。面對贊譽與榮譽,汪大文看得很淡,因此,在熙熙攘攘的當代上海畫壇,很少看見她的身影,但只要說起她筆下的觀音、荷花,業(yè)內(nèi)外無不是交口稱贊。程十發(fā)大弟子,旅美著名藝術家,上海中國畫院第一代嫡傳正脈……無論身上有著怎樣的榮譽,汪大文始終生活得像一個畫壇隱士,享受生活,醉心筆墨,僅此而已。她總說自己真是幸運的一個人,老先生們在她一生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而一生天南海北的際遇又有緣得遇許多高人、貴人、好人,妙不可言的緣分構筑了自己別樣精彩的人生。

“從地球的這邊到另一端,走過的是一個圓,遇到的都是貴人,不忘的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人生之路好比行舟,迷時師渡,悟時自渡,最終渡己,渡人。”在汪大文心里,“師承”繼承的不是具體的一筆一墨,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繼承,是中國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