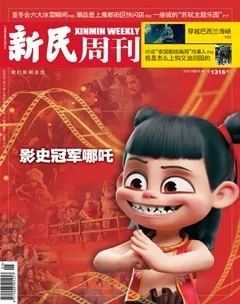經由猝死,擁抱無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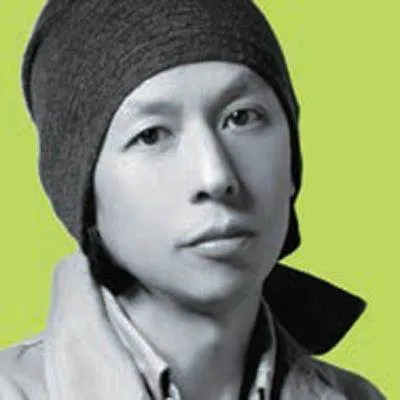
在書店舉行的簽書會上,作家,也是電影女主角,正一本一本給讀者簽上名字的著作,叫《關于猝死》。
沒有比這幾個字能讓看《隔壁房間》時的我,更快打開進入這電影的門。短短兩三個月期間,在我身邊的“猝死”事件,共有三起,如果不把瓊瑤的“安樂死”計算在內。
雖然上星期客死東京的大S徐熙媛,不屬“身邊的人”,但公眾人物與我們的密切性,對比親友的“熟悉卻陌生”,可以是“陌生而熟識”。恰恰由于她是陪伴一代人成長的“閨蜜”,余震肯定持續更長更久,因為死者是震中央,生者才是漩渦。
另兩位的身份是幕后功臣,但行業翹楚如電影美術設計樸若木,他的成績如《阮玲玉》《色,戒》有目共睹,忽然傳來他的死訊,大眾一片惋惜的同時,一個月前才跟他聊過電話的我,只有更覺不可置信。還有編劇王紀堯,年齡尚輕,怎么會才出現不適,便因細菌入侵(據說)而倉促離世?
回到銀幕上的簽書會,當有讀者問作家英格麗(朱利安·摩爾飾):“在序言里,你說寫這本書,是為了更了解和接受死亡?”她回答:“是的,看起來死亡有違自然,我很難理解有生命的東西非死不可。”
為了控制而活的我們,什么時候才學會擁抱無常?
簽書會上,英格麗抬眼一望,面前站了許久未見的史黛拉,從她口中,得悉也是久違的瑪莎罹患癌癥,英便坐言起行,到醫院探望垂死的老友。
有趣的是,這個序幕只在電影才有,在小說里,故事由一個大學的講座開始,出席講座的英格麗沒有名字,她就是“我”。“我去聽一個男人演講,地點在某大學校區……我跑這一趟是有個朋友生病,住在這邊一間專門治療她這種癌癥的醫院。我和這位親愛的老友已經幾年沒見,以她的病情來看,見了這一面,也許就沒有下一面了。”
那位“朋友”,和小說中的“我”,或“他”無異,都沒有姓名。原著作者以“去名化”呈現筆下人物的普遍性,電影導演阿莫多瓦卻把“他”的大學講座,從小說的開篇,搬到電影的后半。更關鍵是,電影中瑪莎曾是身經百戰的戰地記者,在小說里,“她”卻只是一個“坐以待斃”的病人。
由小說到電影,一個問題不能不問,觀眾在看電影《隔壁房間》前后,有讀原著小說的必要嗎?
且看原著小說的內容簡介:一位女士講述了她在平常生活中與不同人的一系列邂逅……在每一個人身上,這位女士都發現了一個共同的需求:渴望談論自己,渴望有一個聽眾來傾聽他們的經歷。直到其中一個人提出了一個非同尋常的請求,將她吸引到了自己的一次強烈的、轉變性的經歷中。
非同尋常的要求,就是陪伴患癌的“她”(瑪莎),完成在美國并不合法的“安樂死”,這同時是“我”(英格麗)重新認識死亡的一課:為了控制而活的我們,什么時候才學會擁抱無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