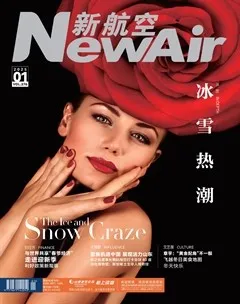徐州印象
徐州,來過許多次,算上中轉火車,次數更多。徐州最早就是津浦線和隴海線的交匯,這兩條鐵路像兩根打毛衣的長針,橫豎把徐州編出了花。很多火車到了徐州,要換火車頭,反著開,像倒著往回走,不少人因此迷向。這是我對徐州的最初印象。
徐州的歷史文化也四通八達。既是楚地,又連上了齊魯和吳越,曾有黃河連接東西,后有運河貫穿南北。劉邦從這里一路打到關中,又打回來,項羽在這里建立都城,又被攻破,歷史在這里涂涂改改,擦去了所謂的輸贏。戲馬臺上秋風依舊,只剩下了游客指指點點。
飲食,徐州也是這樣,哪里的風格都有,又都融匯了徐州的特色。地鍋雞、把子肉、八股油條都算是運河文化的遺留。饣它湯據說起源于彭祖的“雉羹”,喝了四千年;燒烤號稱是中國最早,有畫像石為證,庖廚圖中,掛著肉,捆著羊,跑著雞鴨,走著狗,切著塊,烤著串,非常生動。不過,沂南和滕州也有類似的畫像石,都是東漢時期,沒必要考證誰更早,好吃就行,徐州的燒烤真的好吃。
“饣它”這個字,來徐州之前真不認識,有朋友推薦,還以為是“鉈”湯,擔心中毒。仔細詢問,才知道念“啥”,和魯南地區的“食糝”一個讀音。魯南地方的“食糝”湯以牛骨湯為底,濟寧的“饣它”則是雞湯,加麥仁,沖蛋,早晨喝特別開胃,發汗,還能解頭天晚上的酒,再把酒解的愁解出來。
徐州的湯,配油條或煎包。泡在里面,用徐州人的話,“淹死一個煎包”,如果煎包太大,只能淹個半死。把子肉,或許除了濟南,就只有徐州這么吃了,同樣的名字,類似的做法和吃法,我只在徐州博物館附近吃過一次,不好做對比。
徐州燒烤倒是和濟南有一拼。也是以羊的各個部位為主,除了羊毛和羊角,都能烤的滋滋冒油。而且,都有只用新鮮羊肉不放調料的烤法,濟南叫“白條”,徐州叫白什么,我記不得了,每次都是別人請客,我白吃。
徐州的大餅叫烙饃,卷著東西吃,和山東一模一樣,把面搟好,放在鐵鏊子上烙熟。小時候,我們家也經常做,奶奶還會烙一種帶辣椒的咸烙饃,特別的香,她去世后,我已經三十多年沒有吃過了。
蘇軾在徐州的日子不到兩年,卻讓這座城市銘記了一千年,今天的大型湖島實景演出《彭城風華》,C位給了蘇軾,體現了一座城市對文化的最高敬意。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像蘇軾這樣的文人,真的是上天對中國文化的賞賜。“古彭州官何其多,千古懷念唯蘇公!”
這樣的徐州,明天一定還會更好。無論是下車,中轉,還是換火車頭,調整座位的方向,永遠不用擔心迷路,徐州的火車會載著厚重的文化,讓每個人都可以抵達心中的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