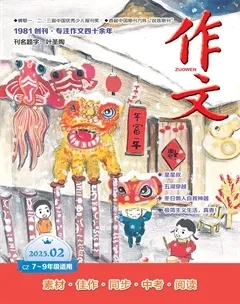起年魚

到了臘月,年就一天天近了。記憶里的年是從在小池塘起魚那天開始的。
祭灶日,父親割去蘆葦,扛著扁擔帶著一身泥點從河堤歸來。次日,吃罷早飯,便張羅起魚。
汲水前,先系桶。將繩子對折,穿過桶底及兩側,折一根柳枝,截成幾節,插在繩子和桶的夾縫處,旋轉繃緊。系好桶,選好汲水位置,鏟兩鍬帶草的泥土放腳下踩實。
父親和大哥雙手各握一根系在繩子上的柳節,手臂揮動,木桶像秋千一樣從地面飛起,“撲通”一聲扎進水里。身體再向后一仰,灌滿水的木桶像裝滿彈藥的炮筒,迅疾出水,飛過水壩,沖向大溝,“轟”一聲,綻放一大團水花。
“咚——轟——咚——轟——”汲水聲如打擊樂般鏗鏘有力,循環往復。幾條白鰱按捺不住躍出水面,有的一個沖刺直抵岸邊……
一千桶后,父親和大哥脫下棉襖掛在柳樹上。我在池塘邊插根樹枝做記號。父親一刻也不歇著,又跟二哥一起汲了五百桶。稍作休息,我接過繩子,對父親說,我也想試試。木桶在空中醉了酒一般,搖來晃去。父親說:“傻孩子,兩個人要步調一致。桶入水時,身體前傾,前手繩子要放;桶出水時,身體后仰,后手繩子要收……”
跌跌撞撞汲了兩百來桶,我渾身冒汗。這時,三爺四爺家兩位叔兄前來助陣。兩個人邊汲邊歌:“老牛入水,燕子高飛,飛過水壩,鐵樹開花……”不一會兒,兩個人便大汗淋漓。大哥和二哥迅速過來換崗。
幾個人輪流著一直戰到天黑。
翌日,我的膀子酸得像是要斷掉。父親說,不礙事,練兩天就好了。
盈盈一池水,不到兩天,我們便從堤壩轉移到池塘。轟轟烈烈又戰兩日,小池塘終于見底。大大小小的魚都匯聚在深池里,還有掉落的紅薯、胡蘿卜,以及睡眼惺忪的癩蛤蟆。池塘四周站著許多看熱鬧的人。
一條白鰱率先躍起,驚擾了身邊同伴,一群白鰱便爭先恐后地跳起,水面銀光閃閃,水花四濺,整個池塘沸騰了,引得眾人陣陣歡呼。
貌若天仙的紅魚在混濁的池塘里似一團耀眼的火苗。草魚泰然自若,慢悠悠地游著。父親雙手對準草魚頭部猛地一掐,草魚瘋狂地甩動尾巴,泥水飛濺,濺了父親一臉一身,眾人大笑,父親也跟著笑。兩位叔兄不斷放長繩子汲水,大哥使勁向上拉系在魚鱗袋上的繩子。我們把拉上來的魚倒進一個小淺水塘,再一條條裝進濕淋淋的口袋運回家。狗子花喜跟在后面寸步不離。
池底見天。黑魚、泥鰍都躲進淤泥里,鯽魚聚集成團,一抓兩三盆。麥穗魚、棒花魚、蒲扇魚、鰷魚……密密匝匝。
天色漸晚,池塘里的魚越來越少,岸上的人紛紛散去。父親的手腳紅得如煮熟的龍蝦,身體直打哆嗦,母親燒好熱水,讓父親泡上。瓷盆、木桶、簸箕、籮筐、塑料布上,到處都是魚。家貓黃丫激動得喵喵直叫。
收獲的魚,大部分賣掉還賬,自家留一點腌起來過年,其余送親友、送鄰里。后莊三愣子媳婦坐月子,母親選了幾條鮮活的鯽魚送去。紹宜娘兒倆孤兒寡母,日子過得扶墻,母親揀了兩條白鰱搭著一大碗小雜魚送去。
也送冤家對頭。隊長小旺家族大,常常以勢欺人。我不愿意送。母親眼一瞪:“小窟爬不出大螃蟹。小孩子家懂什么?”
最后,全莊二十戶人家幾乎一家不落。
父親匆匆吃罷早飯,挑著魚趕集。街道的石子路坑坑洼洼,長龍一樣的攤位自東向西一眼望不到頭,叫賣聲此起彼伏。小街人占據地利,貨攤都是涼床、木架,鄉下來的是清一色的地攤。父親在集市僻靜角落鋪塊塑料布,把魚倒在上面。街上人潮涌動,人們拎口袋,挎籃子,互相熱情地打著招呼。每個人臉上都掛著春天,沉甸甸的年貨壓得竹籃提手吱吱響。幾只麻雀從頭頂掠過,年的香味如同河水一樣肆意流淌。
小鎮十天四個集日。這是新年到來之前的最后一個集,可以多賣幾塊錢。賣完魚,父親一身輕松,買完一些年貨,還想買雙解放鞋。忽想到我們仨來年的學費與母親看病欠下的外債,只得放棄。
朝思暮盼的年終于來了。三十早上,很多人家早早貼好了對聯。我們叔兄弟一行八人隨四爺一起祭祖。近午,鞭炮聲聲,肚子嘰里咕嚕,遠遠地就能聞到村莊飄出的香味。我家延續多年的傳統——兩葷兩素,四菜一湯。土屋里,熱氣騰騰,一家人圍在一起。父親品著土酒。我們三兄弟平時都不飲酒,這是家規,但年三十可以破例。大哥、二哥各飲一杯,我剛濕了下嘴唇,便觸電般連連搖頭,綻放一屋子笑聲。
除夕夜,父親點燃柴火,上面架個槐樹根,濃濃的火焰照亮了漆黑的土屋。一家人圍在火盆旁,邊嗑南瓜子,邊聊天。父親憶昔撫今,暢想來年,鼓勵我們學業繼續進步。火光里,每個人臉上都暖暖的……
賞析:文章以“起年魚”為線索,生動描繪了臘月時節一個普通農家為過年而進行的池塘捕魚活動,以及由此展開的一系列生活場景和年節習俗,充滿濃郁的鄉土氣息和人情味兒。作者通過細膩的筆觸,描繪了汲水、捕魚、賣魚、過年等一系列場景,畫面生動,讓讀者仿佛身臨其境。語言質樸自然,富有節奏感。文化內涵豐富,寫了祭祖、貼春聯、放鞭炮等年節習俗,以及鄰里之間的互助與分享,傳遞了正能量,弘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